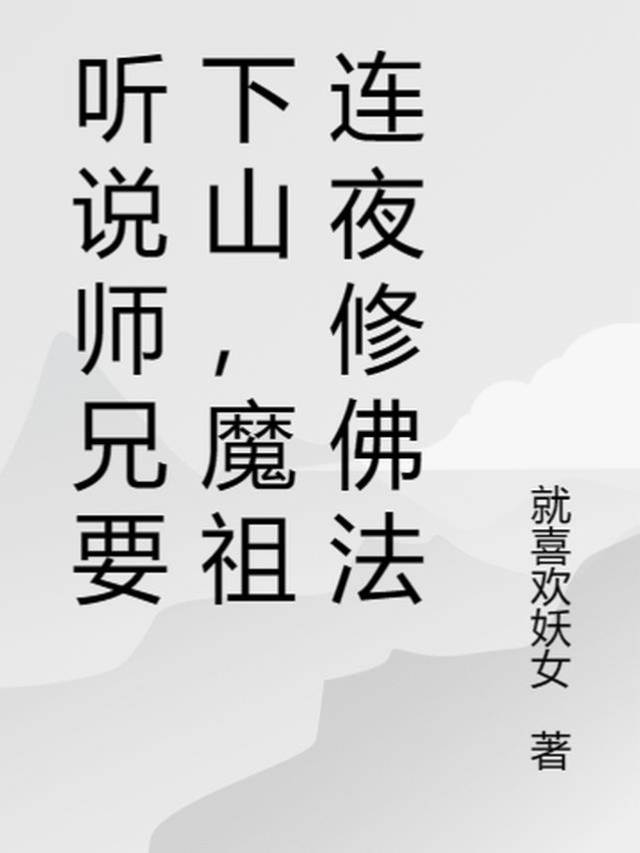《雅騷》 第19章 左耳進右耳出
霞爽軒在東,壽花堂在北,戲臺在南,圍在中間的就是半畝大小的一池碧水,在霞爽軒或壽花堂都可以觀賞戲臺上的演出,軒、堂、臺之間有曲廊相連。 前幾日一場大雨,暑氣消退了一些,依山傍水的V園當然更為涼爽宜人,午前的日照下來,池中鯉魚往來遊,那些鯉魚大大小小,紅黃灰黑,群結隊地遊躥,當那些魚兒不約而同潛水裡時,水面漣漪圈圈紋紋,微微漾,好似一塊綢的大幕被風吹皺,這大幕在等著張原去豁然拉開,就會有妙的事發生――
“會上演什麼,鯉魚躍龍門?”
張原一邊跟在族叔祖張汝霖後走,一邊這樣想,一尾胖的大紅鯉魚率先躍出水面,幕幔撕破,若無其事。
就在這時,張原聽到邊那個跟王思任的俊俏年“嗯”了一聲,鼻音婉轉,帶著詢問、試探、矜持,含意富,同時腳步一緩,與前王思任拉開幾步。
張原從池魚這邊收回目,側頭去看,正與年目相接,這年個頭比他還高一些,雙眸如黑寶石一般,清瞳可鑒,見張原看過來,年眉微微一挑,邊那一笑意很象王思任,低聲問:“你幾歲?”
這年先前立在王思任後,張原沒留意,他眼疾雖然好了,但眼睛還不是很好使,這時近在咫尺,總看得清楚了,第一便是,這年是郎,扮男裝的,因為那、眼神、聲音都象是子――
Advertisement
雖然如此,張原還是不敢確定,這世道怪事多,那“可餐班”的聲伎王可餐就是年郎,可那模樣神態比子還象子,還有,李玉剛花枝招展的在那唱《貴妃醉酒》,不明底細的人誰敢說他是男的?至於說看,呃,這年一襲素細葛長衫寬大飄逸,除非很大,否則也看不出來,再說了,他憑什麼探尋人家是男是?
“算是十五歲吧。”
張原答道,這世上不確定事太多了,他可是兩世為人,所以不好斬釘截鐵地說自己隻有十五歲。
霞爽軒與壽花堂相隔不過四丈遠,也就隻有問答一句的時間,張汝霖和王思任已經步壽花堂,轉過來就座,那俊俏年急趨數步,又站到了王思任後。
戲臺上的曲笛已響起,王可餐嫋嫋婷婷而出,開唱:“夢回鶯囀,煞年遍――”
張原侍立在族叔祖張汝霖後,等待問話。
張汝霖很耐得住子,眼睛只看著戲臺,手按節拍賞戲聽曲,並不開口問話,這想必也是一種試探,看看這個頗有天賦的族孫耐心如何?
張原耐心當然足夠,百日的黑暗熬過來,這片刻等待算得了什麼,侍立一邊,穩穩沉靜。
等到“驚夢”一出唱了一大半,張汝霖站起,走到壽花堂外的圍廊上,面對竹樹蓊鬱。
張原跟了出來,聲:“叔祖。”
張汝霖點點頭,問:“你這過耳誦的本事真是得了眼疾後才有的?”
張原答道:“是。”
張汝霖道:“這也算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而且你眼疾也痊愈了,那我問你,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有這樣天分足可自傲了?”
Advertisement
張原道:“晚輩沒有這樣想過。”
張汝霖問:“怎麼會沒這麼想過?”
張原道:“晚輩覺得記好若不能活學活用,那讀書再多也隻能算是兩腳書櫥,更何況晚輩現在隻囫圇吞棗記得幾部書,義理不明、文理不通,哪裡敢自傲呢,有宗子大兄、祁虎子這樣的神在前,
晚輩真沒覺得有什麼可自傲的。” 張汝霖頓時和悅起來,連連點頭:“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你這從容不迫的氣度,宗子也不如你,嗯,你今年十五歲,啟蒙雖然晚了一些,但還來得及,你眼睛既已痊愈,那就盡早社學讀書吧,先把社學必讀的書籍通讀了,待明年我推薦你去大善寺師從啟東先生,啟東先生是萬歷二十九年辛醜科進士,這些年因為接連守喪,一直未京選,啟東先生儒學淵博,更且於製藝,因家貧去年來大善寺設館,擇徒極嚴,祁虎子已拜在他門下,張萼頑劣,被拒之門外――”
說起張萼,又想起《金瓶梅》,張汝霖問:“你真的不是在張萼看得的《金瓶梅》?”
張原道:“晚輩不敢欺瞞叔祖,的確是眼疾昏蒙憂憤難當時,夢見一山,有瀑布如雪,松石奇古,山巖間卻有幾個書架,藏書數千卷,晚輩一一翻看,醒來時能記得大半,而且記也變好了。”
張汝霖不得不信,說道:“那是你的宿慧,也是福緣哪,好了,你去吧,勤學苦讀,會有出人頭地之日的,以後若有什麼難就來告訴我。”
Advertisement
張原道:“多謝叔祖,晚輩一定努力上進。”施禮而退――
張汝霖又道:“去向謔庵先生見個禮,莫失了禮數。”
張原正有此意,王思任是他比較欣賞的晚明人之一,還有,王思任邊的那個俊俏年是什麼人,這點好奇心還是有的。
戲臺上的《驚夢》一出已演完,張原走到王思任座前,鄭重施禮:“小子張原拜見謔庵先生。”
王思任笑問:“尊叔祖已經考過你了吧,還要來我這裡請考?”
張原道:“曲終人散,晚輩是來向先生告辭的。”
王思任號謔庵,自然是非常會說笑的,說道:“賢侄天生神耳,讓人羨慕,隻是這每日除了讀書聲,還有鳴犬吠、鄉鄰爭罵,種種聲響過耳不忘,豈不脹塞?”
張原含笑道:“好教謔庵先生得知,耳朵有兩隻,可以左耳進右耳出。”
王思任放聲大笑,對張汝霖道:“肅翁,你這個族孫有趣,也有捷才。”他後的那個俊俏年也低著頭笑。
張汝霖笑道:“謔庵既這般說,不如收他為弟子, 謔庵的時文乃是一絕,都說時文枯燥,謔庵的時文卻是靈多姿,於八框框中,偏能才逸出,兩百年來第一人也。”
張原便待拜師,王思任卻一把扶住他,笑道:“我這時文學不得,學我者必不中,既我自己也不知當年怎麼就中了,僥幸,僥幸!”
張汝霖大笑,連聲道:“謔庵,你太謙了,不肯教他也就罷了,怎麼把自己也一並取笑了。”
王思任道:“能笑得自己方笑得他人,不然只顧笑他人,那是輕薄。”
張汝霖向張原擺擺手,示意他可以走了,王思任的那些非禮逾矩的奇思怪想不適合年人多聽。
張原走出壽花堂,回頭見那俊俏年也正好朝他看過來,肯定是一直盯著他背影看呢,便向那年招招手――
年一愣,遲疑了一下,走了過來,拱手問:“何事?”
張原也拱手道:“還未請教尊姓大名?”
年道:“姓王。”不肯說名。
張原心道:“必是子無疑了,結似乎也不明顯――哦,我才十五歲。”拱手道:“王兄,後會有期。”轉往霞爽軒那邊走去,不料那年追上幾步低聲問:“那《金瓶梅》哪裡能購得?”
張原“啊”了一聲,心道:“看《金瓶梅》的年惹不得啊。”搖頭道:“買不到,買不到。”大步回到霞爽軒,再看那年,已經站回王思任邊。
――――――――――――――――
求票票啊,求票票,新書票票很重要,請書友們果斷支持一下。
猜你喜歡
-
完結845 章
神醫狂女
她,是一代鬼醫的繼承人,她腹黑記仇,一朝靈魂穿越,卻重生在一個身中劇毒受盡折磨的廢物身上。再一睜眼,她不再是那個任人欺淩折磨的廢柴三小姐,靠醫術覺醒天賦,從此,她要做自己的主。『低調』做人,『高調』做事,她一向都是『和平愛好者』,不喜歡『打打殺殺』,隻要不欺到她頭上,她就是一隻可愛的『小綿羊』。帶著萌寵到處遊山玩水,順便收收小弟,調戲小姑娘。納悶,她帶著小可愛好好的環遊世界,什麼時候招惹一個麵癱?雖然臉長得不錯,八塊腹肌看起來好想摸……咳!但是這麵癱悶騷的個性是個什麼鬼!「大爺,你喜歡嗎?」指著自己的臉,眨眨眼望著麵癱大爺。「恩!」好吧,大爺惜字如金!「大爺,你滿意嗎?」乖巧的給大爺捶腿,討好的看著大爺。「恩!」大爺還是麵癱的大爺。「大爺,我走還不行嗎?」
146.1萬字8 53695 -
完結820 章

我在原始社會風生水起
我是現代人我怕誰!!地毛?不認識!臭果?像屎!我有系統我怕誰!!開啟?不行沒有技能點!技能點在哪?努力干活有就了!我干我干我努力干!系統呢?不能換東西,只給個百科全書有什麼用?說好的有系統的現代人可以躺平,為什麼我到了這里一天不干活就沒有飯吃?想吃飯?自己找!想住房子?自己建!想......?好吧,我知道了,一切靠自己,那就建個王國玩玩?且看我如何撐起原始的大梁,有吃有住有美女!這才是有系統的現代人應該有的生活!
154.6萬字7.73 39989 -
連載4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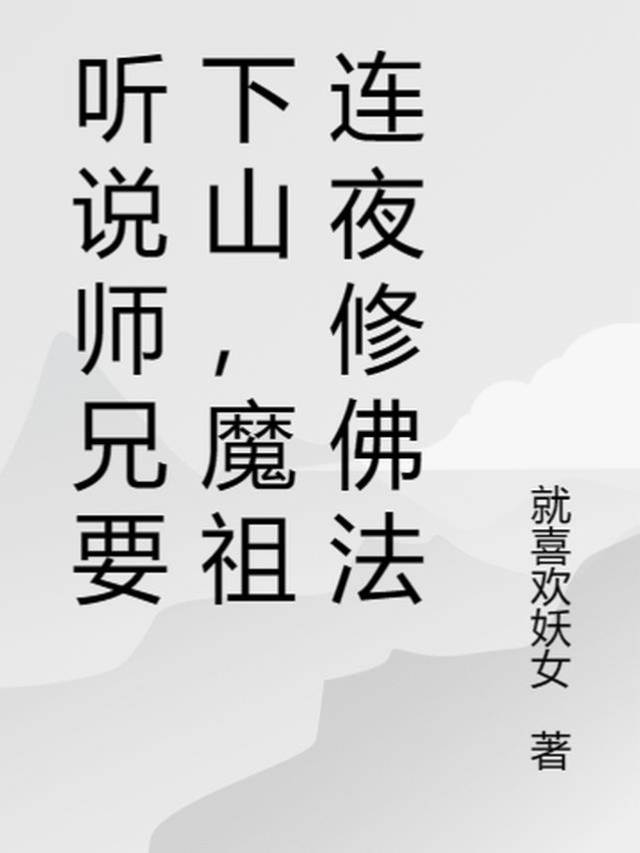
聽說師兄要下山,魔祖連夜修佛法
王慧天,自卑的無靈根患者,劍術通神。自他下山起,世間無安寧!魔祖:“啥?他要下山?快取我袈裟來。”妖族:“該死,我兒肉嫩,快將他躲起來。”禁地:“今日大掃除,明日全體保持靜默,膽敢違令者,扔到山上去”向天地討封,向鬼神要錢。燒一塊錢的香,求百萬元造化。今日不保佑我,明日馬踏仙界……
87.8萬字8.18 148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