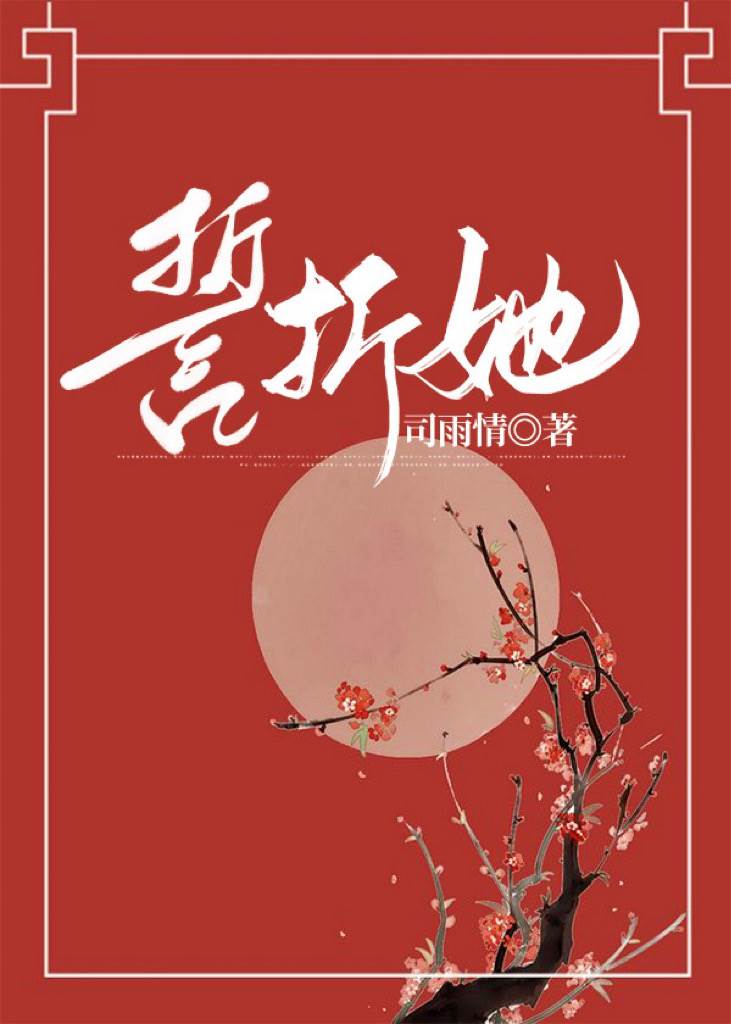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劍尋千山》 第27章 第二十六章
夜深重, 西境各宗徹夜不眠。
謝長寂主合歡宮的消息一夜傳遍西境,擾得西境眾人揣測紛紛。
鳴鸞宮中,子素玉簪, 正提筆在書桌上作畫。
一位黑人修士跪在地上, 恭敬匯報:“溫清本是打算帶五千人給花向晚的夫君一個下馬威, 結果謝長寂出現, 反將溫清的臉打壞了。”
“確認打在臉上?”
子在畫面上勾勒出一朵艷麗的梅花。
黑修士應答:“對,用桃枝打的。”
“那看來, 他是對花向晚真的了。”
子說著, 涂出一樹枝:“后來呢?溫清不可能就這麼罷休。”
“他夜里去了合歡宮,差點被謝長寂殺了。”
“謝長寂敢殺他?”子詫異。
黑人點頭:“謝長寂曾經屠了一界,殺孽非常, 似乎有些不管不顧,若非花向晚攔著, 已經殺了,溫清走之前,說要給他們大婚送一份禮。”
這話讓子來了興趣, 抬眼看向黑人:“什麼禮?”
“不知。”
黑人搖頭,子想了想,輕輕一笑:“好歹是我的未婚夫婿, 我得幫幫他。你今夜過去——”
子抬頭,清雅的眉目間俱是溫和,仿佛是在吩咐什麼救濟災民的好事。
“把薛子丹的‘云煙’給溫清, 告訴他,若天劍宗的弟子死于花向晚人之手, 那麼,這門婚事, 也就不了了。”
聽到這話,黑人微微皺眉,他抬頭,似有遲疑:“若謝長寂發了瘋,直接殺了溫清怎麼辦?”
“不會的。”子聲音搖頭,“花向晚不會讓謝長寂殺了溫清,若溫清死了,我們即刻聯合清樂宮前往魔宮,請魔主出手,聯合西境全宗,立斬謝長寂。花向晚不會讓合歡宮陷以一宮之力對上整個西境的局面。”
Advertisement
“但若保了溫清,”子笑起來,“那與天劍宗的聯姻,便算是完了。”
“可……”黑人還是有些擔心,“若謝長寂追查到我們怎麼辦?”
“為何會追查到我們?”
子看回來:“下毒的是溫清,制毒的是薛子丹,而你——與我鳴鸞宮有何干系?”
黑人不說話,許久后,他輕聲一笑:“主說的是。我這就去辦。”
“去吧。”
子抬手,一只翠鳥落到手指上,溫欣賞著這只活蹦跳的翠鳥,片刻后,抬手覆了上去。
翠鳥驟然尖銳起來,沒了一會兒,就流在子素白纖長的手指上,回過頭,走到畫前,將水往畫上一甩,似如梅點點而落。
欣賞著畫面笑起來,溫道:“真好看。”
*** ***
合歡宮,花向晚愣愣看著謝長寂。
雖然知道早晚有這麼一天,但沒想到謝長寂會這麼直接說出來。
謝長寂神淡淡,這話似乎只是例行公事。
花向晚想了想,只道:“如今我筋脈不暢,靈力控制不周,貿然滋補金丹,怕是有害無益。還是等筋脈暢通之后,再做打算。”
說著,笑起來,面上十分誠懇,但笑意卻不見眼底:“你的心意我領了,但還是得再等等。”
謝長寂不說話,他遙遙看著花向晚,好久,終于才低下頭,應聲:“嗯。”
花向晚見謝長寂不作糾纏,舒了口氣,轉走向凈室。
謝長寂抬頭著的背影。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
他覺自己心里似乎住了一條巨蟒,它沒有神智,它所有求,所有妄念,都是眼前這個人。
它想纏住,死死裹,將每一寸,每一寸骨頭,都與它相連。
Advertisement
想要的過去,想要的現在,想要的未來。
想要將一切據為己有,不讓他人窺視半分。
這樣的念頭太為可怖,他不敢讓知曉,甚至不敢讓察覺。
他聽著房間里的水聲,好久,才克制住自己走上前的沖,轉到了團上坐下。
對于謝長寂的一切,花向晚渾然不知。
了衫,將自己浸水中,悶了一會兒后,才覺自己冷靜幾分。
謝長寂是個目標很強的人,自律克己,定下目標,便一定會完。
一開始還想或許他忍不了這件事,但今日看來,之前他大概是估計狀態,打算找個最佳時機。
就像當年山雙修,雖是不得已,他也神志不清,但是他還是會把這件事做完。
如今他一心一意想幫,這最重要的一件事,自然不會放棄。
其實換旁人,倒也不是很在意,也沒什麼資格在意。
可謝長寂……
笑了笑,決定不作多想,靠在浴桶上,將水凝結刀片,在手指之間翻轉,鍛煉著手指上的筋脈。
這是傷后開始的習慣,一點一點磨,一點一點練。
每一寸筋脈,都是合,銜接,從無法使用,鍛煉到今日。
這次刀片終于沒有割出傷口,冷靜下來后,回頭看了一眼云紗簾外端坐的道君,片刻后,垂眸收起刀鋒。
垂頭看向水面,水面浮現出兩個金字——
云煙。
花向晚看著金字,想了想,抬手一撥,水面字消失,又了普普通通的清水。
簡單做了清洗,花向晚站起,走到床邊,謝長寂已經坐在團上,花向晚已經習慣他夜里打坐,打著哈欠上了床,好奇開口:“你天天打坐,不累嗎?”
Advertisement
“還好。”
謝長寂背對著,聲音不咸不淡。
花向晚撐著腦袋,靠在床上,漫不經心閑聊:“三日后咱們大婚,你明日去對一下婚流程?”
“好。”
“哦,有一點我和你說清楚,”花向晚想起什麼來,微瞇上眼睛,“因為是我迎你合歡宮,按著西境的規矩,這次是我的主場,我得在外面招待賓客,你在房等我,查探魊靈這件事,你只能在同我一起行禮時注意,這事兒你不介意吧?”
查探魊靈不方便也就罷了,畢竟還可以暗中查。
但換謝長寂在房等,便有些像贅了,把握不清楚,對于謝長寂這種土生土長的云萊正派修士而言,這事兒好不好接。
然而謝長寂聞言,也沒多說,只淡道:“好。”
花向晚聽他不介意,也放下心來,靠在床上,瞇著眼道:“你要是想睡,我讓人給你支個床。”
說著,花向晚又覺得這話作為夫妻來說,顯得很不近人。
于是又客氣了一句:“當然,你想上來睡也行。”
雖然覺得,謝長寂大約是不會上來的。
畢竟他要用努力修行,而且,記憶中,他是很怕與人接的。
記得那些年,不管再艱辛的環境,他都始終和保持距離,雖然努力制造機會,但他都能想盡辦法和不同床。
買通店家制造“只有一間房,只有一張床”的假象,他就能在地上打坐打一晚上。
故意傷喊冷,他就能運功給發熱一夜。
如此柳下惠千古難尋,這些時日他更是恪守規矩,想來雖然過了兩百年,習慣應當沒多大變化。
除了更瘋,更孤僻,話更以外。
花向晚迷迷糊糊睡過去,等睡著,謝長寂睜開眼。他回過頭,靜靜看著床上的人,過了片刻后,他站起,掀了的被子,便鉆了進去。
他上有些冷,花向晚察覺,便下意識了。
謝長寂想了想,便運功讓熱了起來。
花向晚質冷,沒一會兒,覺到熱源存在,便往前挪了挪。
謝長寂靜靜注視著,皮很白,在月下仿佛是著。
他覺自己心里那只巨蟒出了信子,盤旋著,打量著,纏繞著。
過了許久,他終于才閉上眼睛。
那一夜他做了一個夢,夢里似乎又回到那個山。
他抱著,好像要將絞殺在懷里。
的腰好細,好,約約的啜泣聲,似如玉碎擊瓷一般人。
什麼都不記得,只會他的名字。
真好。
花向晚一夜睡得很沉,過往是睡得從來沒這麼死的。
想來或許是因為謝長寂守夜的緣故,其他沒把握,謝長寂現在不會殺,是很清楚的。
第二天醒來時,謝長寂已經不在房間,靈南進屋來伺候著起,花向晚看了一眼外面,忍不住詢問:“謝長寂呢?”
“上君去找玉姑核對婚禮流程去了。”
靈南回著花向晚的話,同時給花向晚系著腰帶,說著近來的況:“這次宮里要請的人多,請帖早早發下去,最近宮都忙瘋了。”
“嗯。”
花向晚點頭,想了想,只道:“這次負責宮宴的人都查過了?”
“查過了,”靈南應聲,“都是合歡宮自己的人,放心吧。”
“其他無所謂,”花向晚叮囑,“但給天劍宗那邊的食住行要注意,若是出了岔子,到時不好收場。”
“這我可不敢保證,”靈南實話實說,“婚宴請這麼多人,人手這麼雜,我只能說肯定盡力。咱們與其等著他們坐以待斃,不如主出擊吧。”
靈南隨口一說,花向晚聞言,卻是笑了起來:“既然你保證不了,那就去幫我做件事。”
“嗯?”
“別讓人發現,”花向晚聲音很輕,“去搞兩株靈均草給我。”
“明白。”
靈南點頭:“我保證不讓人發現。”
靈南伺候著花向晚起,下午就出了門。
謝長寂好似很在乎婚禮,每日親自過去檢查細節,等晚上回來守夜。
這幾日花向晚都睡得很好,等到大婚當日,神飽滿,興致昂揚。
合歡宮這場大婚從花向晚去云萊就開始著手準備,得知來的是謝長寂后,又趕增加了規格,當日禮儀繁雜程度與天劍宗截然不同。
兩人從清晨便起床,開始坐在花車上游街,等到午時到達祭壇,一起祭天簽下婚契。
婚契分分三份,一份燒在鼎中祭告上天,另外兩份各自給自己帶來的侍從,裝禮盒封存。
婚契花向晚先寫,謝長寂再寫,謝長寂看著婚契上落下花向晚的名字,眼神溫和了許多。
然后他寫下自己名字,他寫得很慢,很鄭重。
等寫完后,他抬眼看向花向晚,輕聲詢問:“這份婚契,可作數了?”
花向晚笑了笑,只道:“那自然是作數的。”
只是到什麼時候為止,卻是不知道了。
說著,兩人牽著手,走下祭壇,然后乘坐花車,一起回到合歡宮。
等到宮中,已到晚宴時間,上前修士齊聚宮,花向晚和謝長寂攜手從宮門一路走到正殿。
所有修士都在旁邊觀禮,花向晚轉眼打量著謝長寂:“可察覺什麼了?”
謝長寂不說話,他垂眸看著紅毯,一一應過去。
西境元嬰期以上修士已經齊聚,剩下不在的并沒有多,如果這里沒有,那就要從剩下的名單,以及出西境定離海的名單中去找。
這兩份名單都有很多人,但如果兩個名單核對在一起,外加元嬰期以上,那篩選出來的修士,便很了。
謝長寂心里坐著打算,面上不,只道:“好好婚,不急。”
謝長寂說不急,花向晚更不急,兩人一起走到大殿,能坐到殿的,都是西境頂尖人。
十八門門主和其親屬坐在最外面接近大門位置,往上是九宗宗主及其親屬,再往上便是三宮主及其兄弟姐妹,等到頂端,便是三宮本人。
花染坐在最高,今日特意畫了濃妝,遮掩了氣,看上去與當年巔峰期并無不同。
左右兩邊,一邊是一位黑中年男人,另一邊則是一位金人。
猜你喜歡
-
完結308 章
農家異能棄婦
王秀秀是一個標準的糟糠妻,本本分分地侍奉刻薄公婆,操持家務,善待幼弟幼妹。然而丈夫一朝秀才及第另結新歡,幾年的辛勞換來的卻是一紙休書……新文《剩女田園》被左右的人生,被成全的貞烈,記憶中全是被拋棄被背叛的片段……重生而來,命運重演,想
81.2萬字8.18 93379 -
完結406 章

穿越農家之妃惹王爺
《本文一對一,男女主雙潔,種田爽文。》穆清媱這個現代法醫穿越了,變成了村裡的病秧子。為了逃脫祖母的壓迫,帶著受欺負的娘和姐姐脫離他們。動手,動腦,做生意,賺銀子。什麼?祖母那些人後悔了?那關她什麼事!敢來找事,穆清媱肯定動手又動口,收拾的他們說不出話。小日子過的溫馨又愜意間,一堆熱心腸的人給她介紹各種優秀的小夥紙。“沒看到我家沒有兒子嗎?本姑娘隻招婿,不嫁人。”一句話打發一群人。本以為她可以繼續悠閑的過日子。啪嗒!“聽說你家招女婿,本王自帶嫁妝,過來試試。”“呃”
171.7萬字8.18 80843 -
完結1230 章

女相傾國
乍一穿越,明雲裳便被人萬般逼迫,個個欲置她於死地!隻是溫良恭謹的女子早已成了腹黑的狐貍,膽小的外表下藏的是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強大靈魂!宅鬥嗎?嫡姐後母儘管放馬過來!看看誰的陰謀的陰了誰!想搶走母親留下的嫁妝?先看看你有冇有那個本事!嫡姐想讓她嫁給瘸子,她便讓嫡姐一出嫁便成了怨婦!後母想要她的命,她便讓後母犯七出之條,徹底離開明府!不要怪她心狠,她隻是有仇必報而已!……明雲裳決定要好好搞事業,一不小心,成了女相!某男人抱大腿:娘子,茍富貴,求罩!
224.5萬字8 18606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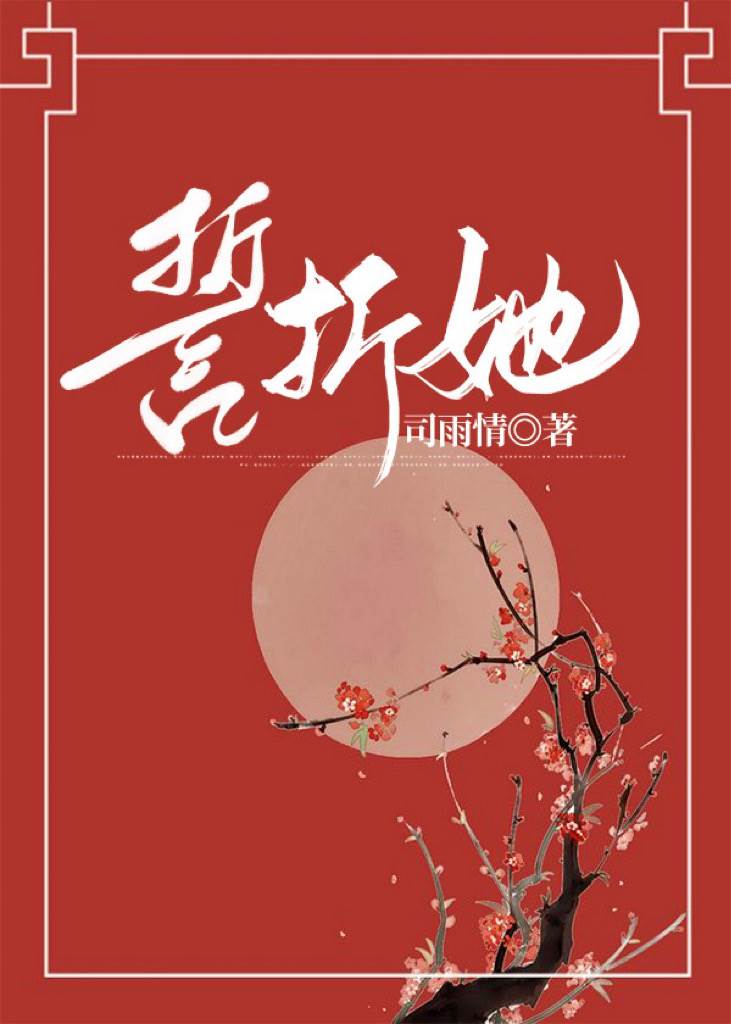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88 章

繼妹又萌又奶,哥哥連哄帶拐
白嬰四歲時,娘親突然回來帶白嬰改嫁,白嬰一躍成為朱雀國第一世家的二小姐。渣爹和姐姐都在等著看白嬰的笑話,說白嬰會被繼父抵觸,會被繼兄厭惡,會被繼祖母掃地出門。 結果——沉靜寡言的繼父,給了白嬰一個儲物袋,儲物袋裏有數不完的錢錢。容冠天下的繼兄,送了白嬰一件上古大能的法衣,扛摔扛打扛天雷。嚴苛的繼祖母,不止將壓箱底的嫁妝都塞給了白嬰,連帶著白嬰那作天作地的母親都給看順眼了。渣爹和姐姐:那個令三界震驚的小少年追著白嬰跑也就算了,為什麼繼兄身份也強大到駭人?
18.3萬字8.18 43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