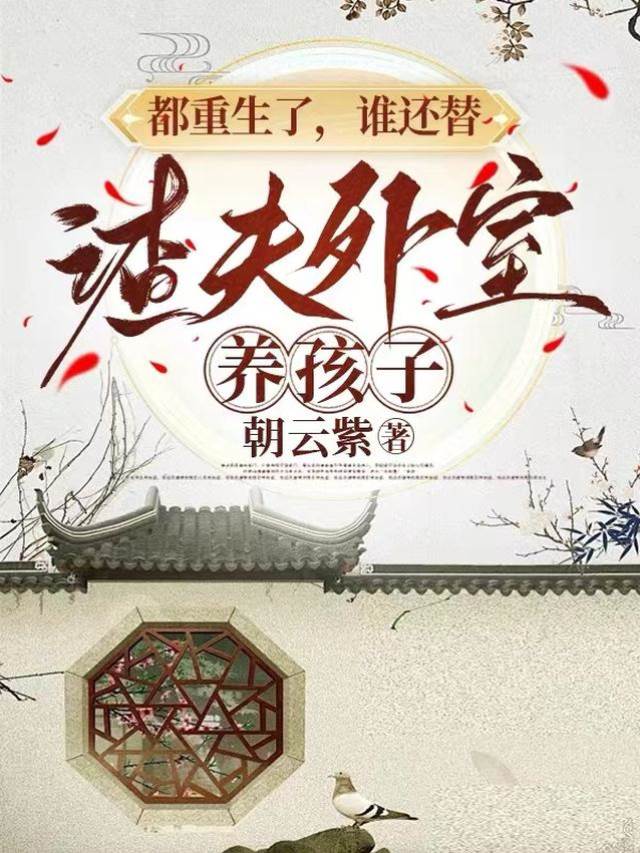《我在東宮當伴讀》 第7章 第 7 章
第七章:
年面如薄紙,輕晃的燭火在他比玉蒼白的面上跳躍,澄黃明亮的火倒映在他烏黑的眼瞳,素來波瀾不驚的眼底,此刻充滿驚慌失措之,惶恐又害怕,生了病的人兒看上去更加孱弱。
盛皎月的手指攥著前的襟,被修剪干凈的指蓋用力摳著盤扣,生怕男人上前來的裳,短促的呼吸逐漸平靜,低聲回話,“殿下,我后腰的傷已經好的七七八八了。”
太子面清冷,窗前泠泠的晨照著他的側臉,下頜鋒利,眉眼冷峻,男人糲的拇指著藥瓶,眼神漸漸變暗,角上揚的弧度也出攝人寒意,男人淡道:“大夫可不是這麼說的。”
衛璟能做到這個地步已經十分給他臉面,若按他平日的脾氣早就扔下藥,轉就走。
盛皎月萬萬不可能開裳讓太子幫上藥,烏睫微,澄澈眼瞳里盈著人的流,猶不自知。輕啟紅,“確實無大礙了,太子不必憂心。”
話已經說這樣。衛璟再繼續堅持就像是在強人所難,他心中已有諸多不快,冷眸盯了他片刻,隨手將金瘡藥在案桌,淡淡說話也有儲君的威懾,“既然病了,這幾日便好生歇息。”
盛皎月繃的后背稍有舒緩,方才的恐懼也逐漸消弭,纖弱蒼白的面龐染著些許氣,“嗯。”
小僧已經煎好祛風寒的湯藥。碗盅里墨黑滾燙的藥冒著熱氣,聞著藥味便覺得苦。
盛皎月不由自主蹙起秀氣的眉頭,本想等太子走后再將難以下咽的湯藥倒掉,可男人似乎并不打算立馬離開。
太子微抬下頜,頷首示意,命人將湯藥端到他面前。
盛皎月從床上坐起子,綢緞細膩的烏發如墨鋪陳落,墜在腰間,落在膝上,只著了單薄雪寢,雖已用白布裹好口,面對太子冷銳審視的眸,還是會覺得不安。
Advertisement
出手,寬大袖口里出的半截手腕細白瘦弱,素白纖的拇指接過碗邊,瀲滟紅抵著碗沿,苦著臉閉眼一口氣灌了小半碗湯藥。
苦味道從舌尖傳腦后,被苦的想吐出來,不得不忍了回去。
剩余的半碗,著實是不想喝。
但抬眸瞥見太子冷淡朝看來的眼神,不得已又著頭皮咽進嚨里。
盛皎月在家喝藥都是要人哄的,每每喝完丫鬟還會將提前備好的餞甜糕遞上來,給解取苦味。
衛璟冷然的目逐漸從的臉龐拂過,仿佛年抬袖,他又聞到了那淡淡的清香,書墨卷香里裹挾著淺淺的梨木香,許是上所穿都被香灰熏過,味道偏甜膩,倒不像他這個人如此清冷。
衛璟還只當他什麼都不怕,沒想喝碗藥像要了他的命,愁眉苦臉,眼神抗拒,怕得很。
—
盛皎月的傷寒好的很慢,這兩日就悶在廂房里,哪里都不去。
大雪連下三天才停,山中早已是白雪茫茫一片銀裝素裹,山林里的苦竹被斷了好多,等這日放晴,寺廟主持便讓小僧去清掃竹林。
日影瞳瞳,午后的日燦爛刺眼。過門窗的隙,照亮冷偏僻的小屋。
盛皎月穿了月白長衫,去院子里曬了會兒太。照過太更襯得是冰雪,白里紅的氣。好似泛著甜香的桃。
穿過長廊,步履緩慢去后山的竹林閑逛片刻。
林中有一供人休憩的亭子,盛皎月額頭被曬出細膩干凈的汗珠,抬袖了額上細的汗,在亭子里坐了片刻。
竹林后是一片梅林。
臘梅正是深冬最冷的幾天才開,遙遙便聞到了陣若有似無的梅花香。
Advertisement
盛皎月穿過竹林,站在梅樹下忍不住踮起腳,勉強夠到梅花枝頭,閉著眼聞了聞枝椏上綻開的梅花香。
年背脊拔細瘦,腰肢纖細,側臉如明月寧靜,皮比檐上的雪還要白上幾分。在后背鋪開的長發,隨著林中的風輕輕晃,雙里呼出暖熱香甜的氣息,站在遠,不仔細看都會將人認錯子。
顧青林差點就認錯了,梅林后的蔽院落里,他掀起眼簾,余瞥見紅梅樹下忽然多出的那道娉婷影,驚不變的世子爺明顯怔松片刻。腔有一瞬心跳劇烈,待瞇起眼細細觀察一番,才認出那人是誰。
裴瑯也認錯了人,小將軍眼神幽幽盯著不遠的影,隨手指了指,問道:“那姑娘是誰?”
太子祭拜這幾日,寺不會讓外人出。
裴瑯以為這名貌子是他們某人中的姬妾,他自小在邊城長大,那里大多是爽朗直率行為魯的子,小將軍還真沒見過長得這麼漂亮的,一時有點新鮮。片刻間心思就想很遠,太子表哥不好,也不缺貌寵妾,他若是開口要人,應當也不難。
衛璟的目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了過去,沉默幾秒,涼薄的邊緩慢綻開一抹譏誚冰冷的笑意,“他可不是什麼姑娘。”
裴瑯不解。
顧青林回過神,心中十分惱怒,沉著張俊俏的臉,“小將軍認錯人了,那是盛家的公子。”
裴瑯反復咀嚼這幾個字,“盛家的公子?”
“嗯。”
裴瑯對盛家自是不陌生,張貴妃的表兄便是盛家大爺,七皇子能有想要奪嫡的野心,不仰仗徐閣老,還有榮寵興旺的盛家。
原來這個模樣漂亮的年,就是盛家送進宮里派去監視討好太子表哥的人。
Advertisement
裴瑯方才起的那點好頓時消失不見,厭從心起,冷聲譏笑:“娘們唧唧,一點男子氣概都沒有。”
他的手搭在腰間的長劍劍柄,又漫不經心地說:“我一只手就能掐斷他的脖子。”
顧青林笑:“小將軍現在可不能沖,等到時機再殺也不遲。”
裴瑯不過隨口一說,劍眉星目下是冷肅矜貴的神,淡道:“我有分寸。”
小將軍在邊城喜走鷹打馬,桀驁,行事直接,最不喜歡擅使心計投機取巧的小人,更看不上京中手無縛之力的文弱書生,和只會耍皮子的酸儒。
先前將軍府尚未離京,便與盛家有過齷齪。
新仇舊恨,加在一起,都快不夠清算。
盛皎月還不知庭院里還有旁人,解下上雪白的斗篷,仰著素白氣的小臉,澄澈的眼珠目不轉睛盯著枝頭的紅梅,盛開的梅花點綴昨晚落下的白絮,紅白相間,別有韻味。
盛正熾,被滋養的雪白皮沁著淡淡的緋紅,領.在外的白皙脖頸稍染,泛著甜的香氣。
清冽如冰雪的人在燦爛熾目的下綻起一抹淺笑,不笑時看著清貴如雪,笑起來時融化了眼底的冷淡,眉梢浸宜人的暖甜。
隔著棱形石窗,衛璟靜靜的目及梅樹下緩緩笑起來的年,男人眼神岑寂,一片難言的暗,不知過去多久,他氣定神閑移開眼睛、
裴瑯掀眸看向表哥,好奇地問:“表哥這次怎麼帶上他了?”
衛璟心底莫名起了躁意,腦海還是方才盛清越的笑,衛璟一直都知道他這個伴讀長得很好看,有幾分,以前竟然沒發現,他笑起來比不笑還好看。
衛璟回神,隨口敷衍:“一時興起。”
裴瑯不怕被盛清越發現他已經京,但讓他知道到底也是樁麻煩,“也無妨,若讓他察覺我便他見見。”
衛璟吩咐:“在京城待夠你就回去。”
“我知道。”
盛皎月折了兩枝梅花,離開時好像聽見廊邊傳來了些靜,邁開步子緩緩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走過去,瞧見院子里的三個人,眼眸猛然間睜大。
站在右側的年穿黑束袖青花絳袍,玉冠束起長發,眉眼冷銳如箭,迎面而來凜冽的殺意。
是小將軍裴瑯。
盛皎月對這位小將軍也是能躲就躲,見過裴瑯在戰場斬殺敵軍的鮮淋漓,手起刀落,干凈利索,殺人時毫不手。
盛家顛覆前夕,裴瑯曾潛后院的房間,徒手劈暈了的丫鬟,很不耐煩著的脖子,“隨我去邊城,我能護你父兄不死。”
那時候裴瑯還不知道的兒,依舊將認作男子,要同他搞斷袖。
后來裴瑯在宮里見到,對總是沒個好臉,說話夾槍帶棒刺耳難聽。
盛皎月不確定他們有沒有看見自己,匆匆逃開,回了后院的廂房。
裴瑯看清了他的臉,模樣不錯,錯愕驚慌的眼神噙著朦朧意,微微發紅的脖頸,倒比冰天雪地里的紅梅還惹眼。
裴瑯說:“表哥,盛清越很怕你。”
瞧見他們跟見了鬼,還以為他們沒看見他。
衛璟抬手,修長分明的拇指緩慢轉玉扳指,想到年驚慌失措躲開的姿,輕笑了聲,這幾天盛清越確實反常。
到底是真的在躲他,還是擒故縱故意同他演戲,衛璟有的是時間弄清楚。
作者有話要說:好多狗男人都喜歡我們寶貝囡囡!哼!
猜你喜歡
-
完結148 章

穿成極品婦,靠著系統脫貧致富
大淵朝三年干旱,地里的莊稼顆粒無收,吃野菜、啃草根等現象比比皆是,許多人被活活餓死。錢翠花剛穿來,就要接受自己成了人嫌狗惡的極品婦人的事實,還要帶著一家人在逃荒路上,艱難求生。好在她手握空間農場,還有系統輔佐,不至于讓家里人餓肚子。可是這一路上,不是遇到哄搶物資的災民,就是窮兇極惡的劫匪,甚至還有殘暴無能的親王……她該如何應對?歷經艱難險阻,得貴人相助,她終于帶著家里人逃荒成功,在異地扎根。但,瘟疫,戰亂等天災人禍接踵而至,民不聊生。無奈之下,她只能幫著整治國家,拯救人民。最后,竟然陰差陽錯的...
26.1萬字8 16090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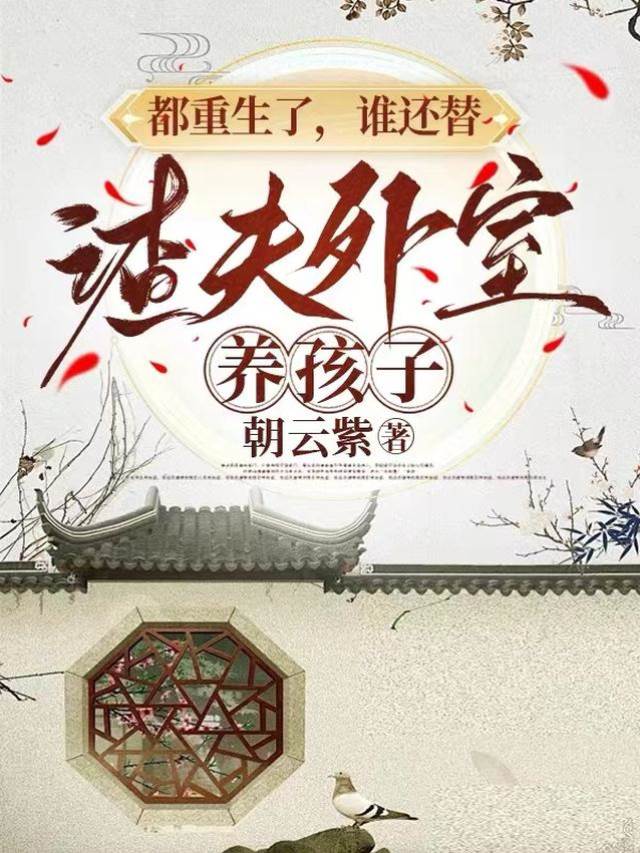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
完結208 章

美艷通房茶又嬌,撩完世子她就跑
全京城都覺得靳世子瘋了!清冷孤高的靳世子,竟然抗旨拒婚,棄權相嫡女於不顧! 坊間傳言,全因靳世子有一房心尖寵,不願讓她受委屈。權相嫡女聽聞,摔了一屋子古董珍玩,滿京城搜捕“小賤人”。 沒人知道,世子的心尖寵,已經逃了。更沒人知道,自從那心尖寵進府,燒火丫頭每晚都要燒三次洗澡水。 遠在揚州的蘇嫿,聽聞此事,在美人榻上懶懶翻了一個身。你幫我沉冤昭雪,我送你幾度春風,銀貨兩訖,各不相欠,你娶你的美嬌娘,我回我的富貴鄉! 至於牀榻上,哄男人說的什麼執迷不悔,非卿不嫁,都是戲談,不會真有人當真吧? 揚州渡口,一艘小船,低調靠岸。靳世子面冷如霜,眼裏波濤暗涌。 蘇嫿!你勾引我時,溫言嬌語,滿眼迷醉。你拋棄我時,捲走黃金萬兩,頭也不回! 這一次,我誓要折斷你的羽翼!把你鎖在身邊!夜夜求寵!
36.3萬字8.18 101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