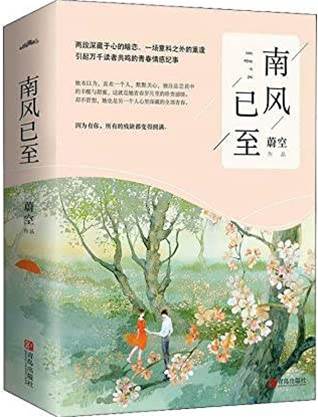《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第23章
蘇毓一怔, 這才一個月不到, 怎麼就要生了?
一般的妖胎孕期至也要三五個月,若是孩子爹修為高, 懷上幾年幾十年都有可能。
十洲三界第一劍修, 運籌帷幄的當世大能連山君,有生以來第一次, 到有些手足無措。
他都顧不上介意這爐鼎要生孩子,竟然放著他一個大活人只當看不見, 向一個假人求助。
小頂倒沒有瞧不起大活人的意思,也不是在和連山君賭氣。
只是親疏有別, 阿亥是好朋友,連山君什麼都不是。
方才那顆蛋忽然從爐子里跑出來, 在肚子里上躥下跳, 弄得一陣劇痛,第一反應自然是向阿亥求助。
不過阿亥一個缺心眼的傀儡人,幫人接生實在不在他的職責范圍之, 只是撓撓頭:“啊呀, 這我也沒生過啊,要不我給你吶喊助威吧。”
蘇毓:“……”
傀儡人氣沉丹田,準備給爐鼎加油鼓勁, 等他一口氣提上來,已經不翼而飛了。
小頂肚子里的蛋蹦跶得越來越歡, 再也坐不住, 慢慢從石凳上下來。
蘇毓也顧不得在乎自己讓人占便宜了, 手把提溜起來,讓靠在自己上:“你忍一忍,我找人來。”
他一手扶著,一手掐訣施,給云中子傳音。
片刻后,耳邊傳來云中子的聲音,周圍人聲鼎沸,十分嘈雜:“小毓啊,找師兄何事?”
蘇毓蹙眉:“師兄在何?”
云中子道:“攝提宗宗主三百大壽,我在華鐘山呢,金竹也在,你有何事?”
蘇毓了眉心,云中子大約每三年出一趟門,這小爐鼎也真是會挑日子,早不生晚不生,偏偏挑在老媽子不在的時候生。
Advertisement
“蕭頂臨盆了。”他撂下一句,利索地掐斷了傳音咒,留下云中子的半截驚呼回在耳邊。
他沒敢耽擱,立即又傳音給歸藏醫館的大夫,誰知唯一一個懂點帶下科的大夫正好放假——因為最近蔣寒秋放下屠刀,立地佛,醫館清閑了不,大夫們趁機把攢了幾年的假都拿出來休。
蘇毓垂眸看了眼靠在他懷中的,臉頰上健康的紅暈已全然褪去,尖尖的小臉比紙還白,只有眼眶是紅的,額頭上沁出的汗流下來,和眼角滲出的淚水混在一,濡了鬢發。
原本鮮滴的櫻紅雙也了。
明明疼這樣,也不哭不,連哼都不哼一聲,只是咬著下。
即便蘇毓對見頗深,心里也有些不舒服。
他咬咬牙,做了一件做夢都不敢相信的事。
蘇毓不不愿地施了個傳音咒,半晌,耳邊才傳來個冰涼刻薄的聲音:“找我何事?”
“蔣寒秋,”蘇毓著鼻子道,“你會不會接生?”
蔣寒秋一怔,隨即冷笑:“蘇毓,你又在耍什麼花樣?”
蘇毓的太突突直跳,他和這師侄大約八字不合,平常說不了三句話就要拔劍,不過垂眸看了一眼懷里的小爐鼎,是把這口氣忍了下來,冷冷道:“蕭頂臨盆了。”
“等等……”蔣寒秋這回是真傻了眼,連妹妹有孕都不知道,怎麼突然就臨盆了?
愣了愣,隨即暴怒:“蘇毓你還是不是人,還是個孩子啊!信不信我今天就殺了你!”
蘇毓差點沒被這一聲吼震聾,耳朵嗡嗡作響。
他從牙中出四個字:“不是我的。”
蔣寒秋“哦”了一聲:“那也是你不對。”
蘇毓:“???”
Advertisement
蔣寒秋:“你別我寶貝,我馬上就到。”
蘇毓冷哼了一聲,兩人幾乎是同時迫不及待地掐斷了傳音咒。
就在這時,的長睫突然。
猛地睜開眼睛,從蘇毓的懷里跳將起來,捂住肚子開始干嘔。
蘇毓有些懵,他自是從未見過人生孩子,但憑著他模糊殘缺的知識,似乎并沒有嘔吐這個環節。
“你怎麼樣?”他的嚨有些發,“蔣寒秋很快就到,再忍片刻。”
蔣寒秋雖然不堪大用,但這一輩就一個徒弟,只能矬子里拔將軍了。
小頂無力地擺擺手,了一口氣,還沒開口,又干嘔起來。
方才這蛋在肚子里竄,似乎是找不到門路出去,便試著引導它,就像在心法課上引導氣在經脈中運行。
連山君教過,從哪兒進去就從哪兒出來,記在心里,便努力把蛋往上引。
沒想到真的有點用。眼下蛋已經到了嚨口,只差一點就能生出來了。
只是蛋的圓頭有點大,有些卡。
深吸了一口氣,氣沉丹田,正準備發力,阿亥突然手在背上一拍。
那蛋力,從嚨里了出來,小頂冷不防一張,一顆外殼紅彤彤,還纏繞著縷縷金的小蛋掉了出來。
蘇毓瞥見那蛋的模樣,不由微怔,這是迦陵鳥蛋,而整個十洲境,只剩下一只迦陵鳥,就在他們歸藏外山。
一時間,他不知道該震驚爐鼎用生蛋,還是該唾棄那只下流無恥的老鳥。
紛繁蕪雜的念頭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過,只是一瞬間的事,然而就因為這一瞬間的愣怔,他錯過了接住蛋的時機。
等他回過神來,那枚小蛋已經“啪嗒”一聲掉在地上。
脆弱的蛋殼“咔嚓”一聲裂兩半,蛋清蛋黃慢慢淌出來。
Advertisement
蘇毓:“……”
小頂打了個嗝。瞪大眼:“我……我的蛋!”這流了一灘,還能撿起來吃嗎?
好不容易生出來的呢!
事態已經完全失控,蘇毓一個只會殺人的劍修,哪里知道怎麼安一個剛生產就失去孩子的母親?
這種時候還是讓傀儡人代勞的好。
蘇毓大方地一揮手,把還給了大淵獻。
傀儡人一拿回,立即指著一片狼藉的鳥蛋道:“那是什麼?”
蘇毓和小頂定睛一看,發現細碎的蛋黃中間,有顆小指指甲蓋大小的小丸子,正閃耀著金紅的芒。
“丹還在,還有救。”蘇毓暗暗松了一口氣,他被這爐鼎哭怕了。
話音未落,忽然有個白影橫躥而來——卻是小頂最后疊的那只紙。
紙的黑豆小眼冒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上來,對著妖丹一啄,脖子一一,便把妖丹吞進了肚子里。
蘇毓:“……”
小頂:“哎?”
就在這時,母一邊長脖子“咯咯咯”地大,一邊發狂似地拍打起短翅膀。
與此同時,金紅芒從它噴涌而出,把它變了一只灼灼燃燒的火球。
它的形隨著芒一起暴漲,很快從一只普通,變了一只兩百斤的。
芒逐漸收斂,原本雪白的羽,被方才的芒染了紅里著金,金里著五彩的絢爛彩,在下流溢彩、璀璨奪目,晃得人眼花繚。
不過這雖然胎換骨,換了一華麗漂亮的,但型態沒有半點改變,還是圓子圓腦袋短翅膀,一雙賊溜溜的黑豆眼嵌在腦袋上。
張了張:“嘰!”
饒是見多識廣的連山君,面對這震撼人心的一幕,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阿亥拍著口:“謝天謝地,母子平安。”
小頂用手背抹抹額頭上的汗,長出一口氣:“生孩子,好難啊!”
蘇毓:“……”
他不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想多了。
畢竟真傻是藏不住的。
傀儡人接著道:“小頂姑娘,該給小公子取個名字啦。”
這可把小頂難住了,歪著頭,盯著:“你想,什麼?”
:“嘰嘰!”
小頂撓了撓腮幫子:“好吧,就你小嘰嘰吧。”
蘇毓:“……”
阿亥眉頭一擰:“這可有點名不副實,恕我直言,小公子的個子其實大的。”
小頂一想,深以為然地點點頭:“那就,大嘰嘰。”
大紅:“?!”
猛扇翅膀:“嘰嘰嘰嘰嘰!”
小頂走過去,踮起腳它的腦袋:“你也,很喜歡吧?”
阿亥:“真是個好名字。我看大嘰嘰公子生得一表人才、眉清目秀,日后肯定大有出息。”
小頂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借你,吉言啦。”
蘇毓:“……”
傀儡人和爐鼎你一言我一語,夾雜著中氣十足的“嘰嘰”聲,蘇毓不覺有些恍惚,仿佛腦袋被人摁進了水里。
就在這時,忽聽“砰”一聲響,院門大開,一黑的蔣寒秋一手提著劍,一手提著只,殺氣騰騰地沖進來:“小頂別怕,我來了!”
小頂粲然一笑:“仙子姐姐,我已經,生完啦。”
蘇毓一見仇人,如夢初醒,瞬間恢復斗志,冷笑一聲,抱著胳膊一挑下頜:“說得好聽,若是等你來,只能給他們母子收尸了。”
蔣寒秋聞言一愣,連蘇毓的冷言冷語都顧不上理會,走到小頂跟前,將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沒事就好。”
轉頭瞪向師叔:“蘇毓你怎麼回事,小頂剛生完孩子,你不讓進屋躺著,讓在這里吹冷風?!”
不等他說話,接著道:“回頭一并和你算賬!”
“快回屋躺著,姐姐帶了只百歲老母,一會兒給你燉湯補,”一邊說一邊環顧四周,“孩子呢?”
小頂指著大紅:“就是他。”
蔣寒秋方才一進門就看見了這只怪,還以為是蘇毓從哪里弄來的妖禽。
此刻,看看手里的老母,又抬頭看看兩百斤的大紅,陷了深深的沉默。
半晌,方才艱難地出一個微笑:“看著,倒是健壯的……孩子父親,似乎不是人吧?”
沒等小頂說話,那大紅里響起個清脆的年聲音,還帶著點味兒:“蘇毓,好你個孫子嘰,竟然趁著爺爺換玩這種招嘰!有種明正大單挑嘰!”
蘇毓一怔,這聲音雖有些陌生,但語氣他是得不能再了。
他蹙了蹙眉:“迦陵?”
猜你喜歡
-
完結71 章

就想把你寵在心尖上
許真真是南城公子哥沈嘉許寵在心尖上的小女友,身嬌體軟,長得跟小仙女似的。 許真真跟沈嘉許分手的時候, 他不屑一顧,漫不經心的吸了一口煙,略帶嘲諷的口吻說, 你被我悉心照料了這麼久,回不去了,要不了一個月,你就會自己回來,主動抱著我的大腿,乖乖認錯。 直到多日后,沈嘉許在校園論壇上,發現許真真把他綠了一次又有一次。 晚會結束后,沈嘉許把許真真按到了黑漆漆的角落里,鎖上門,解開扣子,手臂橫在墻上,把小女人禁錮在了自己的臂彎里,他的眼眸波光流轉,似笑非笑。 許真真的肩膀抖了抖,咽了咽口水,睫毛輕顫。 “當初不是說好,我們和平分手嗎?” 沈嘉許淡笑,手指劃過許真真柔軟馨香的臉蛋,陰測測威脅。 “要分手可以,除非我死。” PS:虐妻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19.5萬字8 18929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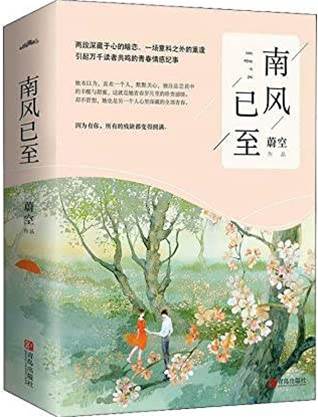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39 章

從替身到白月光
【男二上位,前任火葬場】 林鳶跟了沈遇傾三年。 他用冷漠和薄涼教會她懂事和順從。 直到她看見了一個黑白相框,照片里的女人,跟她長得一模一樣。 林鳶終于放下了三年來的執念,轉身離開。 沈遇傾卻只是挑挑唇,淡漠又從容,“她離開我活不下去的。” —— 在別墅外,林鳶目光停留在一個消瘦且滿身血痕倒在泥濘中的少年身上。 他美得近乎妖孽,白瓷一般的小臉,濃黑眼睫低垂,滿是柔弱感。 林鳶當即走過去,從幾個流浪漢手里救下了他。 起初,美少年總是陰鷙著一張臉,一言不發。 不管她對他多麼悉心照顧,都換不來他一個笑臉。 他傷好的那天,林鳶摸摸他的頭有些不舍地說:“你自由了。” 美少年眼里氤氳了霧氣,死死抓著她的手不放,“你不要我了?” —— 沈家真正的掌權人,沈遇傾的小叔叔闊別三年,終于重回家族。 為此,沈家舉辦了隆重宴會,恭迎這位憑借一己之力撐起沈氏家族的沈燃。 所有人都知道沈燃殺伐果決,掌控欲極強,沒人能違抗他的話。 就連沈遇傾都要在他身后畢恭畢敬。 卻有人在宴會角落發現,一個嬌美女人驕橫地瞪著沈燃。 而他收斂了一身的傲氣,低聲哄道:“下次不敢了。” —— 沈遇傾沒想到會在宴會上碰到一直找不見的林鳶。 他抓住她的手腕,咬牙切齒道:“聽話,跟我回家。” 林鳶揚眉一笑:“沈先生,請自重。” 傳說中的沈燃一身白色西裝翩翩而至,將林鳶擋在身后。 強而有力的修長手指,生生將沈遇傾的手腕掰開來,眸子里的陰鶩一閃而逝,嘴角似笑非笑的勾起,語氣沉穩卻不羈。 “遇傾,叫小嬸嬸。” 沈遇傾:“?” 林鳶:“?……告辭” 沈燃一秒恢復了往日的嬌弱,拉住要逃走的林鳶,松軟的短發蹭了蹭她的臉頰,漂亮的眼里一片純良。 “姐姐,往哪走啊?” #病弱小奶狗竟然是腹黑大boss# #我成了前男友的嬸嬸# #追不上的追妻火葬場# 1v1,雙C ————
18.1萬字8 16780 -
完結371 章

惑君
嫡姐嫁到衛國公府,一連三年無所出,鬱郁成疾。 庶出的阿縈低眉順眼,隨着幾位嫡出的姊妹入府爲嫡姐侍疾。 嫡姐溫柔可親,勸說阿縈給丈夫做妾,姊妹共侍一夫,並許以重利。 爲了弟弟前程,阿縈咬牙應了。 哪知夜裏飲下嫡姐賞的果子酒,卻倒在床上神志不清,渾身似火燒灼。 恍惚間瞧見高大俊朗的姐夫負手立於床榻邊,神色淡漠而譏諷地看着她,擡手揮落了帳子。 …… 當晚阿縈便做了個夢。 夢中嫡姐面善心毒,將親妹妹送上了丈夫的床榻——大周朝最年輕的權臣衛國公來借腹生子,在嫡姐的哄騙與脅迫下,阿縈答應幫她生下國公府世子來固寵。 不久之後她果真成功懷有身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嫡姐抱着懷中的男娃終於露出了猙獰的真面目。 可憐的阿縈孩子被奪,鬱鬱而終,衛國公卻很快又納美妾,不光鬥倒了嫡姐被扶正,還圖謀要將她的一雙寶貝兒女養廢…… 倏然自夢中驚醒,一切不該發生的都已發生了,看着身邊沉睡着的成熟俊美的男人,阿縈面色慘白。 不甘心就這般不明不白地死去,待男人穿好衣衫漠然離去時,阿縈一咬牙,柔若無骨的小手勾住了男人的衣帶。 “姐夫……” 嗓音沙啞綿軟,梨花帶雨地小聲嗚咽,“你,你別走,阿縈怕。” 後來嫡姐飲鴆自盡,嫡母罪行昭彰天下,已成爲衛國公夫人的阿縈再也不必刻意討好誰,哄好了剛出生的兒子哄女兒。 形單影隻的丈夫立在軒窗下看着母慈子孝的三人,幽幽嘆道:“阿縈,今夜你還要趕我走嗎?”
61.6萬字8 10053 -
完結294 章

死后宿敵給我燒了十年香
大魏皇后沈今鸞死前,恨毒了大將軍顧昔潮。 她和他少時相識,爲家仇血恨鬥了一輩子,她親手設局將他流放北疆,自己也油盡燈枯,被他一碗毒藥送走。 生前爲了家國殫精竭慮,她死後卻被污爲妖后,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不入皇陵,不得下葬,連墳頭都沒有。 若非不知誰人供奉的三炷香火,早已魂飛魄散。 直到一日,大雪紛飛,她顛沛流離的魂魄又逢顧昔潮。 十年未見,當初所向披靡的戰神,甲裳破舊,爲人追殺,窮途末路。 同樣走投無路的鬼皇后幽然現身,血污斑斑的寡白羅衣拂過大將軍磨鈍的刀鋒: “我執念未了,不得往生,想和將軍做個交易。” 卻沒想到,交易達成之後,這位冷心冷情的昔日宿敵,會不惜一切,入京都,爲她報仇雪恨,得以往生。 *** 顧昔潮出身簪纓世家,少時成名,半生輕狂,位極人臣,權傾天下。 所以,無人不嘆惋,他被那妖后害得身敗名裂,在極盛之時背棄所有,遠走北疆,一世伶仃。 顧將軍不事神佛,不信鬼魂。 可每逢大雪,將軍總會燃三炷香火,供於那妖后的靈位前。 雪夜焚香十載,枯等一縷孤魂歸來。 而最後,在他深陷敵陣,瀕死之際,也是那縷孤魂—— 她早已沉冤得雪,卻未去往生, 仍是一身素衣帶血,踏過屍山血海,爲他招來千萬陰兵,千里相救。 他戰至力竭,肩甲浸赤,沉聲相問: “還有執念未了?” “有的。” 她拂去他面上血污,含笑道, “想請將軍,爲我燃一生一世的香火。”
44.6萬字8 25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