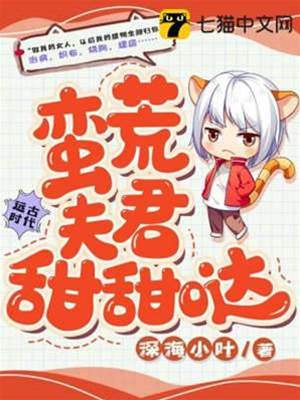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囚雀》 5、第 5 章
沈邵下了早朝,乘輦返回門,路上忽想起什麼來,轉頭問邊的王然:“可求到藥了?”
前首領太監王然聽到問,忙上前兩步靠近龍輦,仰頭答:“已經好幾日了…長公主連肅王府的門都沒進去。”
沈邵聽了,再沒說什麼。
王然暗暗打量沈邵的面,未瞧出什麼變化,以為此事揭過,卻不想快到門時,沈邵突然開口,要去庫房走一趟,王然先是一愣,后忙命人調頭。
沈邵親自去了庫房,將還魂丹尋出來。
王然規矩立在沈邵后,見他站在窗前,手握著還魂丹出神,不開口:“陛下是想…將這藥賜給長公主嗎?”
王然話剛出口,便聽沈邵冷笑一聲,側過頭瞧了他一眼。
過窗紙打在沈邵上,他半張臉逆在影里,王然看見沈邵瞥看來的目,頓時周一,心底打鼓。
“啪”的一聲響,震在王然耳里,嚇得他子暗暗一抖。
沈邵將手中的藥匣收合上,單手握著,背在后,離開了庫房。
***
永嘉乘馬車抵達皇宮時已至下午,天霧靄,門下的石階不知何時灑了水,結了層薄薄的霜。
永嘉在殿外求見沈邵。
王然走進去又很快出來,對永嘉一禮:“殿下請回吧,陛下不見。”
似乎是意料中的結果,永嘉低垂著眉眼,聞言什麼都沒說,只提起擺,直跪了下去。
王然見此,搖頭嘆了口氣。
他現下其實心里也有點糊涂,按理說陛下是絕不會將藥給淑太妃的,可為何今日晌午又親自跑去庫房將藥取了出來呢。
永嘉在門外跪到日落,后來殿掌起了燈,天際皆黑了,空中無星無月滿是云,冷風席卷,吹著屋廊下的燈籠‘咯吱咯吱’的作響。
Advertisement
王然又進了一次殿,出來時將永嘉扶起,攙著慢慢過殿前的門檻,看著走進去,才關上了門。
永嘉有些發,一步一步緩慢的走,進去見前殿無人,便順著亮朝后殿尋去,穿過略有昏暗的房廊,眼前復亮起來。
永嘉走到屋門前,正見里面的宮人伺候沈邵寬,腳步一停,低了下頭。
沈邵看見站在門外久不的,瞇了瞇眸:“進來。”
永嘉聞言,沒再遲疑,踏過門檻,朝屋走去,在沈邵不遠不近站定,忍著膝蓋的疼,規矩行了個禮。
“剛才在外頭跪著不走的時候,倒是有主意,現在怎了啞?”沈邵見永嘉還默默杵在那不說話,他抬了抬手,邊伺候的宮人們停下作,垂頭退了下去。
永嘉低垂著眸,見宮人們的擺從自己旁劃過,待聽腳步聲遠了,慢慢抬起頭。
幾步外的沈邵解了腰帶,袍寬松著,比平日里多了幾分慵懶閑適,永嘉著他,不敢輕易開口。
進宮前,已將今晚視做死局,著實再想不到自己于沈邵還有什麼籌碼,甚至不但沒有籌碼還有把柄。
的命在他的一夕之間,救命的藥也在他的一夕之間。
“陛下…臣想求您賜一顆還魂丹。”
永嘉話落,倒是先聽見沈邵笑了笑:“怎麼,一支釵子,長公主想從朕這換走多東西?”
連忙搖頭,急切的著他,想要解釋,可還未開口,眼睛驀然就紅了,又慌忙的低下頭躲閃,眼淚還是沒能藏住,一顆一顆的掉下來。
永嘉哭了:“行堯…求求你了…求你了……”
殿的燈火浸染在漆黑夜里,沈邵垂眸沉沉的看永嘉,燭掩映著面龐的蒼白,此刻瞧上去,教人可憐又可憐。
Advertisement
沈邵朝永嘉走了兩步,他長立在面前,抬手上尖瘦的下,輕輕托起,他一不的看著,眸底深邃如淵,似乎藏著波濤洶涌。
的淚落下,了他的指尖。
沈邵的眸子了,他抬手,略帶糲的指腹稍有用力的蹭著的臉頰,蹭掉上面的淚,留下一抹生疼。
永嘉到沈邵的作,先是一愣,接著心頭發酸,一時間淚掉得更厲害。
“阿姐有多久沒替朕梳過頭發了?”沈邵著的淚,忽然開口:“伺候朕寬吧。”
長夜深寂,窗外的風吹不殿的火燭,暗暖的漫延了滿室。
永嘉靠近沈邵,蔥白的指尖劃過山巒起伏的紋路,上他的領,解開肩上的扣子,替他一件件-掉外裳,從他前繞到后再回到前,鼻息間皆是他衫上的淡淡檀香。
第一次聞到他上有香。
永嘉將-下的服仔細疊起放好,抬起頭時,沈邵已坐在臺鏡前等。
永嘉走過去,站到他的背后,他們的目在銅鏡中短暫匯,有些局促,永嘉先低下眸,抬手將沈邵發間的玉簪掉,將他的發髻一點一點松散開,握著梳子,將他-的頭發一點一點梳通,他這發像極了他這倔強的子。
永嘉一邊替沈邵梳發,一面不由憶起小時候,他最喜歡的就是大早上披頭散發跑到房里,央求著給他束發。
只因有一日早上忽然興起,親手幫沈桓梳了頭發,宮人都夸好看,桓兒更是洋洋得意,跑到學堂與眾兄弟炫耀一番,許是教沈邵聽到了,至此每天早上都要跑來找,若不給他束發,他便賴著不去學堂。
后來這事教何皇后知道了,皇后一向不喜歡母妃,順帶著不喜歡,見沈邵日往母妃宮中跑,大概深宮孤獨,又只有沈邵一個兒子,患得患失,護子心,一日沈邵從房中剛走,皇后突然前來,不待開口請安,先狠甩了兩掌,大罵庶子卑劣,壞嫡子。
Advertisement
殿燭火跳躍,晃了永嘉的眼,一時回神,抬眸見鏡中的沈邵正一眨不眨的看著。
永嘉收了手,移上前,將梳子放置案上,正向后退去,手腕忽被沈邵用力握住。
永嘉不解,見沈邵仰眸看過來,似是在笑,問:“想好要如何求朕了嗎?”
永嘉聞言怔了一怔,著沈邵依舊冷清的目,漸漸反應過來,心底才存的暖意,頃刻間便散了。
本以為,他是心了,他讓幫忙梳發,是還念著點曾經的誼,愿意幫此番…但原來,并不是。
沈邵執著于文思皇后的死,他認定是母妃害了皇后,就像沒辦法勸他相信文思皇后的死只是個意外,也沒有辦法勸他寬恕,如果一定要泄恨,便一命抵一命吧。
永嘉著腕上的那抹疼,垂低眉目:“陛下若開恩…臣愿意替母妃去死。”
話落,整個殿霎時寂靜,沒去看沈邵的表,只是清晰的到腕上的力道在不斷加重,像是要將折斷。
沈邵盯著永嘉,盯著此刻波瀾不驚的眉目,有時候,他真恨不能殺了。
沈邵忽然起,高大的影下來,他盯著永嘉那張臉,幾近咬牙切齒的罵:“你們母的賤-命就算加起來,也賠不起朕母后…你還要替去死,你信不信朕馬上就能讓你死?”
永嘉自然是信的。
“那陛下如何才肯將藥賞給臣呢。”看不懂今夜的沈邵,他若不想,大概不會教踏進門一步,可他若愿意,已將的命都給他了,他為何還不肯點頭。
沈邵聽見這問,懷中掀起的怒意忽沒了一半,他凝視著永嘉瞧了半晌,忽擒著的腕,將纖細的手臂別到背后,手上用力,將-到懷中來,順勢向下,環住的纖腰,如斯弱小,他只需單臂便將穩穩錮住。
沈邵只覺懷中涌一抹愉悅的香,這縷香與那些名貴的香料不同,這捧與那些錦被帛枕亦不同。
他見又驚又懵的模樣,反倒笑起來,垂頭近的耳畔,在纖細的玉頸間留下一抹燙。
“你若肯伺-候朕,朕便將藥給你。”
永嘉聞言懵了,雙眸怔怔看著沈邵,待反應過來,拼命從他懷中掙開,急急向后退了數步,懷中起伏,瞪著他,驚得說不出話來。
沈邵眼瞧著永嘉這般激烈的反應,面上皆是冷漠,反問:“這是不肯了?”
“你瘋了!我是你姐姐!”永嘉不住的搖頭,不敢相信,方才那句話,是沈邵說的,對說的。
他聽了,嗤笑一聲:“掛個名而已,還當自己是皇室脈呢。”
永嘉幾乎是逃出殿的,沈邵沒有攔,跑過長廊,跑到外殿,用力推開殿門,王然的臉出現在眼前。
他有些詫異:“殿下…您…您這是……”
永嘉氣息不定,看著攔在前的王然,忽抬手推開他,大步跑出門。
永嘉跑下臺階,迎面打來的是冰冷的雨,細的雨像是一張網,籠罩過來,要將溺-死似的。
王然站在殿上,見永嘉頭也不回的冒雨跑出去,不知是發生了何事,他左右尋傘想著人給送去,卻一時找不到,再一抬頭,暮夜雨中已不見了永嘉的影。
永嘉迎著雨,一步步向宮外走,今日,才徹底明白,沈邵變了,變得面目全非,不肯舍的年誼,皆是可笑妄念,他們,永遠也回不到過去。
冷雨將淋,除了裳,除了子,連著心一并也冷了。
宮墻甬道,又深又長,走不到盡頭似的,永嘉開始跑,又摔倒,爬起來繼續跑,再摔倒,放聲大哭,被這傾盆夜雨掩蓋住了所有聲音,像極了會被溺死的魚,進不能退不得,的生路也是死路。
許久,永嘉從地上爬起來,不再向前走,而是慢慢轉,回首去,天地風雨,百年宮殿的最中央,無垠夜下,燈火最明亮,是宮中門。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法醫娘子狀元夫
我的接檔存稿文《重生之公府表小姐》[11月17日開坑,男主忠犬甜寵偽表哥] 現代女法醫曲明姝穿回北宋,嫁給神童狀元晏子欽,從此: ①大忽悠屬性全開,把小丈夫騙的近不了身還團團轉。 ②法醫金手指全開,小丈夫一改高冷臉,五體投地求指教。 ③歷史金手指全開,知道大體走向,規避官場風險。 當①②③都做到時,明姝驚恐地發現,小丈夫長大了,賤笑著磨“刀”霍霍向媳婦…… 曲明姝曾對天許愿:“請神賜予我一個像霍建華一樣盛世美顏,像孫楊一樣八塊腹肌,像花滿樓一樣溫柔儒雅的男子。” 于是,她收獲了一枚像霍建華一樣老干部,像孫楊一樣逗比兒童歡樂多,像花滿樓一樣“目空一切”的晏子欽。 曲明姝:?????? 作者有話說: 0. 排雷:男女主十五歲結婚,但最開始一段時間什麼也沒發生。女主吐槽帝。部分尸體描寫不適宜用餐時間觀看。女主內心狂野,外表矜持。男主技能點全加在讀書從政上了,缺乏生活常識。 1. 本文半架空北宋,作者希望盡量貼近歷史,法醫部分查了資料,但是沒有十分的自信,所以謝絕考據,謝絕追究法醫相關描寫的真實性/(ㄒoㄒ)/~~ 2. 如果喜歡這篇文,請收藏吧!作者謝過了,小天使們能收藏對作者來說就是很大的激勵了! 3. 作者小窒息,謝絕扒榜! 4. 作者愛你們~~~留評隨機發紅包~~~
26.5萬字8.18 13248 -
完結81 章

天生撩人
梅幼舒生得嫵媚動人,在旁人眼中:心術不正+狐貍精+禍水+勾勾搭搭=不要碧蓮! 然而事實上,梅幼舒膽子極小,只想努力做個守禮清白的庶女,希望可以被嫡母分派一個好人家去過活一世。有一日君楚瑾(偷)看到她白嫩嫩的腳,最終認定了這位美豔動人的小姑娘果然如傳聞中那般品性不堪,並且冷臉上門將她納為了妾室。 梅幼舒驚恐狀(聲若蚊吟):「求求你……我不要你負責。」 君楚瑾內心os:欲迎還拒?果然是個高段位的小妖精。梅幼舒:QAQ 婚後每天都被夫君當做黑心x做作x惡毒白蓮花疼愛,梅幼舒表示:我TM是真的聖母白蓮花啊! 精短版本:小嬌花默默過著婚前被一群人欺負,婚後被一個人欺負日子,只是不知不覺那些曾經欺負過她的人,都漸漸地匍匐在她腳旁被迫要仰視著她,然而幾乎所有人都在心底等待著一句話的應驗—— 以色侍君王,色衰而愛弛! 瑟瑟發抖小兔嘰vs衣冠楚楚大惡狼 其他作品:無
25.8萬字8.25 26644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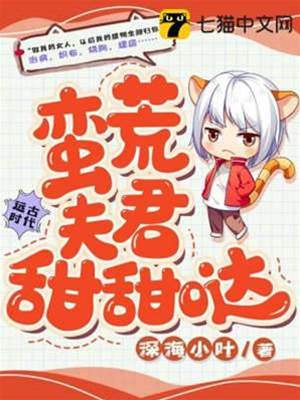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連載2267 章

權臣寵妻媳婦兒是個小錦鯉
趙錦兒是十裡聞名的掃把星,被迫嫁給一個病鬼。大家都以為這兩口子到一起要完,不想過門後老秦家卻好運連連,日子是越過越紅火。進山挖野菜撿到狐貍;路邊買頭老羊,老羊肚裡帶著四隻羊崽;就連被采花賊擄走都能帶輛驢車逃回家......而眉目俊朗的病相公也恢複健康,成了攝政王?鄰國公主要來和親,相公大手一揮,“家有嬌妻,這輩子不娶妾!”
187.2萬字8 126703 -
完結1320 章
毒醫小狂妃
21世紀的醫學界天才少女,中西醫雙強,年紀輕輕就拿遍國際醫學大獎的葉小小,誰都沒想到,她竟然因為追星……意外摔死了!醫學界嗷嚎大哭,男色誤人……一場穿越,葉小小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晉國公府的嫡女葉夭夭,從此醫術救人,毒術防身,吊打一群渣渣!哎……等等,那個美太子,你站住!我這不是追星,我這是愛情!
235.8萬字8 535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