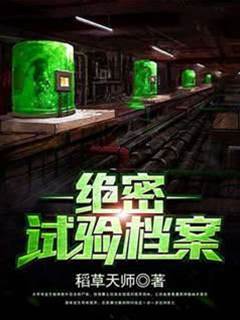《血字的研究》 十三、再錄華生回憶錄
我們的罪犯瘋狂的抵抗顯然並不是對於我們每個人有什麼惡意,因為當他發覺他已無能為力的時候,便溫順地微笑起來,並且表示,希在他掙扎的時候,沒有傷害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他對福爾斯說:「我想,你是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去的。我的馬車就在門外。如果你們把我的鬆開,我可以自己走下去上車。我可不是象從前那樣那麼容易被抬起來的。」
葛萊森和雷斯垂德換了一下眼,似乎認為這種要求太大膽了些。但是,福爾斯卻立刻接了這個罪犯的要求,把我們在他腳腕上捆紮著的巾解開了。他站了起來,把兩條舒展了一下,象是要證明一下,它們確實又獲得了自由似的。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我瞧著他的時候,一面心中暗想,我很見到過比他更為魁偉強壯的人了。飽經風霜的黑臉上表現出的那種堅決而有活力的神,就象他的力一樣地令人驚異和不可忽視。
他注視著我的同伴,帶著衷心欽佩的神氣說:「如果警察局長職位有空缺的話,我認為你是最合適的人選了。你對於我這個案子的偵查方法,確實是十分謹慎周的。」
福爾斯對那兩個偵探說道:」你們最好和我一塊兒去吧。」
雷斯垂德說:「我來給你們趕車。」
「好的,那麼葛萊森可以和我們坐上車去。還有你,醫生。你對於這個案子已經發生了興趣,最好也和我們一塊走一遭吧。」
我欣然同意了,於是我們就一同下了樓。我們的罪犯沒有一點逃跑的企圖,他安安靜靜地走進那個原來是他的馬車裏去,我們也跟著上了車。雷斯垂德爬上了車夫的座位,揚鞭催馬前進,不久,便把我們拉到了目的地。我們被引進了一間小屋,那裏有一個警把我們罪犯的姓名以及他被控殺死的兩個人的姓名都記錄了下來。這個警是個面白皙、神冷淡的人,他機械而呆板地履行了他的職務。他說:「犯人將在本周提法庭審訊。傑弗遜·侯波先生,你在審訊之前,還有什麼話要說嗎?但是我必須事先告訴你,你所說的話都要記錄下來,並且可能用來作為定罪的據的。」
Advertisement
我們的罪犯慢慢地說道:「諸位先生,我有許多話要說,我願意把它原原本本地都告訴你們。」
這個警問道:「你等到審訊時再說不更好嗎?」
他回答說:「我也許永遠不會到審訊了呢,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我並不是想要自殺。你是一位醫生麼?」他說這句話時,一面把他的兇悍而黧黑的眼睛轉過來瞧著我。
我說:「是的,我是醫生。」
「那麼,請你用手按一個這裏。」他說時微笑了一下,一面用他被銬著的手,指了一下口。
我用手按按他的部,立刻覺察到裏邊有一種不同尋常的跳。他的腔微微震,就象在一座不堅固的建築中,開了一架強力的機平時的形一樣。在這靜靜的屋中,我能夠聽到他的膛裏面有一陣輕微的噪雜聲音。
我道:「怎麼,你得了脈瘤癥!」
他平靜地說:「他們都這樣說。上個星期,我找了一位醫生瞧過,他對我說,過不了多天,瘤就要破裂。這個病已經好多年了,一年比一年壞起來。這個病,是我在鹽湖城大山之中,由於飽經風霜,過度勞,而且又吃不飽的緣故所引起的,現在我已經完了我的工作,什麼時候死,我都不在乎了。但是,我願意在死以前,把這件事代明白,死後好有個記載。我不願在我死後讓別人把我看是一個尋常的殺人犯。」
警和兩個偵探匆忙地商量了一下,考慮準許他說出他的經歷來是否適當。
警問道:「醫生,你認為他的病確實有突然變化的危險嗎?」
我回答說:「確是這樣。」
這位警於是說道:「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了維護法律起見,顯然,我們的職責是首先取得他的口供。先生,你現在可以自由代了。不過,我再一次告訴你,你所代的都要記錄下來的。」
Advertisement
「請允許我坐下來講吧。」犯人一面說,一面就不客氣地坐了下來,「我的這個瘤癥很容易使我到疲乏,何況半個鐘頭以前,我們鬥爭了一番,這絕不會使病有所改進。我已經是墳墓邊上的人了,所以我是不會對你們說謊的。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千真萬確的。至於你們究竟如何置,這對我來說,就無關要了。」
傑弗遜·侯波說完這些話以後,就靠在椅背上,開始說出了下面這篇驚人的供詞。他敘述時的態度從容不起,並且講得有條有理,好象他所說的事十分平淡無破。我可以保證,這起補充供詞完全正確無誤,因為這是我乘機從雷斯垂德的筆記本上抄錄下來的。他是在他的筆記本中,把這個罪犯的供詞按照他原來的說法,逐字逐句地記錄了下來的。
他說:「我為什麼要恨這兩個人,這一點對於你們說來,是無關要的。他們惡貫滿盈,他們犯了罪,害死過兩個人——一個父親和一個兒,因此他們付出了他們自己的命,這也是罪有應得的。從他們犯罪以來,時間已經隔了這麼久,我也不可能提出什麼罪證,到任何一個法庭上去控告他們了。可是,我知道他們有罪,我打定主意,我要把法、陪審員和行刑的劊子手的任務全部由我一個人擔當票來。如果你們是男子漢大丈夫,如果你們站在我的地位上,你們一定也會象我這樣乾的。
「我剛才說到的那個姑娘,二十年前本來是要嫁給我的,可是卻被迫嫁給了這個錐伯,以致使含恨而死。我從的手指上把這個結婚指環取了下來,當時我就發過誓,我一定要讓錐伯瞧著這隻指環斃命;還要在他臨死的時刻,讓他認識到,是由於自己所乾的罪惡,才到了懲罰。我萬里迢迢地踏遍了兩大洲,追蹤著錐伯和他的幫兇,一直到我追上了他們為止,這隻戒指都一直帶在邊。他們打算東奔西跑,把我拖垮;但是,他們是枉費心機。即使我明天就死——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在我臨死的時候,我總算知道了:我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作已經完了,而且是出地完了。他們兩個人已經死了,而且都是被我親手殺死的,此外,我就再也沒有什麼別的希和要求了。
Advertisement
「他們是有錢的人,而我卻是一個窮蛋。因此,我要到追趕他們,這件事對我說來並不容易。當我來到倫敦城的時候,我已經差不多是囊空如洗了。當時我發覺,我必須找個工作,維持我的生活。趕車、騎馬對我來說,就是象走路一樣的平常。於是我就到一家馬車廠去找點工作,立刻就功了。每個星期我要向車主繳納一定數目的租金,剩下的就歸我自己所有。但是,剩餘的錢並不多,可是我總是設法勉強維持下去。最困難的事是不認識道路。我認為在所有道路複雜的城市中,再沒有比倫敦城的街道更複雜難認的了。我就在旁帶上一張地圖;直到我悉了一些大旅館和幾個主要車站以後,我的工作才幹得順利起來。
「過了好久,我才找到這兩位先生居住的地方。我東查西問,直到最後我在無意之中上了他們。他們住在泰晤士河對岸坎伯韋爾地方的一家公寓裏。只要我找到了他們,我知道,他們就算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已經蓄了鬍鬚,他們不可能認出我來。我地跟著他們,待機下手。我下定決心,這一次絕不能再讓他們逃。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幾乎又溜掉了。他們在倫敦走到哪兒,我就形影不離地跟到哪裏。有時我趕著馬車跟在他們後邊,有時步行著。然而趕著馬車卻是最好的辦法,因為這樣他們就無法擺我了。只有在清晨或者在深夜我才做點生意,賺點錢,可是這樣一來我就不能及時向車主繳納租金了。但是,只要我能夠親手殺死仇人,別的我都不管了。
「但是,他們非常狡猾。他們一定也意識到,可能有人會追蹤他們,因此他們決不單獨外出,也絕不在晚間出去。兩個星起以來,我每天趕著馬車跟在他們後面,可是我一次也沒有看見他們分開過。錐伯經常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斯坦節遜卻從來毫不疏忽。我起早黑地窺伺著他們,可是總遇不到機會。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失,因為我總覺到,報仇的時刻就要來到了。我唯一擔心的卻是我口裏的這個病,說不定它會過早地破裂,使我的報仇大事功虧一簣。
「最後,一天傍晚,當我趕著馬車在他們所住的那條做陶爾魁里的地方徘徊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一輛馬車趕到他們住的門前。立刻,有人把一些行李拿了出來,不久,錐伯和斯坦節遜也跟著出來,他們一同上車而去。我趕催馬加鞭跟了上去,遠遠地跟在他們後邊。當時我到非常不安,唯恐他們又要改變住。他們到了尤斯頓車站,下了馬車。我找了一個小孩替我拉住我的馬,我就跟著他們走進了月臺。我聽到他們打聽去利浦的火車;站上的人回答說,有一班車剛剛開出,幾個鐘頭以不會再有第二班車了,斯坦節遜聽了以後,似乎很懊惱,可是錐伯卻比什麼都要高興。我夾雜在人群之中,離他們非常近,所以我可以聽到他們之間每一句談話。錐伯說,他有一點私事要去辦一下,如果斯坦節遜願意等他一下的話,他馬上就會回來。他的夥伴卻攔阻他,並且提醒他說,他們曾經決定過彼此要在一起,不要單獨行。錐伯回答說,這是一件微妙的事,他必須獨自去。我聽不清斯坦節遜又說了些什麼,後來只聽見錐伯破口大罵,並且說,他不過是他僱用的僕役罷了,不要裝腔作勢地反而指責其他來。這樣一來,這位書先生討了一場沒趣,只好不再多說,他只是和他商量,萬一他耽誤了最後的一班火車,可以到郝黎代旅館去找他。錐伯回答說,他在十一點鐘以前就可以回到月臺上來;然後,他就一直走出了車站。
「我日夜等待的千載難逢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我的仇人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可以彼此相助;但是,一旦分開以後,他們就要落到我的掌握之中了。雖然如此,我並沒有鹵莽從事。我早已定下了一套計劃:報仇的時刻,如果不讓仇人有機會明白究竟是誰殺死了他;如果不讓他明白為什麼要到這種懲罰;那麼,這種復仇是不能令人稱心滿意的。我的報仇計劃早就安排妥當,據這個計劃,我要讓害苦了我的人有機會能夠明白,現在是他惡貫滿盈的時候了。恰巧,幾天以前有一個坐我的車子在布瑞克斯頓路一帶查看幾房屋的人,把其中一的鑰匙落在我的車裏了。他雖然當天晚上就把這個鑰匙領了回去,但是,在取走以前,我早就把它弄下了一個模子,而且照樣配製了一把。這樣一來,在這個大城市中,我至找到一個可靠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地干我的事,而不致到阻礙。現在要解決的困難問題就是如何把錐伯弄到那個房屋中去了。
「他在路上走著,並且走進一兩家酒店中去。他在最後一家酒店中,幾乎停留了半個鐘頭。他出來的時候,已是步履蹣跚,顯然他已醉得夠勁了。在我的前面恰好有一輛雙小馬車,於是他就招呼著坐了上去。我一路地跟著。我的馬的鼻子距離前面馬車的車夫的最多只有一碼遠。我們經①過了鐵盧大橋,在大街上跑了好幾英里路。可是,使我到詫異的是,我們竟然又回到了他原來居住的地方。我想像不出,他回到那裏去究竟是想幹些什麼。但是,我還是跟了下去,在距離這所房屋大約一百碼的地方,我便把車子停了下來。他走進了這座房子,他的馬車也就走開了。請給我一杯水,我的都說幹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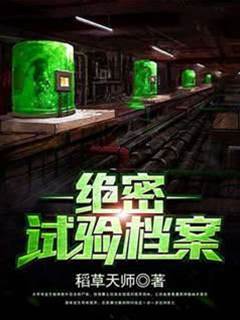
絕密試驗檔案
大學畢業生鮑帥意外目擊碎屍案,但報警之後案發現場卻詭異消失,之後他更是遭到神秘兇手襲擊,身體發生可怕變異,在獲得力量的同時也正一步一步邁向死亡。保護自己的警察突然變成了監視自己的眼睛,重重監視之下突然出現詭異字條,兇案現場出現的神秘標記竟然涉及六十年前的失蹤大案。鮑帥意識到眼前的事情絕不簡單,他必須自救!憑藉變異所得的力量一路追查,與死神賽跑,終於發現一切都源於一場恐怖的絕密試驗……
98.1萬字8 1220 -
連載179 章
張公案
禮部侍郎蘭玨偶遇窮試子張屏,引出張屏從窮書生到小吏最後官至丞相的亂七八糟的人生……
43.2萬字8 935 -
連載257 章

高校之洛清寧
洛清寧重生了,也聰明清醒了,原來,蕭然從來沒有愛過她。聽說蘇雲青來了華市,他身無分文,不帶任何資源,說是要做一個普通人……華大危機謎團四起,洛清寧決定相信蘇雲青,開啟飛一般的人生。
43.2萬字8 896 -
連載334 章
狐祭女
我家後院有三口口棺材,我們一家皆因它而死……十八歲那年,我打開了院裏的一口棺材后,無盡的怪事接踵而來……
45萬字8 7327 -
完結676 章
基本演繹法則
这是一个破碎的时代。 灰雾笼罩,异端降临。 畸形的血肉怪物拼命挣脱机械躯壳,在粘黏的钢铁内嘶吼,在迷乱的霓虹下爬行。 …… 江城在十二月的严寒中醒来,眼前模糊朦胧。 滴答水声作响,他被绑在浴缸里,花洒缓慢放水,水面已经淹到了下巴。 “距离被淹死还有大概二十分钟。” 这片区域每天都会死很多人。 江城算了算剩下的时间,安然躺在浴缸里,开始按照流程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160.9萬字8 609 -
完結55 章

絕品鑒寶師
蘇南天,因為一次被教訓的經歷獲得了異能。從此,價值連城的古玩珍寶,精妙絕倫的書貼字畫,璀璨奪目的天價翡翠,一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此過程中,財富和美女接踵而至,而他也最終成了一名大收藏家!
14.5萬字8 4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