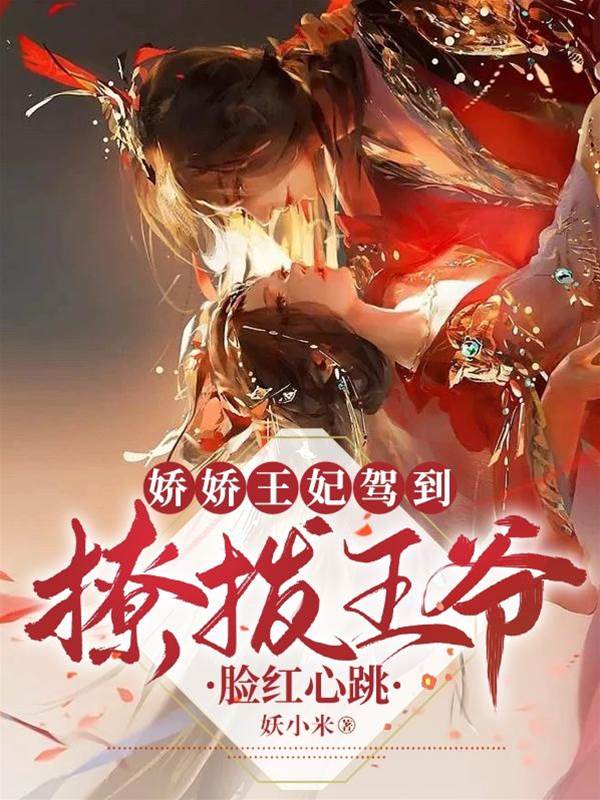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被庶妹替嫁后》 第11章 第十一章
白家府邸的宅子本是前朝忠臣白啟良的居所,□□大赦之際,這位前朝忠臣自刎在府上,追隨而去的亦有妻仆從。
韓祎住在這兒,郁桃意外。白家雖打掃的頗為干凈,但終年閉,平城膽再大的人也不敢住進這里面,當初也是死了七七四十九口人的,忠良不兇,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避諱著,就怕沾染上什麼東西。
郁桃起早就關心著韓祎的馬車修的怎麼樣,翹楚喊甘驢兒出去監工,約莫午時來回話,說已經修好了,還架著在路上跑了兩圈,確實是沒有問題。
不過郁桃極納悶,撞見世子兩回,都是馬車出了問題,便問甘驢兒:“這馬車不結實嗎?是何緣故車轱轆容易落呢?”
甘驢兒跟著修車師傅學了一早上,能說個七七八八,“這架馬車工藝極好,車轱轆落要麼上頭東西落,不過落幾率極小,這是要長年累月使用或重力撞擊,修車師傅說,馬車磨損不大,多半是因人為而致,”
郁桃咬著手里的杏子沒松口。
韓祎該不會是的得罪誰了吧,聽說這些勛爵世家,兄弟反目仇,互相暗殺,爭權奪利。
默默的打了個冷戰,覺世子夫人似乎也是個極危險的位置。
康棣街離郁府稍遠,平城南北相對。郁桃擔心空跑一趟,吩咐甘驢兒先去探探,世子是否歸府。
一來一回兩趟,等甘驢兒從白府探完消息回來,已經是落日西斜時候,郁桃仰在榻上聽拾已念賬本。
翹楚傳話進來:“甘驢兒去白府打探,說主人家估這個時候歸家,姑娘現下過去,正趕得上。”
“走,重新給我梳妝。”郁桃翻起來,來不及趿拉上鞋子,便站在妝梳臺子前,挑了一頂珍珠攢花冠,讓拾已梳完頭給戴上。
Advertisement
盡可能的將自己打扮的漂亮又隨意,翹楚特意在腰間掛了鏤花的香球,清甜的果子香。
郁桃手撥了撥,尚不及問是什麼香料,外頭甘驢兒已經來通報,說兩架馬車備好,正在西角門外的巷子候著。
云海間落日定無限,霞一覽無余的鋪陳在橘橙的天幕上。
舊白家府邸牌匾還在,巷道挨著白墻角生了整條兒的聚八仙,四月初頭八片白花圍一圈襯在青瓦檐邊。
甘驢兒前去叩門,不多時門開半面,一張白胡子白眉須的頭探出來,看了看門前的馬車,笑意盈盈道:“閣下是?”
甘驢兒呵呵腰拱手回:“勞煩老先生,昨日小主子外出,巧遇見貴府大人車轱轆壞了,這不小主子將馬車借給大人,順帶著修好了馬車特來歸還。”
“噢。”白胡子老頭看了看那家馬車,果然是自家府上的,急忙開了門,“來請客人里面坐先喝喝茶,咱們大人稍會兒就回來。”
甘驢兒原本覺著時候不早,姑娘上門不方便,回頭想聽郁桃示下,誰知道轉頭一看,已經扶著翹楚和拾已的手下了馬車,拾階而上。
郁桃戴著幕籬,隔著層紗眼睛滴溜溜的四張。
白胡子瞧見愣了愣,他沒料到世子到平城首位上門的朋友竟然是位客,忙巍巍的扯了后掛著一柄暗劍的小廝,小聲道:“讓后面備上花茶和點心。”
他在前頭領路,一面走一面嘟嘟囔囔:“來的還是個娃娃。”
郁桃進白府,好奇勝過害怕,四多是蔥蔥綠綠的竹子和矮扎叢的含笑梅,出乎意料的清凈雅意。
正廳點了油蠟,昏黃的燈紙罩著,半面屋子拉起竹簾,風進吹了滿屋子的斜,青詹爐中燃著白合子熏香。
Advertisement
沒見幾個仆人,但在落座時,右手的案幾上已經擺好了茶盞與點心。
茶水還冒著白煙。
郁桃睜大眼睛瞧著正對廳堂的屋子,因為窗扇沒有打下來,還能看見里面一座接一座的書架,似是屋子有多長,書架子就有多。
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問:“那屋子里面多書啊?”
老頭捋了捋胡子,朝一笑:“這老奴也不知道,都是大人一本本收集的,姑娘還得問他。”
代之后,老頭便離去了。
郁桃撐著頭發呆。
大人……剛才在外面有注意到這個稱呼,其實到看,想法淺,只是純粹想探一探,韓祎府上有沒有藏著什麼花姑娘。
可惜,并沒有。
畢竟沒有姑娘家能忍滿地都是竹子,像進了寺廟一樣的生活。
郁桃想到這,在心里笑了笑。
也不算特別修士,畢竟竹子可以做竹子釀酒,竹筒飯,竹筒燒,竹灰底下埋土,烤紅薯,碳烤栗子,粟米花……
但很快,默默對著竹子咽口水的行為被終止。
沒什麼聲兒,一道黑影倏然倒映在地上,郁桃嚇了一跳,轉過頭看見門外的人。
韓祎站在廊下,邊還有兩三個帶刀侍衛模樣的男子,畢恭畢敬的垂首聽令。
萬頃下的男人,眉眼間都被鍍上一層暖意。
郁桃睜著眼睛出神,猝不及防的韓祎轉過,兩人四目相對。
手指在桌上摳著,實現中韓祎走進來,隨手解下披風扔給起宿,垂眸瞧向:“看什麼?”
“啊?”郁桃扶著茶杯的手了下,腦中遲緩的打轉。
眼睛眨了眨,無意識道:“沒看你啊。”
韓祎端茶的手眼可見的停頓一瞬。
忙解釋:“別誤會嘛,我的意思是沒有看你。”
Advertisement
欸?這話好像不對啊…
反應過來,蓋彌彰的努力解釋:“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其實沒看你我在看日落。”
韓祎端著茶,沒說話,目淡淡的瞧著,似是能把人看。
行吧…
郁桃閉了閉眼,一口氣說完:“確實看你了因為落日很好看你長得也好看我的眼睛自己看的不是我本意想看。”
屋里本不亮堂,韓祎的眸子晦暗不明。不知道韓祎是何想法,但總之,從一開始在他面前就與“外表純善有德才”這八個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著實委婉了,這輩子郁桃都不可能和這幾個字有什麼集。
也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世子哥哥。”
郁桃將臉頰上的頭發掖到耳后,坐到了與韓祎一案之隔的椅子上。
撐著頭,咬咬眨眨眼,輕聲道:“馬車我都替你修好了,不知道世子哥哥用我的馬車還算習慣嗎?我真是擔心死了,要是是世子哥哥在路上又遇到什麼危險,沒有人像我一樣可以把馬車借給你用,那怎麼辦呀。”
說著話,另一只手在桌上畫著圈,說一句一個圈,慢慢的擴大。
“是不是呀,世子哥哥。”
最后一圈,了眼對面的男人,手指輕輕的似不經意的從他手背上劃過。
“哎呀,到你了,我的手上有水呢。”郁桃驚訝的張著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帕子按在那只骨節分明的手上。
“我給韓偉哥哥一。”
“郁桃。”
“嗯?”抬頭,看向跟前那張面不逾的臉,眸中已然充斥著危險的暗意。
卻忍不住角上揚,“你沒問過我名字,怎麼知道我什麼?”
韓祎面無表的用兩指夾起那張桃的綢手絹。
“我沒告訴過你我的名字,你怎麼知道我什麼?”
郁桃得瑟的在底翹起腳尖,昂著頭道:“還能有我想知道能不知道的事?”
說完,又出的笑容,刻意諂道:“何況韓偉哥哥名揚天下,誰不知道您的大名啊?”
“哦。”
韓祎慢條斯理的用凈手帕子將手指一一的過,半響,掀起眼皮看一眼。
“所以我原來韓偉。”
?韓偉怎麼了?您爹娘取的名字您不滿意嗎?
郁桃忍不住在心里翻了個白眼,臉上卻仍舊帶著甜甜的笑意:“您是不是不喜歡阿桃稱呼您的名字呀?”
學以致用,試探著:“那韓哥哥?世子哥哥?大哥哥?”
男人的眉愈發皺,郁桃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自己哪里了他的眉頭,逢迎半天都干了。
“你都不喜歡嗎?”癟了癟,使勁的想著,突然靈一現,想起翹楚那句話 :若是頭次相見,就稱偉哥哥顯得有些過分親了 。
但顯然,和“韓偉”明顯已經是十個指頭掰不過來的相見次數。
于是,郁桃眨著眼睛,將頭往韓祎面前湊了湊,小心翼翼的喚:“偉哥哥?”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戀愛腦女配被彈幕劇透后
燕驚雙被雷劈后,感覺自己好像有些不正常了。自己從小就非常喜歡的未婚夫寧墨溫柔帶笑地送她玉佩。她剛準備滿心歡喜地接下。一行加粗白字在她眼前飄過。【傻不傻,別接啊,這是寧墨送他白月光,人白月光沒收,他廢物利用,來敷衍你這個傻子的!順便讓他白月光…
45.1萬字8.18 15116 -
完結247 章
命定太子妃
死前巨大的不甘和執念讓柳望舒重生,只是重生的節點不太妙,只差最後一步就要成為晉王妃,走上和前世一樣的路。 柳望舒發揮主觀能動性,竭力避免前世的結局,也想將前世混沌的人生過清楚。 但是過著過著,咦,怎麼又成太子妃了?
15.6萬字8 9902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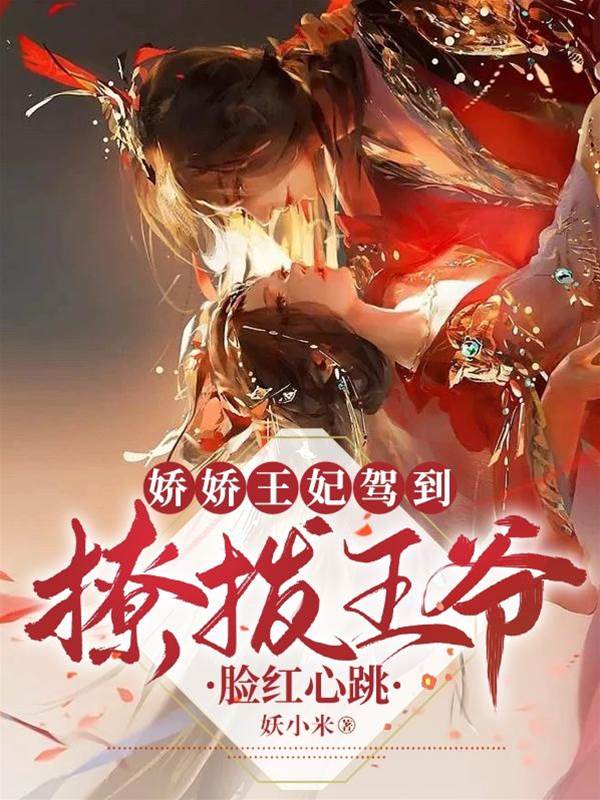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