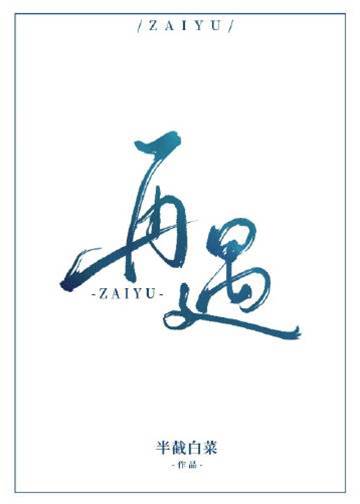《夢斷幽閣》 第6章 巧遇奇男子
七月的最后一天,又是祥州一年一度趕集的日子,天剛亮,挑擔的商販便已趕早了城。晨時未至,東西兩條長街兩側便已陸續滿了趕來賣貨的小販,鋪一簡易的竹臺子,擺上各自的貨,或者索地上鋪塊油麻布,將竹筐中的取出來擺放整齊,便也占了一塊攤位,如是,祥州城里霎時便熱鬧起來。
用罷早膳趁著天氣涼爽,婧兒便與小翠上了街。
出得門來,街上喧鬧無比,小翠興地拉著小姐的手,穿梭在人流之中,一雙大眼撲閃撲閃亮晶晶地,東瞅瞅西看看, 跑到胭脂水攤前,喊道:
“小姐快看,這個胭脂水真香呢。”
鉆到做糖人的攤位前,用力搖晃著家小姐的手,鬧著非要吃糖人,婧兒從腰間懸掛的繡著芍藥花的荷包中掏出銅板給買了一個,拿著糖人的小翠高興地像個孩子。
婧兒給自己買了一支雕有芍藥花的玉簪子,又給小翠買了一副花紋銀耳環,兩人心甚好,一時玩的興起,順著長街越走越遠。
聽到打把勢賣藝的吆喝聲,一路尋到賣藝的場口前,早已里三層外三層地圍了許多人,一陣陣的好聲此起彼伏,聽得二人不免心。尋著個空擋生生了進去。
但見場上一個頭壯漢,格健碩,濃眉圓眼,上赤膊,只穿了件開襟短背心,出口古銅結實的,下著黑大,手中一柄樸刀,翻轉騰挪,甚是靈活,刀花舞的是虎虎生風,一團刀影直將個壯漢裹挾其中,刀凌凌中帶起陣陣涼風,將眾人看的是目瞪口呆,連聲好。直待一套刀法舞完,沖著圍觀眾人雙手一抱拳,頓時引來掌聲一片。
Advertisement
立時有個瘦弱的小哥拿著個銅鑼來,“咣咣”地敲兩聲,隨即鑼在手中一個翻轉,面朝下里朝上,托手里走上前來,吆喝道:
“眾位鄉親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嘞。”
圍著場子轉一圈,眾人紛紛慷慨解囊,有給個三五子兒的,也有出手闊綽地丟個散碎銀兩。 那小哥笑的眼睛都瞇了,連連鞠躬道謝。
婧兒也從荷包里掏出幾枚銅錢丟在了銅鑼里。
不一會兒,小哥收完錢退下,上來一個半大小子,左不過十歲年紀,頭上盤一簡單的發髻,用黑發帶束,穿一黑短打,倒也十分地干練。
這小子雙手各拿一柄鐵骨朵,短柄鐵桿上各有一個像蒜頭一般的鐵質圓球,,只是這小子拿著的比尋常練武之人用的小了一號。
只見他沖著圍觀眾人一抱拳,扯著個稚的音高聲唱道:
“各位鄉鄰,現在由我來為大伙兒練一段,好不好的請眾位多多包涵!”
待得一陣掌聲過后,他便演練開了,虎、蹬、腰,空心翻,左虎打右,右虎打左,雙手舉鼎,直將兩柄小骨朵舞的是有模有樣。
一個后空翻落地,眾人正待好,突然,那孩子腳底一,一個重心不穩,腳向前沖,子向后仰倒,右手一柄鐵骨朵便了手,直向后方砸了過去。
圍觀眾人齊齊一聲驚呼,紛紛向后躲避,而鐵骨朵不偏不倚,直沖站在最前排的婧兒面門撞來,婧兒兩只驚恐的眼眸里鐵骨朵迎面而來的影像越來越近,頓時花容失,這時便是連驚呼也來不及了......
就在此危急時刻,一只手臂從后方來箍住纖細的腰,生生將托了出去,同時一束金線飛而出,纏住鐵骨朵手柄,再反向一拉,鐵骨朵 “嗖”一聲,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重重墜落在場,砸出掌大一個坑,揚起一片塵土。
Advertisement
待驚恐萬狀的婧兒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已是站在了場子中央的空地上。芊芊細腰上被一只手臂箍著,而自己卻在一個人懷中......
震驚中側目去,此人足足高了一頭有余,面容白皙,俊眉朗目,齒白紅,竟是個極為俊俏的年輕男子。兩人的臉一上一下盡在咫尺,甚至能從他晶亮的眸中看見自己驚慌的臉,婧兒不由得一臉窘迫,面紅耳赤,心跳如鼓,男子見狀亦是面上一紅,即刻松開了手臂。
此時那些了驚嚇的圍觀眾人一個個瞪著眼,張著,當他們看清安然無恙站在場中央的二人,不住鼓起掌來,直呼好險好險。
回過神來的小翠急匆匆奔了過來,“小姐,你沒事吧?”
“我、沒事。”
婧兒面紅如,著那救了自己的男子,剛要開口說聲謝謝,男子掃了一眼周邊圍觀之人,邊挑起一彎炫目的弧度,先開了口,“我們可不是猴兒,總不能站在這里讓他們觀賞吧?小姐冒犯了。”
他那極磁的聲音輕彈著婧兒的耳,婧兒沒來由得到一陣心慌。
男子陡然抬手指向天空,高呼:
“看,那是什麼?”
仿佛聽到了一聲號令,所有人的眼睛無一例外,都隨著他的手指向上看去,便在此時,婧兒到自己的腰部再次一,瞬間腳不沾地“飛”了起來,尚未來得及驚呼出聲,腳下又驟然踩實,定睛一看,已是站在了圍觀眾人的后。
婧兒不可思議地扭頭著這男子,一雙秀目中滿是驚訝,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從人群中出來的,也不知他如此神行奇步究竟是如何做到的,難怪這男子生的比子還要艷,莫非他真的不是凡人?
Advertisement
那男子也正低頭瞧著,長長的睫微微,那深邃如海的眼眸中閃爍著別樣的神采,四目相對,時間瞬間停滯。
恍惚間,一淡淡地帶著藥味的氣息浸鼻中,自生長在醫藥世家,從小與藥材相伴,婧兒對這種氣味兒極為敏,仔細嗅了嗅才發現,這奇怪的氣味居然來自這男子的上,心中一怔……
“小姐,小姐你怎麼在這里啊。”
小翠急促的呼聲驚醒了二人,那男子慌不迭松開了手臂,白皙的面頰瞬間染了櫻紅。局促間手腕輕輕一點,手中象牙扇“唰”一聲展開,出淡黃描金扇面,上繪一幅雄鷹圖,臨近午時的暖暖地拋灑在扇面上,散出點點金,盡顯高貴華麗之氣,一枚白玉墜隨著晃的折扇輕輕搖擺。
他將扇面遮住口鼻,打量著面前這個剛被自己救出的子,但見眉目如畫,雙瞳剪水,窈窕姿亭亭玉立,多一分嫌胖一分嫌瘦,此刻的雙睫微垂,含帶怯,端莊文靜、氣質如蘭,不由得怦然心,一時心醉竟然看癡了。
到他那輕漾的眼波,婧兒心里好似十頭小鹿撞一般,一張小臉直紅到了脖子……
見他二人這般神,小翠忍不住笑,沖著那男子低聲說道:
“這位公子,你這樣看著我家小姐好像不太禮貌哦。”
男子猛然回神,忙合了折扇,沖著婧兒一抱拳,道:
“方才,在下魯莽了。”
婧兒極力保持著一份鎮定和矜持,額首施禮道聲:
“多謝公子相救。”
男子俊絕倫的臉上現出一抹笑意,洋溢著如沐春風的溫馨,“舉手之勞,姑娘不必掛懷,在下還有事,先告辭了。”
言罷微一額首,即刻轉離去。
看著那一襲白長衫的矯健背影,烏黑的發髻下更襯出他白皙的脖頸泛出珍珠般澤,背脊直,一陣微風吹過,薄紗的極地褙子下擺輕輕揚起,在風中搖曳,如夢如幻。
這宛如不食人間煙火的畫中人漸行漸遠,不一會兒便淹沒在了熙熙攘攘的人中,婧兒心中倒沒來由得生出些許失落來,失落之中又帶著幾分好奇,心中暗想:“他是誰?是人,還是仙?”
“小姐,這救了您的公子是誰啊?”小翠搖了搖正在愣神的婧兒。
“哎呀,忘記問名字了。”婧兒驚覺。
“小姐,這公子好生俊俏呢。”
“嗯,是…”
陡然發現說了,不免臉上一紅,瞪了一眼,“別胡說了,快回家吧。”
此驚嚇,婧兒也沒了游玩的興致,二人轉往回走,一袖袋,卻不見了新買的簪子,恐是人多丟了,如今去找又如何能找得到,心中不免惋惜。
……
卻說那救人的男子,徑直去了一家酒樓,取了寄放在店里的白馬,抬踩鐙時,陡然腰間被什麼東西咯了一下,低頭看去,腰帶上居然卡著個白晃晃邦邦的件,取下來一瞧,竟是一枚致的白玉簪子,簪子一頭雕刻著一朵芍藥花。
他手握簪子一頭霧水,實不知此從何而來,如今細細想來,那方才被自己救了的子,頭上不就是戴著一朵芍藥花嗎?莫非這簪子正是那子之?說來真巧,怎麼這簪子就正好卡在他的腰帶上了?想來倒甚是有趣。
牽著白馬原路返回尋找,卻再不見這子的影。又不知子姓什名誰,人海茫茫這般盲目去尋,又如何尋的到。索先將簪子揣懷中,只等日后有緣遇見再奉還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349 章
我與你的情深似海
少帥說:“我家夫人是鄉下女子,不懂時髦,你們不要欺負她!”那些被少帥夫人搶盡了風頭的名媛貴婦們欲哭無淚:到底誰欺負誰啊?少帥又說:“我家夫人嫻靜溫柔,什麼中醫、槍法,她都不會的!”那些被少帥夫人治好過的病患、被少帥夫人槍殺了的仇敵:少帥您是瞎了嗎?“我家夫人小意柔情,以丈夫為天,我說一她從來不敢說二的!”少帥跪在搓衣板上,一臉豪氣雲天的說。
459.9萬字8 14962 -
完結1110 章

婚情不渝
錯愛八年,卻不知也被人愛了多年,離婚後某高冷男窮追不捨,顧小姐冷漠開口:“紀先生,我們不合適。”“我看挺合適的。”“哪裡合適?”“哪哪都合適!生辰八字,五官看相,樣樣匹配!要不你說,哪裡不合適?”顧小姐:“……” 婚情不渝,白生米,
191.5萬字8 20099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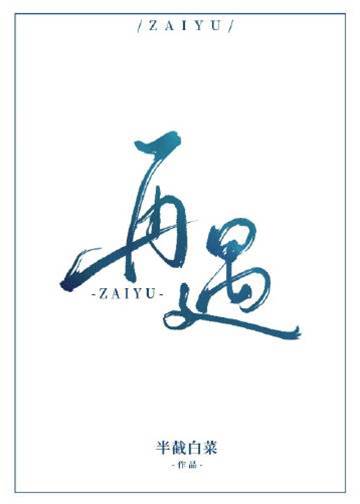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7739 -
完結475 章

閃婚拐個大佬做老公
在發現未婚夫出軌後,葉深一時賭氣拐了個農民工去領證。農民工丈夫不僅人帥活還好,這讓葉深倍感驕傲。不過...她的農民工丈夫好像還有副業?報紙上宋氏企業的總裁,和自己身旁這個一臉灰土的男人只是撞臉了吧?早上還在和包工頭說這月工資沒發的男人,怎麼到了晚上,就搖身一變霸道總裁,砸了幾個億將自己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這一切好像有點不對勁…… 夜晚,宋城一把摟住她的細腰:“老婆,咱們該加把勁了。”
82.1萬字8 611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