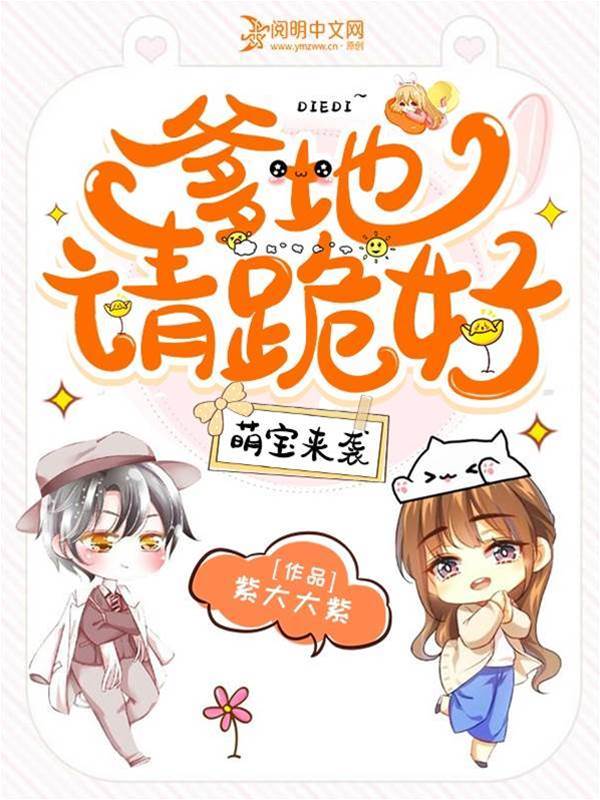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罪妻求放過》 第9章 不可言說之事
他朝著秦天翼訕訕一笑,故作輕鬆地轉了話題道:“天翼,昨天婚禮上你那樣戲弄新娘子,生氣了嗎?昨晚你們真房了?”
秦天翼一想起那個人,自己就像有團火在燒。
他昨夜失控地做出那樣瘋狂的不可言說之事,令他自己都詫異,沒來由地怒道:“這事和你有關嗎?滾犢子,讓我清淨下。”
蕭安景看他這樣子比剛才更可怕,不得趕溜出去,他不是一直說本不在乎娶什麽人嗎?可一提起昨天的新娘他這反應也太強烈了吧。
蕭安景逃似地剛拉開辦公室的門,卻又被他住了,“等等,讓你查這個什麽素素的資料查到沒?尤其是在國外的履曆和行蹤,要越詳細的越好。”
“正在查。”蕭安景扭頭問他道,“昨晚你在上發現了疑點?這個艾家千金那長相真不賴。老太太先相中了艾以薇,可艾家舍不得艾以薇,說還在國外有個兒。老太太能答應,絕對幫你把過關,比那個艾以薇漂亮……”
Advertisement
“你哪來這麽多廢話,趕滾。”秦天翼的臉已難看到了極點,其實他沒生氣蕭安景多話,而是在氣自己,一向自控力超強,為什麽會在麵對那個人時毫無自控力?
蕭安景忙逃出低氣的辦公室,在外麵舒了口氣,剛坐在休息區,就有員工和他打招呼,“蕭總好。”
“好。”蕭安景充滿親和力的笑著回應。
他表麵上是翱翔集團的BOSS,但做到集團高層的員工都知道幕後還有一位神的大老板,才是集團的正主。
蕭安景雖然平易近人、極親和力,但對於神大老板的份,絕對不會半個字。
他和秦天翼算是遠房親戚,上輩人算是同族,當年沾了蕭家鼎盛時的,有幸得到自助出國留學。
可到了國外,他才讀一年的大學,蕭家就破產了。
沒有了經濟來源,不起國外大學的昂貴學費,他隻能靠做黑工,在國外四漂泊自生自滅。
Advertisement
有人將他請到了英國的一家療養院中,他見到了那時隻有十三四歲的秦天翼。
他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見到年的秦天翼,那張好看的臉上已有著年人的穩重和深沉。
年的秦天翼開門見山地對他說:“蕭氏集團完全落到秦家手中,我母親當年的那場車禍不是意外,是有人害慘死。我要報仇,需要你幫忙。”
他的聲音冰冷麻木,讓蕭安景聽得心中一滲,可當時的秦天翼畢竟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不羈地笑問道:“憑什麽幫你?你姓秦,不姓蕭。”
“你不想完中斷的學業?想這樣一直到做黑工,被移民局的人抓住遣送回去,做個一事無的混混?”秦天翼平靜地問他。
蕭安景無所謂地道:“隻要能賺到錢,我沒覺得有什麽不好。”
“那你在國的母親呢?可是以為你還在勤學苦讀。既然什麽都無所謂,為什麽還要偽造那些在校園裏、課堂上的照片視頻?”
Advertisement
蕭安景手指彎曲繃,見他眼眸寒涼,看來他是非答應不可,再一想答應他對自己也沒壞。
“好,我幫你。”
秦天翼高深莫測地瞥了他一眼,“你還有別的選擇嗎?”
他就這樣為了秦天翼的幫手,從此聽命於比他小好幾歲的秦天翼。
後來他才知道在蕭詠梅死後,秦天翼暗中繼承了蕭家一筆的財富,這也是蕭詠梅瞞過了所有人,未雨綢繆,為自己的兒子留下的產。
靠著這筆產由他出麵,秦天翼藏在幕後,他們創建了翱翔集團。
集團從開始一家普普通通的外貿公司,在短短幾年發展為了延到各個領域的國集團,簡直就是創造了瀾城商界的奇跡。
外界都說敗落的蕭家將在他手中再次崛起,而他以秦天翼表哥的份,說是要代替過世的姨母照顧天翼,經常出秦家,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他正在回想他們一路走來的過往,手機上有條秦天翼發來的消息,“來辦公室,送我回去。”
真是大爺啊,剛他滾出來,還沒一會就他去辦公室,太會使喚人!
算了,誰他是金主,蕭安景立刻起,看了下時間,也該送他回秦家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盲婚
唐啟森這輩子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大概就是把姜晚好變成了前妻,將兩人的關系從合法變成了非法 因為幾年后再相遇,他發現自己對這女人非但興趣不減反而越來越上心了,然而這女人似乎比以前還難追 唔,不對,以前是那女人倒追他來著…… 唐先生有些犯難,追前妻這件事,說出去還真是有些難以啟齒 閱讀提示:狗血的破鏡重圓文,楠竹前期渣,不換楠竹,雷點低者慎入!!
24.3萬字8.18 32969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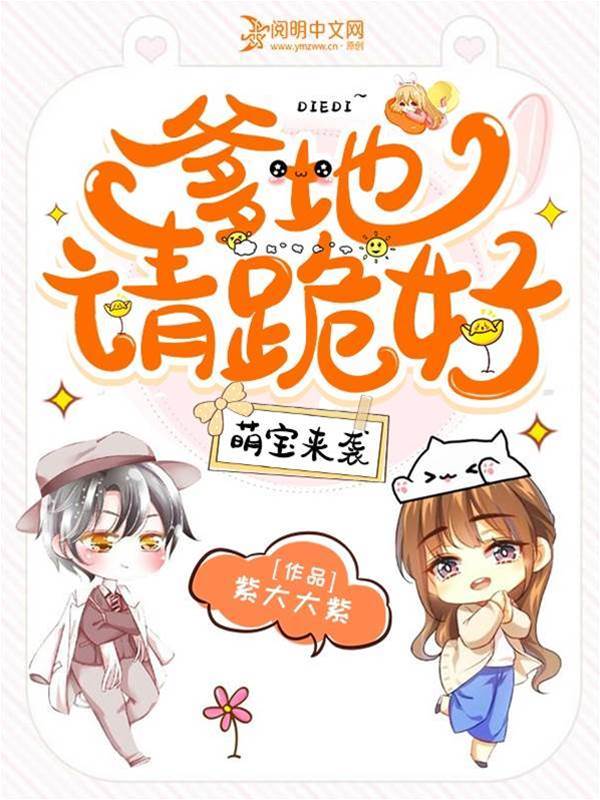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482 章

隱婚密愛:唐少強娶小逃妻
四年前,他們約定登記結婚,她卻被他所謂的未婚妻在民政局門口當眾羞辱,而他卻人間蒸發,無處可尋,絕望之下,選擇離開。四年后,再次相遇,卻被他逼問當年為何不辭而別,她覺得諷刺,到底是誰不辭而別?他將她壓在身下,肆意的掠奪著她的一切。唐昊,請記住…
83.7萬字8 48085 -
完結167 章

乍見歡
【京圈高干+年齡差+現實流+女性成長+上位者為愛低頭】【情緒穩定高冷太子爺vs人間尤物清醒金絲雀】 眾人皆知沈硯知,克己復禮,束身自愛。 只有聞溪知道,他在私下與她獨處時,是多麼的放浪形骸,貪如虎狼。 — 聞溪是沈家為鞏固權勢豢養的金絲雀。 將來,沈家要把她送給誰,就給誰。 她守身守心,可偏偏被那個金字塔尖的男人撬開了心房。 他白天跟她裝正經,晚上跟她一點不正經。 直到有一天,有個男人宣稱要帶她走。 而她也不愿再當金絲雀,她想遠走高飛。 沈硯知終于坐不住了。 “聞溪,你贏了。” “我這根高枝,隨你攀。” 他是別人高不可攀的上位者,卻甘愿做她的裙下臣。 聞溪終于恍然,原來自己才是沈硯知的白月光。 為她,他低了頭。 — 階級這種東西,他下不來,你上不去。 最體面的結果就是,君臥高臺,我棲春山。
28.9萬字8 97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