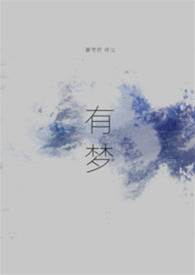《言教授,要撞壞了》 第7章
甩臉
醒來的時候,都已經是第二天中午了。
言征不在家,倒是有一個很面善的保姆來給梳洗,遞上乾淨的。
阮誼和心裡惦記著上課的事,換了服就匆匆趕到學校去上課。畢竟現在是高三,只有兩個月不到就要高考了。
誰知等趕到學校時,高三一班正好在上理課。
阮誼和一看到言征就想起昨晚那些讓恥的事,站在教室門口,垂著頭低聲說了句「報告」。
言征卻像沒事人一樣,裝出「好老師」的模樣,溫和地說:「進來吧。」
阮誼和背著書包迅走到自己那個單獨座位,生怕別的同學看到脖子上的吻痕。
言征不愧是q大的頂級教授,他的理課容很充實。
一節課快上完,別的學生都有種「居然這麼快就要下課了」的依依不捨,意猶未盡地想再聽幾道題解析。阮誼和倒好,一個人在最後一排聽得迷迷糊糊打瞌睡——別的科目都很優秀,唯獨在理這門科目上不開竅,每次考試墊底。
「阮誼和,」言征點名:「我剛剛說了什麼?」
Advertisement
這人,是故意整吧?
哼,要給他點顔瞧瞧,讓他知道阮姐也不是吃素的!
阮誼和懶懶散散站起來,隨口說:「你剛剛,念了我的名字啊。」
衆生投來小刀般的目——這個阮誼和,怎麼完全不給男神老師一點面子啊?!
「除了名字呢?」
「沒聽見,睡著了。」
這真是……太拽了吧。
阮誼和前排那男生回頭看,在心暗暗佩服阮誼和這種完全不怕老師的膽量。
言征對阮誼和出奇的有耐心,以往別的老師要是被阮誼和這麼懟,肯定要翻臉罰阮誼和站到教室後面,甚至站到教室外面。
「下課來我辦公室。」言征給的回應風輕雲淡。
繼續上理課。
阮誼和看著黑板上清晰的板書,有種看天書的覺……唉,理這玩意,真的是學不會,學不會。
過了不到五分鐘就下了課,阮誼和裝作忘了言征的話,從課桌肚裡掏出一張的皺的數學卷子,把卷子展開平了正要開始刷題,卻聽那人魂不散地說——
「阮誼和,過來。」
本來是下課的時間,班上的學生有的在做題,有的正圍在一起說話,這會兒全都齊刷刷把頭扭向最後一排,看向阮誼和——
Advertisement
大概是要看好戲,看怎麼跟新來的代課老師杠到底。
阮誼和討厭這種爲焦點的覺,不願地拖著步子走向講臺。
言征指了指講臺上那兩本理習題書,說:「幫我拿到辦公室去。」
……這人自己沒手啊?就兩本書還要學生幫他拿,多大的威風?!
阮誼和拿著那兩本理習題書,逛花街似的晃晃悠悠跟在言征後面走。
整層樓就最特殊,不好好穿整套的校服。
其實阮誼和委實冤枉,之前在酒吧住宿,有一次和一個同居的人吵架吵的厲害,那人拿著剪刀二話不說就把的校服長剪得七八糟,完全沒法再穿出門。阮誼和也捨不得花錢再買一套新校服,乾脆就每天象徵地套一件校服外套大搖大擺走在學校裡,路人要多看兩眼也無所謂了——反正打死也不會花冤枉錢再買這醜兮兮的大校服。
至於校被人剪爛了這事,阮誼和也絕口不提,每次年級主任、校長逮到不穿整套校服,就一臉無所謂地站在那兒挨訓,挨完訓了就走人,從不解釋半個字。
Advertisement
到了言征的辦公室,化學老師正好要來找他換課,看到了跟在他後的阮誼和,於是調侃言征——「怎麼樣,言教授,是不是高中學生比大學生還難管?」
言征似笑非笑看著阮誼和:「你說呢?你難管嗎?」
阮誼和不說話,氣鼓鼓地瞪著他。
「其實不難管。」言征淡淡地說。
阮誼和撇了撇,毫不買帳。
猜你喜歡
-
完結14 章
白領麗人
石文靜這時瞪大眼睛由鏡中看到由身后抱緊她與她腹背相貼的我,高傲的眼神流露出來的是極度的驚慌,不斷的搖著頭,長發在我臉上刮來刮去,發際的幽香不停的往我鼻子里鉆。扭動的纖細腰肢使她俏嫩富有彈性的美臀不停的在我已經脹鼓鼓的陽具上磨擦,弄得我本已經抬頭的大陽具更加的粗硬。
6.6萬字7.81 41645 -
完結79 章

玲瓏孽怨
趙霜靈忍著淚,依言照做。成進一邊發號施令,教她吹喇叭的技術,一邊在她雪白的身子上下其手。趙霜靈只覺口中之物捅得她喉嚨很不舒服,幾欲作嘔,身上又給摸來捏去,一雙手掌一會抓她乳房,一會摸她下身,感覺怪不可言,羞恥無比。身體輕輕扭動,卻躲不開這對淫爪,心內氣苦,卻只得任他玩弄。
22.7萬字6.94 127577 -
完結80 章
龍神是個騙炮狂
修煉成型的第一天,夏天決定找個男人,通過“采陽補陰”提升修為。然而,她卻不知道,自己的采陽對象,竟然是從三界消失了萬年之久的龍神墨離。墨離告訴她,因為她的修為太渣,她采陽不成,反被別人采了。三魂七魄丟了一魄,她只剩下三年陽壽。想要拿回魂魄,兩人雲雨一次,可以延壽三天。夏天算了算,要拿回原本五百年的壽命,她需要向墨離獻身:六萬零八百三十四次……毛都要被他做禿了啊……P.S.1.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虐身,不會變態血腥。2.我也不知道算甜寵文,還是追妻火葬場。3.嬌軟傻白甜女主 x 高冷白切黑男主4.1v1,SC,劇情肉,盡量不會為肉而肉。5.作者是個老沙雕,會忍不住寫沙雕梗。6.完結之後,H章開始收費了。一個吃女孩子不吐皮的故事。已完成:《離朱》點擊直達正在寫:《大理寺.卿》點擊直達
15.7萬字8.33 68215 -
完結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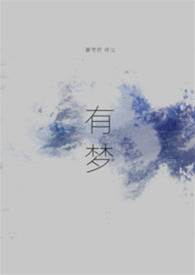
有夢
作品簡介: 她總說他偏執。 是了,他真的很偏執,所以他不會放開她的。 無論是夢裡,還是夢外。 * 1v1 餘皎x鐘霈 超級超級普通的女生x偏執狂社會精英 練筆,短篇:) 【HE】 其他作品:無
5.9萬字8 55327 -
完結48 章

史上最強腹黑夫妻
牧白慈徐徐地撐起沉甸甸的眼皮,面前目今的所有卻讓她沒忍住驚呼出聲。 這里不是她昏倒前所屬的公園,乃至不是她家或病院。 房間小的除卻她身下這個只容一個人的小土炕,就僅有個臉盆和黑不溜秋的小木桌,木桌上還燃著一小半截的黃蠟。 牧白慈用力地閉上眼睛,又徐徐地張開,可面前目今的風物沒有一點變遷。她再也顧不得軀體上的痛苦悲傷,伸出雙手用力地揉了揉揉眼睛,還是一樣,土房土炕小木桌••••••
14.5萬字8 97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