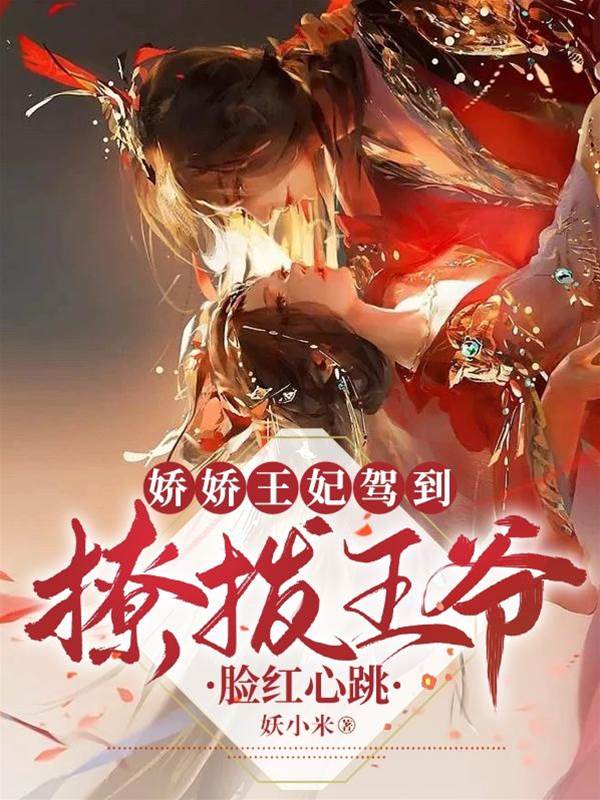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乖,叫皇叔》 第1卷 第3章 夫君的男人
虞清婉果然沒有來找的麻煩。
翌日。
曉風殘月,天蒙蒙亮。
宮里派來的喜娘領著幾個丫鬟走進來,為虞清歡開面、梳頭,上妝、穿。接著上花轎、迎青廬、拜天地、喝合巹酒。
一套繁文縟節走下來,花了整整一日的時間。
“淇王長孫燾,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虞清歡坐在床上,聽著外頭的竹聲漸漸息止,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前世臨死前一幕幕。
重活幾日,這是困擾著最大的疑,讓百思不得其解,加之想要擺虞家,不再重蹈前世的覆轍,所以心甘愿地穿上嫁,嫁進淇王府為他的王妃……
虞清歡心房微,思忖稍后該怎樣試探。
想過無數種他們見面的景,唯獨沒想到,長孫燾本就沒有再踏進房間一步。
虞清歡招來守在門口的小丫頭一問,原來長孫燾早已在他的房間宿下。
前世的種種,難道都是錯覺?!
Advertisement
“帶我去見淇王!”虞清歡拆下頭上的九翟冠,用力擲在地上,命令道。
小丫頭嚇得面一白,戰戰兢兢地領著虞清歡在王府里彎彎繞繞,好長一段距離,走得雙酸痛,才走到長孫燾的臥房——暮梧居。
要想出其不意,必要先聲奪人。
虞清歡推開小丫頭,一腳踹開房門。
里頭,本該出現在房花燭夜的長孫燾,此刻卻正與另一個男人滾在一起。
一上,一下。
二人舉止親,仿似耳鬢廝磨。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王爺的男人?
虞清歡捂住了緩緩張大的,一雙有神的大眼打量著被長孫燾著的男子。但見他長相昳麗,朗目疏眉,神骨氣質飄瀟,就像玉立瑯嬛仙鄉的芝蘭玉樹。
越看越像王爺的男人。
二人同時轉過頭看著,下一剎那,長孫燾立即彈開,語氣涼淡:“謝韞,你先下去。”
虞清歡目送謝韞離去,甩開腦海中那些七八糟的猜測,定了定心神,轉頭一瞬不瞬地看著長孫燾:“為什麼沒有來房?”
Advertisement
長孫燾整了整襟,跪坐在小幾前,神淡漠:“本王以為王妃心里有數。”
虞清歡問:“王爺懷疑我是祖父派來的細作?”
長孫燾冷哼一聲,沒有說話,算是默認。沉默使得他周溫度直降,不怒而威的氣度,讓人而生畏。
那帶著凜凜迫的氣場,駭得虞清歡心突突地跳,虞清歡強迫自己保持鎮定,握拳頭擲地有聲地道:“不是每個虞家的人都想跟你作對,我不是細。”
長孫燾抬眸掃了一眼:“那便證明給本王看。”
虞清歡傾,雙手按在小幾上,目灼灼地向長孫燾,纖弱的子就像一桿不折的青竹:“如何證明?”
長孫燾認真地道:“想讓一個子忠誠,必先占據的子,既然你如此有誠意,那……了,只有你做了本王的人,本王才會考慮要不要信你。”
說著,長孫燾猛地湊過來,灼灼的鼻息噴在虞清歡臉上, 麻麻的。而他的手,順著的面頰落至腰際,輕輕挑開腰間的束纓羅帶。
Advertisement
淡淡馥郁的清貴氣息,無孔不地包裹著,虞清歡強忍住靠近男子的不適,目不轉睛地盯著長孫燾,角噙著一抹若有似無地笑。
他的眼角,不屑于任何與。
知道,這一切只是戲謔的試探。
“淇王,這樣太慢了,不若我們各各的?”
長孫燾的手,突然一僵。
虞清歡忍不住“撲哧”一聲笑了出來,長孫燾雙眼危險地瞇起,猛地手將撲倒在地,而他整個人瞬間傾覆過去。
“王妃如此急不可耐,本王也不好王妃久等。”長孫燾側躺在虞清歡邊,一手攬住虞清歡的后頸,一手住的臉頰,薄有的,慢慢地湊過去。
虞清歡呼吸一窒,下意識地想要推開長孫燾,但理智告訴,絕對不可以。
兩者較量,誰先沉不住氣誰就輸了。
一下、兩下、三下……
落針可聞的屋,兩人的心跳聲漸漸變得一致。
“砰砰!”就在雙即將及的剎那,敲門聲響起,接著便是一道悅耳的男聲,“王爺,急事。”
兩人幾乎同時暗自舒了口氣,長孫燾彈起,整了整裳,一甩潑墨傾瀉的青,意味深長地看了虞清歡一眼,轉大步離去。
虞清歡著他絕世靜邃的背影,輕輕地笑了:無論你披著什麼樣的皮,我都要開來瞧一瞧,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你。
猜你喜歡
-
完結474 章

喜嫁
穿入夢中,一夢成真。 連續三日做同一噩夢,可再次蘇醒,發現自己成為夢中人! 大族後裔、庶嫡之身,父慈母寵弟可愛,可清正小家成了各房爭鬥的靶子、刀俎上的魚肉,這怎能忍? 噩夢場景縈繞心頭,會否真的發生? 她,心中隻有兩個字活著。
126.4萬字8 18298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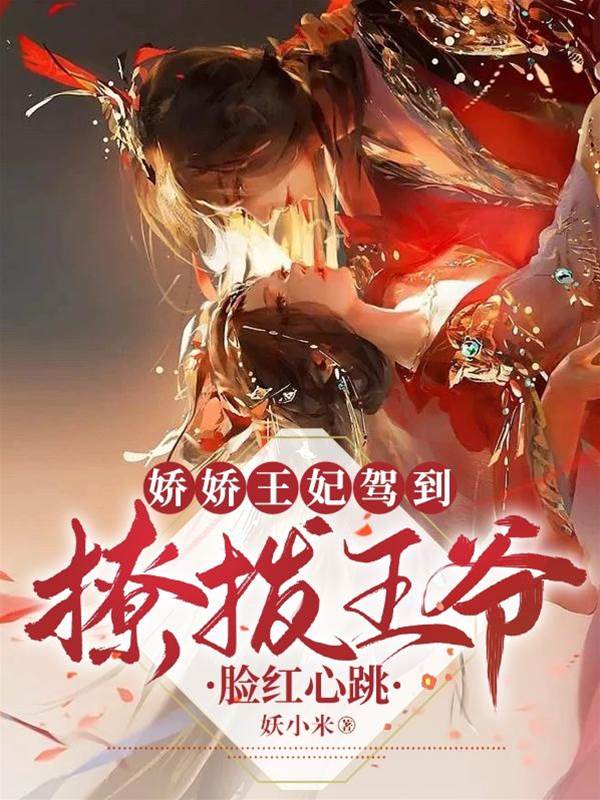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1033 章
紈绔夫妻互捧日常
未婚夫被搶? 被迫嫁京城著名紈絝? 蘇予安:嘖,當我這心理諮詢師是白當的? 這十年是白穿的!! 江起雲:我要娶我堂哥的前未婚妻? 打死我也不服...... 真...... 真打?! 滿京都的人都在等著看兩個人的笑話,可等到的卻是兩人的日常互捧。 江起雲:我家娘子機敏聰慧,可旺夫鎮宅! 蘇予安:我家夫君玉樹一棵,可遮風擋雨! 京都貴族VS百姓:......
182.3萬字8.18 19262 -
完結759 章
神醫棄女要強嫁
明幼卿是中西醫雙料博士,一朝穿越,成為被太子退婚後,發配給了廢物王爺的廢材嫡女。 世人都笑,廢材醜女配廢物王爺,真絕配。 只是新婚後……某王:沒想到明家醜女樣貌傾城,才氣絕倫,騙人的本事更是出眾。 某女勾勾手:彼此彼此,也沒想到廢物王爺舉世無雙,恩,身材也不錯~兩人真真絕配!
138.2萬字8 110557 -
完結733 章

和離后禁欲殘王每天都想破戒
前世,她為家人付出一切,卻被人棄之敝履。重生后,她果斷與眼盲心瞎的丈夫和離,與相府斷絕關系。斗婊虐渣,從一個棄婦搖身一變成了各個大佬爭相寵愛的國寵。帶著疼愛她的外祖一家青雲直上。當發現前一世一直救她護她的人,竟然是她的“大表哥”時,她紅了眼,緊緊摟著那人不撒手。欲拒還迎的男人緊繃著唇角:“青天白日,成何體統!” 可他那冷情的眉眼,都已經彎成了月牙。聲音啞沉地道:“關門!”
132萬字8.18 1744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