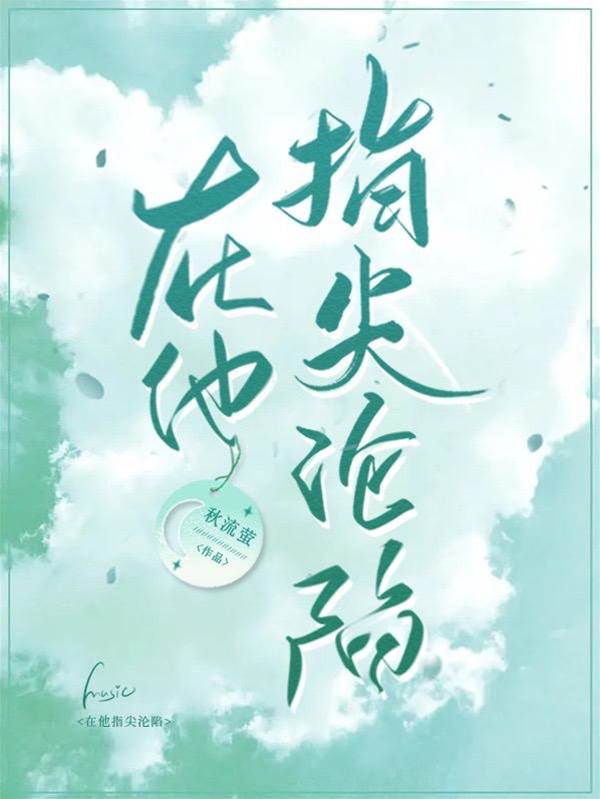《渣男白月光回國后,豪門千金她不裝了》 第23章 酒吧遇騷擾
初棠問:“讓江家收養許靜萱?”
周雪落搖搖頭,湊近了點,小聲說:“不止,當初跟江夫人說,讓時序哥以后娶了許靜萱當老婆。”
聞言,初棠震驚地睜大眼睛。
“我去,這麼勁?”陳媛媛聲音拔高,“還真敢說啊!”
周雪落道:“后來不知道江夫人怎麼跟說的,那個保姆也接了讓江家收養兒這個報恩方式。”
陳媛媛語氣不屑道:“也是,江夫人就這一個兒子,怎麼可能讓他娶一個保姆的兒。”
周雪落:“是啊,時序哥可是江家唯一的繼承人,說什麼都不可能娶一個保姆的兒的。”
初棠抿了口果酒,若有所思。
幾人聊著八卦,沒有注意到在們后不遠,有個人目狠戾地盯著們。
初棠喝了幾杯果酒,度數很低不會醉人。
跟兩個閨聊了會兒,初棠站起,“我去下洗手間。”
洗手間外的過道上。
初棠上完洗手間出來,被兩個男人攔住去路。
一個男人個頭壯實,剃著頭,穿著黑背心,出大花臂。
他吹了吹口哨,笑得極其猥瑣,“,陪哥哥玩玩兒,嗯?”
初棠正拿著手機回復消息,聞言抬眸看了男人一眼,不聲地調到錄音界面,開始錄音。
Advertisement
然后將手機揣進兜里。
另一個男人是個細狗,染著一頭黃,他里叼著煙,“長得倒是漂亮,起來很帶勁兒啊。”
初棠冷聲道:“剛在廁所里吃飽?這麼臭。”
黃笑得里氣,“一晚上多?開個價吧。”
走廊很窄,路被這兩個男人擋住,初棠過不去。
冷靜地抱臂站在原地,淡然開口:“守靈五千一晚,哭喪加兩千,嗩吶班子兩千八,一般火化四九九,加紙棺多五百,火化后骨頭沒碎另加敲碎人工費一千二,你家里誰去世了?兩個以上有優惠,死得多可以打折,滿一萬減一千。”
黃氣急敗壞地啐了一口,“臭婊子!給臉不要臉是吧?”
大花臂壞笑著走上來一步,還手解開了皮帶,“裝什麼清純?早就被人玩壞了吧?還裝?老子今天就要在這里辦了你!”
說著,他對小黃揚了揚下,“走,把拖去男廁所里好好玩玩兒。”
說著,他和黃就朝著初棠走過去。
在他走過來的一瞬間,初棠猛的抬起腳快準狠地往他下踢去。
這一腳,使了十力氣。
“啊——”
花臂男慘一聲,兩只手捂著下痛苦地倒在地上。
他蜷著,痛得渾痙攣。
Advertisement
細狗小黃見狀,揮舞著拳頭罵罵咧咧地沖上去就要揍人。
初棠擒著他的胳膊使勁一扭,“咔嚓”一聲,小黃的胳膊臼了。
過道上頓時慘連連。
初棠勾了勾,眸微微瞇起,“就這?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一臉嫌棄地出紙巾了手,“巧了,姑擒拿散打剛好都會一點兒,好久沒活筋骨了,剛好拿你們練練手。”
這話傷害不高,侮辱極強。
黃揚起另一只手還要再上,被初棠一個過肩摔狠狠地摔在地上。
高跟鞋碾在黃臉上,就像在碾一直螞蟻,“回去再練練。”
“救命啊,救命啊!”花臂男痛苦地捂著聲嘶力竭地喊著救命。
初棠扭頭一看,他的竟然滲出了。
嘖,力道沒有控制好,不會給他那玩意兒踢了吧?
很快,酒吧工作人員聞聲趕來,瞧見這場面當場愣住,一時間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花臂男躺在地上,額頭滲出冷汗,他吃力地說:“疼死老子了,你愣著干嘛啊,快打120,我要疼死了。”
這邊靜太大,很快就圍滿了人。
陳媛媛和周雪落見初棠去洗手間去了這麼久還沒回來,不放心過來看看。
這一看就不得了。
Advertisement
“臥槽!”陳媛媛一驚一乍地跑過來,“初棠你的佛山無影腳和降龍十八掌重出江湖了?”
周雪落看了看地上哀嚎慘的倆人,“嘖”了聲,轉頭看初棠,“棠棠,你沒有傷著吧?”
初棠了頭發,“沒,就憑他們倆,連我一頭發兒都不到。”
“太猛了我的棠!”陳媛媛一臉崇拜,“早知道當初就跟你一起去學散打了。”
酒吧工作人員報了警,打了120。
兩個男人被救護車拉去醫院,警察帶阮初棠和酒吧負責人去派出所。
周雪落和陳媛媛跟了過去。
圍觀群眾散去。
藏在柱子后面的許靜萱緩緩走出來,眼中閃過寒。
真是廢。
二打一阮初棠卻毫發無傷。
沒想到這個阮初棠看起來瘦瘦的,一副弱不風的樣子,竟然是個練家子。
看來一般的混混流氓不是的對手。
下次得多找幾個人,還得找專業的打手來對付。
……
江時序趕到的時候,初棠正在做筆錄。
警察這邊調了監控,確定是那兩個男人先挑釁手的,初棠這是正當防衛。
不過醫院那邊來信說花臂男傷得嚴重,睪丸破裂,要做傷鑒定。
阮初棠的正當防衛很有可能超過必要限度構防衛過當了。
警察說現在不能放人。
江時序正要打電話找關系讓警局放人。
初棠攔住他,淡定自若地對警察說:“一顆破碎是輕傷,兩顆是重傷,如果兩顆都破裂切除了那我確實有可能會構防衛過當,警局可能會以故意傷害罪立案調查。”
這一塊就涉及到初棠的專業領域了。
“但是——”初棠拿出手機打開錄音播放了一段音頻。
那兩個男人在過道上說的話被初棠完完整整地錄了下來。
初棠眸淡定,緩緩道:“警察同志,我有證據證明這兩個人意圖強,對于強罪這種暴力犯罪,我的反抗合合理,不會構防衛過當。”
初棠將手機放在桌面上,神嚴肅,“我現在正式報警,對方意圖強我。”
猜你喜歡
-
完結94 章

豪門女配不想擁有愛情
許辛夷一覺睡醒,得到一個系統,系統告訴她,你是女配,下場凄涼。 為了避免這一結局,許辛夷在系統的驅使下,兢兢業業干著女配該做的事。 易揚忍無可忍,終于提了離婚。 許辛夷懷著愉悅的心情,將早已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放自家老公面前,悲痛欲絕等著他簽字。 ——“快簽快簽!我終于可以離開這鬼地方了!” 突然能聽到許辛夷心聲的易揚把筆一扔,“不離了。” *** 自從易揚能聽到許辛夷心里話后發現,一直口口聲聲說愛自己的妻子表面麼麼噠,心里呵呵噠。 “老公,你真好,我好愛你啊!” ——“我不會就這麼守著這個自大的男人過一輩子吧?我真是天底下最慘的女人!” 易揚聲嘶力竭:我哪里不好!你說!我改還不行嗎! * 現代架空
34.5萬字7.73 11338 -
完結2765 章

天降萌寶求抱抱
當秦薇淺被掃地出門后,惡魔總裁手持鉆戒單膝跪地,合上千億財產,并承諾要將她們母子狠狠寵在心尖上!誰敢說她們一句不好,他就敲斷他們的牙!…
637.4萬字8.18 548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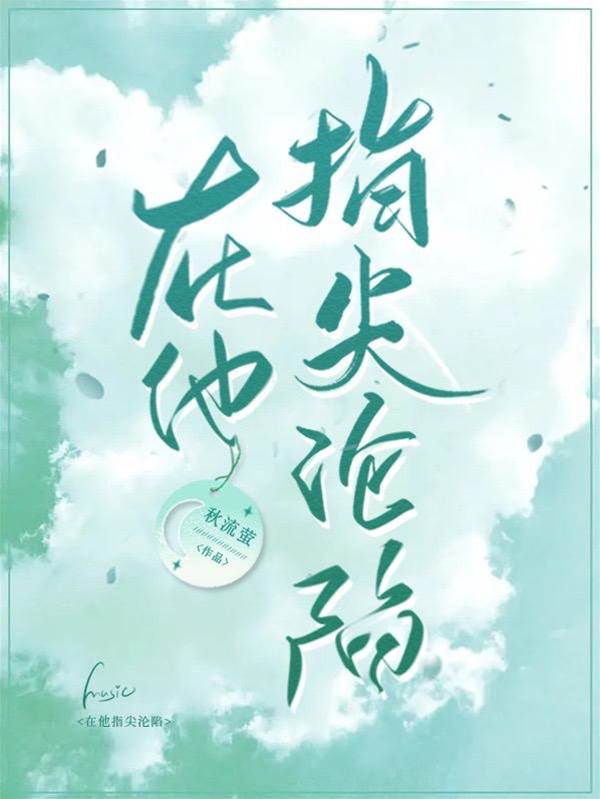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 22009 -
完結178 章
含梔
路梔天生一張乖巧臉,像清晨夾着露珠的白梔,柔軟得不帶攻擊性。 但只有親近的人知道,她那張氧氣少女臉極具欺騙性,偶爾狐狸尾巴冒出,狡黠得一身反骨。 畢業那年聯姻出現意外,她嫁給原定人選的兄長,是傅氏集團赫赫有名的傅言商,世家圈內名號響動,心動者無數。 她謹慎着收起自己不服管的狐狸尾巴,摸索着不熟婚姻的相處之道,爲討些好處,驚喜地發現裝乖是個不錯的方向。 於是她噓寒問暖、甜美溫柔,一切盡在掌控,有條不紊地升溫。 意外發生在某天,她清好行李離開別墅,只留下“合作愉快”四個大字,然後翅膀揮開不到幾天,被人當場抓獲。 後來覆盤,她挨個細數:“……所以你喜歡的那些乖巧,都是我裝的。” “你以爲我不知道,”男人慢條斯理的聲音響起,“爬山我走山路你坐纜車,一包薯條偷吃幾個來回,送我的眼鏡根本不是給我買的,做了幾個小時的爆漿蛋糕,你吃一口就嫌膩。” “喝醉了坐我肩膀上,看別的男人揮熒光棒。”他沉沉,“敢在傅言商頭頂蹦迪,誰能有你膽子大。” “你乖?你哪乖?” 他視線微動,漫不經心哼笑道:“也就接吻讓你張嘴的時候乖點。” “……”
28.6萬字8 8391 -
完結145 章

小嬌嬌嘴毒心野,禁欲男人來撐腰
【雙潔 先婚後愛 老夫少妻 扮豬吃虎 寵妻】二嬸單獨搬回家住,逼得爸媽外出租房, 蘇悅怒火衝天回家討要說法, 等著她的是白蓮花表妹勾搭了她男朋友, 蘇悅笑盈盈使出了殺手鐧, 不好意思啊,我已婚。 被結婚的神秘男人抱著她進了民政局 做戲做全,領證吧。 婚後,小嬌嬌管不住嘴,動不動就跟人幹架。秦爺,你都不管管你家小祖宗?秦爺:小祖宗,別怕,看誰不順眼就動手,老公給你撐腰。
26.4萬字8.18 12303 -
完結126 章

少爺們的寶物/無處逃!京圈太子鎖嬌嬌
【甜寵+團寵+蓄謀已久+暗戀拉扯+強取豪奪】楚柔十歲來到顧家,然后開始跟顧家的四位少爺糾纏不清。 尊貴冷冽的大少將她鎖入懷中:“楚柔,你這輩子只能屬于我。” 溫柔貴氣的二少從后圈著她:“阿柔,你永遠是我的公主殿下。” 冷漠疏離的三少像個騎士般守護在她左右:“小柔,,你可以隨意的活著,我永遠都在。” 英氣張揚的四少是她永遠的死黨:“小棉花,誰敢欺負你,告訴我,我給你揍回去!” 楚柔是顧家四位少爺的寶物,也是他們的今生唯一。
20萬字8.33 176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