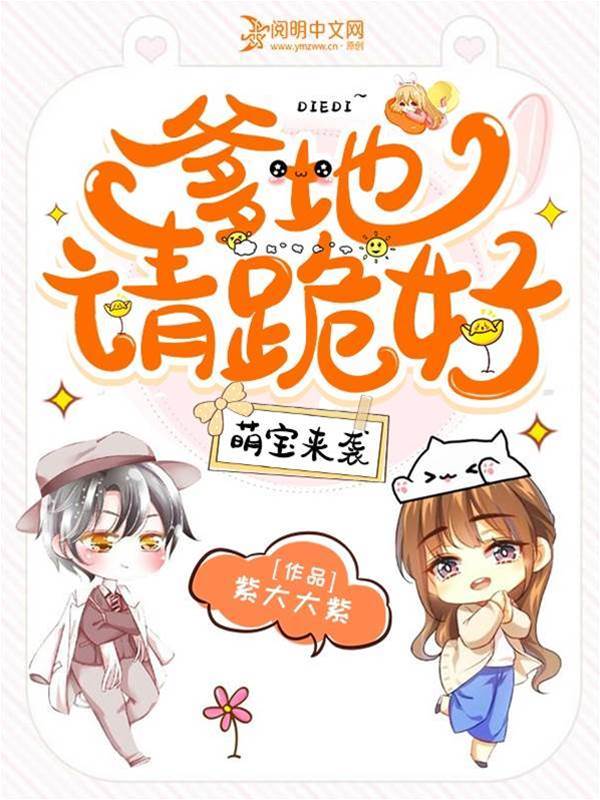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相依為病》 第1卷 第15章 懷孕
南桑在別人那是半點虧都不吃,哪怕是口舌之爭。
但江州是真的喋喋不休。
全都是高燒后的疲乏,按了按眉心,選擇捂住耳朵。
江州的喋喋不休乍然而止。
手掌握了拳,半響后砸了下方向盤,摔了車門就走。
南桑手放下,看向后視鏡里他氣沖沖的背影,找出手機了個代駕,開車把送回了南家。
到家的時候趙欣在,看見抱起孩子起就走。
南桑沒理會,上樓去找南鎮。
“我懷孕了。”南桑扯個凳子坐下,“我和江州一個月后辦婚禮。”
南鎮怔住,“你說什麼?”
“懷孕。”南桑有點沒神的按了按太,“你時間人去江家一趟,安排婚禮細節。”
南家的宅子很多年前就買了。
景家給買的。
其實從跟上算,算是南桑母親的東西,也算是南桑的東西。
但好像是因為名字在南鎮名下,從小到大沒住過幾次,所以南桑總覺這里很窒息,從空氣到一切。
Advertisement
說完直接起,“我去車里,你找個人送我回去。”
不等南鎮答應,轉出去,坐上了車。
昏昏睡的時候車門被打開。
“江州在外的人懷孕了?”
傳來的聲音冷冷清清的,有種別樣的質。
南桑睜眼,從后視鏡里和坐上駕駛座的景深對視。
景深穿了一黑,修長的手掌覆在漆黑的方向盤,便顯得手背顴骨那的紅痕分外明顯。
像是打人打的。
南桑想自己真是有病。
景深可不是脾氣暴躁又霸道的江州。
他和青梅竹馬相依為命那麼多年。
大多時候卻依舊冷淡。像是對什麼都不關心,也像是對什麼都不走心。
南桑很見他發脾氣,更別說打人。
就算是做檢察那會,也是如此,和他搭檔的肖玉恒說景深像是沒七六。
他這種人,估著只有南初當著他的面和別人在一起親親我我,才能惱到點手。
Advertisement
南桑別過眼,淡道:“為什麼這麼說?”
“你昨天剛做了全檢查,沒懷孕。”
南桑哦了一聲,看向窗外。
景深開車,路上說:“你要早做打算。”
南桑沉默幾秒,笑笑:“什麼打算?”
“拿這事重簽協議。”景深等紅綠燈的時候點了煙叼在邊,含糊道:“想辦法把江州名下的財產,收攏一部分到你名下。”
南桑了后槽牙,笑笑:“我不要臉的嗎?”
南桑坐正,盯著他:“圈里給別人養孩子的,統稱為窩囊廢,我南桑這麼不要臉嗎?要活別人眼里的笑話。”
景深從后視鏡和南桑對視了眼。
這瞬間。
景深的臉在南桑眼中,以一種奇異的速度扭曲了。
幾乎稱得上是面目全非到讓人生厭作嘔。
景深像是看不出眼底濃郁到溢出來的厭惡,啟嗤笑,“你早就活一個笑話了。”
Advertisement
南桑和江州吵架。
江州暴跳如雷,南桑不如山,心如止水。
這瞬間,覺事像是反了過來。
景深心如止水,冷靜無所謂,南桑因為病后的蔫吧一掃而空,臉被怒火充的嫣紅。
氣沖沖的摔了車門,轉就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后車響起鳴笛。
南桑扭頭想罵。
駕駛座的窗戶下,一個面生的人小心道:“您好,我是代駕。”
南桑頓了幾秒,拉開車門上去。
到家掀開被子蒙住臉。
昏昏沉沉睡過去的時候,邊進一個滾燙的子。
帶著酒氣,不止,還有濃郁的香水味。
開的服,手著的腰間朝上索。
舌湊近挨著南桑的耳畔輕舐。
呼吸又又重。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盲婚
唐啟森這輩子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大概就是把姜晚好變成了前妻,將兩人的關系從合法變成了非法 因為幾年后再相遇,他發現自己對這女人非但興趣不減反而越來越上心了,然而這女人似乎比以前還難追 唔,不對,以前是那女人倒追他來著…… 唐先生有些犯難,追前妻這件事,說出去還真是有些難以啟齒 閱讀提示:狗血的破鏡重圓文,楠竹前期渣,不換楠竹,雷點低者慎入!!
24.3萬字8.18 32969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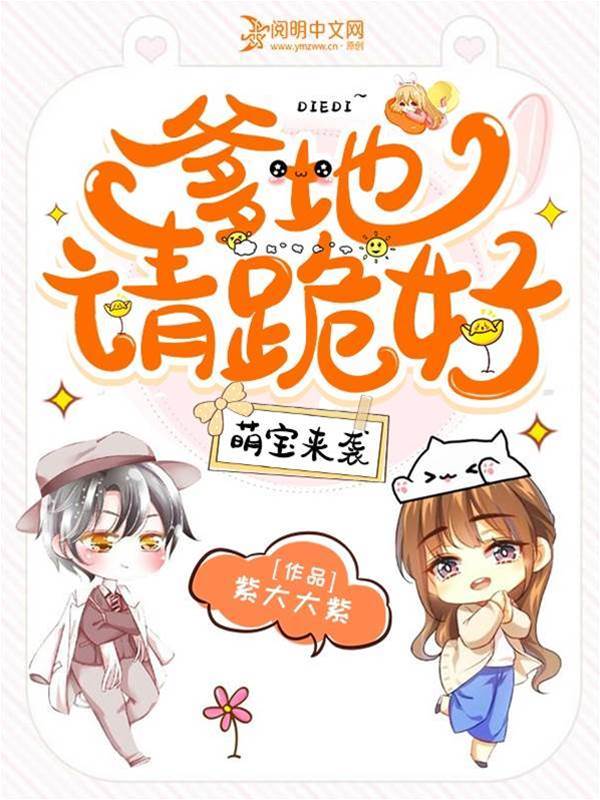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482 章

隱婚密愛:唐少強娶小逃妻
四年前,他們約定登記結婚,她卻被他所謂的未婚妻在民政局門口當眾羞辱,而他卻人間蒸發,無處可尋,絕望之下,選擇離開。四年后,再次相遇,卻被他逼問當年為何不辭而別,她覺得諷刺,到底是誰不辭而別?他將她壓在身下,肆意的掠奪著她的一切。唐昊,請記住…
83.7萬字8 48085 -
完結167 章

乍見歡
【京圈高干+年齡差+現實流+女性成長+上位者為愛低頭】【情緒穩定高冷太子爺vs人間尤物清醒金絲雀】 眾人皆知沈硯知,克己復禮,束身自愛。 只有聞溪知道,他在私下與她獨處時,是多麼的放浪形骸,貪如虎狼。 — 聞溪是沈家為鞏固權勢豢養的金絲雀。 將來,沈家要把她送給誰,就給誰。 她守身守心,可偏偏被那個金字塔尖的男人撬開了心房。 他白天跟她裝正經,晚上跟她一點不正經。 直到有一天,有個男人宣稱要帶她走。 而她也不愿再當金絲雀,她想遠走高飛。 沈硯知終于坐不住了。 “聞溪,你贏了。” “我這根高枝,隨你攀。” 他是別人高不可攀的上位者,卻甘愿做她的裙下臣。 聞溪終于恍然,原來自己才是沈硯知的白月光。 為她,他低了頭。 — 階級這種東西,他下不來,你上不去。 最體面的結果就是,君臥高臺,我棲春山。
28.9萬字8 97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