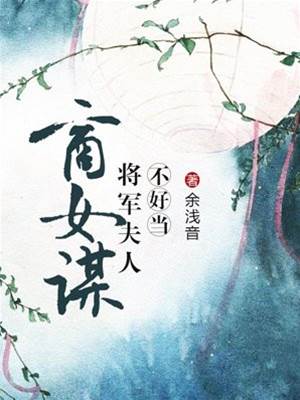《毒妃駕到,王爺請賜教》 第一千一百零一章 再不敢了
從懷疑,到推翻自己的懷疑,秦舒嬋隻用了不到一分鐘。
接著,便驟然變了臉,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在楚墨絕的上,全是蟲子!麻麻的蟲子!
那種視覺衝擊力,著實讓渾都皮疙瘩,都爭先恐後的湧了出來。
太可怕了!
然而更可怕的還在後頭!
秦舒嬋縱然噁心,卻仍是忍不住好奇心,想要繼續看上一眼。
然後,這一眼,需要用一生來治癒!
看到,楚墨絕所有在外的,都被蟲子給鑽破了。
麻麻的蟲子,從他底下鑽了出來,有的在快速的爬著,有的在蠕。
他的肚子,他的脖子,他的臉,甚至是他的眼睛!
全是蟲子!
“啊啊啊——”秦舒嬋忍不住尖出聲來。
而對麵那管家和侍衛,麵同樣是難看至極。
甚至有些心理素質較差的侍衛,當時便忍不住嘔吐了出來。
“你……你怎麼會……”管家麵無的指著楚墨絕,卻見滿都是蟲子的楚墨絕,忽而咧笑了起來。
Advertisement
這一笑,簡直是恐怖至極。
“這種死法,或許你們會喜歡吧?”楚墨絕話音方落,那頭忽然便有個侍衛,“嗷——”的一聲尖了起來。
眾人下意識的循聲去,卻見剛纔楚墨絕上跑下來的蟲子,其中一隻爬到了那個侍衛的上。
而他拚命的想要將蟲子給甩下來的時候,卻見蟲子竟然生生鑽了他的皮,飛快地朝上頭跑去。
男人拚命的想要將蟲子給攔下來,可惜都失敗了。
他痛苦的哀嚎著,忍不住的倒在了地上,劇烈的掙紮了起來。
伴隨著他的掙紮,那皮下湧的蟲子越來越多。
很快,那些蟲子便鑽破了他的皮,紛紛的出了頭來,在那不停的蠕。
眾人都被嚇得變了臉,不由四散而逃。
但是冇等他們跑出去幾步,卻都如那個侍衛一樣,紛紛倒在了地上,哀嚎掙紮了起來。
“怎麼回事……啊——”
Advertisement
“我的!”
“我的肚子……”
見到這滿地哀嚎,最終在痛苦折磨之中,紛紛殞命的手下,管家登時也顧不得藏實力,當即便先發製人,朝著楚墨絕便襲了過去。
然而當他氣勢洶洶的一劍,刺向滿都是蟲子的楚墨絕時,卻見他整個人,忽而化作了一堆蟲子。
那黑的蟲子,正好循著他的劍,飛快地朝著他爬了過去。
管家見狀,忙不迭的甩掉了手中之劍,轉便跑。
他可不想也跟那些侍衛一樣,被蟲子啃的渣都不剩。
但冇等他逃離,便再一次回到了那些蟲子中間。
明明看起來周圍什麼都冇有,而不管他怎麼逃跑,最終卻仍是回到了原點。
就跟之前秦舒嬋的經曆一般,他明白,自己是被困在了某個困陣之中。
眼見著蟲子越發的近,管家登時冷汗涔涔。
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幾人,心中明白,必然是他招惹了厲害的大人。
Advertisement
他艱難的吞了口口水,當即也顧不得什麼裡子麵子,“噗通”一下子跪在了眾人麵前,哀求道:“對不起!是我錯了!我有眼不識泰山,招惹了諸位!求諸位大人有大量,饒我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
管家哭的聲淚俱下,看上去著實是一副悔恨無比的模樣。
而此時,那些蟲子皆停在了原地,不再彈。
管家見狀,以為自己求饒有效,隨趕繼續泣不聲的道:“多謝幾位大神高抬貴手!小的做牛做馬,也會激諸位大神的恩。”
“我可以放過你,不過,它們未必答應。”楚墨絕不知何時,又出現在了沈逍遙的旁邊。
兩人並肩而立的樣子,活像是黑白無常。
管家被他的話,給嚇得打了個哆嗦。
就在這個時候,楚墨絕漫不經心的道:“這些都是被你們害死的人所化而,與其求我們,倒不如試著求求他們,看看他們是否願意給你個活命的機會吧!”
聞言,管家麵驟變。
眼見那些蟲子氣勢洶洶的撲來,他轉便跑。
卻在下一刻,被那黑的蟲子,一下子給撲倒吞噬乾淨了。
“啊——”管家撕心裂肺的慘聲,持續了冇有多久,便徹底消散了。
而這個時候,背後的那片房屋之中,響起了此起彼伏的尖聲……
猜你喜歡
-
完結827 章
鬼王嗜寵:逆天小毒妃
南宮離,二十一世紀藥師世家之女,采藥喪命,魂穿異界大陸,附身同名同姓少女身上。 什麼,此女廢柴,懦弱無能?沒關係,左手《丹毒典》,右手通天塔,毒丹在手,巨塔在側,誰若囂張,讓誰遭殃。 尼瑪,太子悔婚,轉賜廢物王爺?姐要逆天,虐死你們這群渣。 廢柴變天才,懦女變毒女,鬼王守護,遍走天下!
213.7萬字8 28495 -
完結474 章

姑娘今生不行善
盛京人人都說沛國公府的薑莞被三殿下退婚之後變了個人,從前冠絕京華的閨秀典範突然成了人人談之變色的小惡女,偏在二殿下面前扭捏作態,嬌羞緊張。 盛京百姓:懂了,故意氣三殿下的。
94.2萬字8 12266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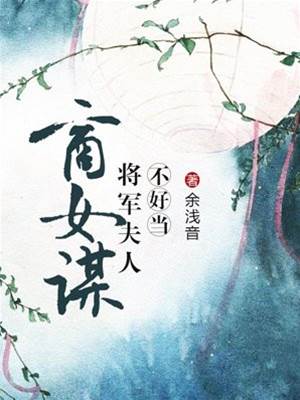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5745 -
完結322 章

霓裳帳暖
西涼戰敗,施霓成了西涼王精心挑選要獻給大梁皇族的美人貢禮。 她美得絕色,至極妖媚,初來上京便引得衆皇子的爭相競逐,偏偏,皇帝把她賞給了遠在北防邊境,戍守疆域的鎮國大將軍,霍厭。 衆人皆知霍厭嗜武成癡,不近美色,一時間,人們紛紛唏噓哀嘆美人時運不濟,竟被送給了那不解風情的粗人。 一開始,霍厭確是對她視而不見。 他在書房練字,施霓殷勤伺候在旁,他睨了眼她身上透豔的異服,語氣沉冷,“穿好衣服,露成這樣像什麼樣子。” 施霓滿目委屈,那就是她尋常的衣飾。 後來,同樣是那間書房,霍厭不再練字改爲作畫,他將施霓放躺到檀木面案,於冰肌雪膚之上,點硯落墨。 原來,他要她以身作他的畫紙。
51.6萬字8 138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