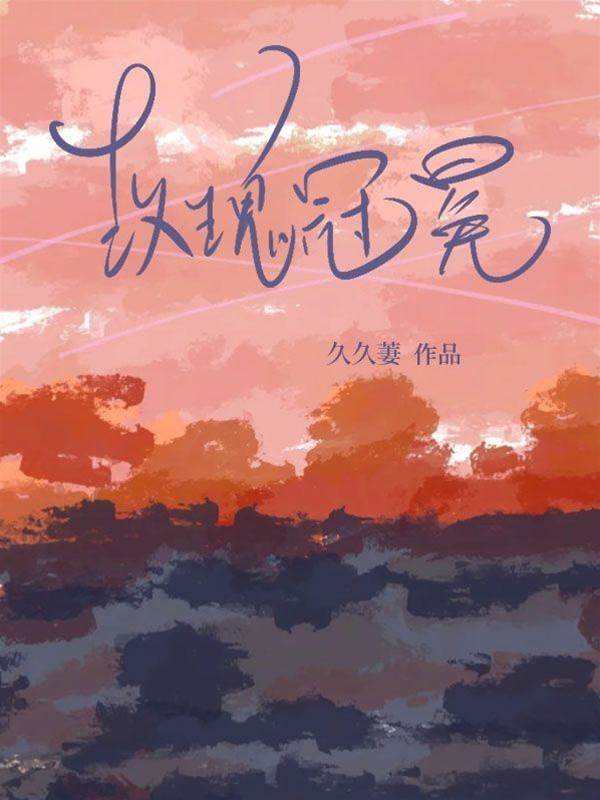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第51章
小寶原本乖乖待在林綰邊, 結果一堆人沖上來搶他的媽媽?
小寶被在里面,他抱著林綰的大,氣得臉頰鼓鼓, 然后他出一只手費力的將搶他媽媽的壞人往外推。
媽媽是他的呀!
歐們到推力, 這才放開林綰,看到小解總面無表的看們,訕訕笑了笑。
林綰扯扯自己的禮服頭發,覺造型都被們弄了。
獎還在繼續, 而且獎品一個比一個大,氣氛越來越熱烈, 每出來一組數字就引來一陣哄然, 中獎的人興得尖。
二等獎也完了,接著是一等獎。
今年的一等獎是五十萬元支票。
公司前面的獎勵全是錢, 但大家都俗氣啊!就錢!
主持人請了五個副總級別的大佬上去,最后出來的是運營部的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
最后一個獎,眾人是最期待的了!
直至現在, 他們還不知道特等獎是什麼。
這時,主持人的說了一段話:“我們策劃年會時,詢問了解總,今年的特等獎以什麼作為獎品,解總說了一段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解總說, 咱們的職員基本來自全國各地, 千里迢迢來到京都,無非是希更好的生活,有個安穩的家,既然這樣,今年的獎就一套房子吧。以后每一年,經濟效益都有增長的話,就以房子作為特等獎勵吧。”
接著另一個主持人也飽含激的說了房子的大概位置,雖然距離市中心有段距離,但是通便利,價格也不便宜,多人斗一輩子都買不起。
不人激得眼淚都出來了,雖然不一定會到自己,但他們都有機會了啊!
這樣大方又懂他們的老板,他們效忠一輩子還嫌!以后別的公司再怎麼中間挖他們都不走!
Advertisement
“接下來有請解總上臺,為我們進行特等獎!”
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中,解禹行邁步走上去。
主持人將話筒遞給他,解禹行言簡意賅的四個字:“繼續努力。”
隨后就開始獎,半點不廢話。
三秒后,解禹行拿出一個球,“1。”
一旁的主持人激的道:“首位是1的朋友們,你們的機會來了!”
又一個數字出來:“2”
再一個數字出來:“3”
歐突然抓著池業峰的手臂,激道:“峰兒,你還有機會!”
林綰頓時問道:“你工號多!”
“12345!”池業峰激的說道,眼睛盯著臺上。
“4!”又一個數字出來,只剩下最后一個數了!
歐他們頓時喊道:“5!5!5!”
書部其他人也跟著喊起來!林綰也握拳跟著激的喊。
大家不知,也好事的跟著呼聲最高的喊,當然也可能是12345這個數字太順口了。
解禹行看了一眼林綰的方向,然后將手探進最后一個獎箱。
主持人在一旁道:“看來是5的數字呼聲最高,究竟是不是5呢?十分之一的機會,我們拭目以待!”
解禹行了半晌,然后拿出一個球。
林綰不自覺秉住呼吸。
“結果出來了!就讓我們解總來為大家揭曉答案吧!”
解禹行沒有賣關子,直接說了一個數字。
“5。”
“啊哈哈哈真是5!峰兒你中了特等獎!”
“恭喜嗷嗷!”
池業峰一臉恍惚,飄飄仙,像是腳踩在云端里。
他得獎了?他真得獎了?他真的真的得獎了!
池業峰不敢置信,欣喜若狂,狂若瘋癲。
啊啊啊啊蹭歐氣果然有用哈哈哈哈哈哈!
Advertisement
歐他們撲上去和池業峰一起蹦蹦跳跳,林綰也想去蹦,但是才走一步,腳步一陣阻力,低頭一看,還有個娃兒仰頭看。
林綰便牽著小寶,站在一旁,為池業峰高興。
這才是真正的錦鯉質啊!特等獎誒!一套房子!
等激的心稍稍平復,池業峰才踩著綿綿的腳步走上臺,期間還得踉蹌了下,引來一陣善意的哄笑。
池業峰發表言,激得語無倫次,最后破罐子破摔,來了個大表白:“我解氏,我要為解氏奉獻一輩子!”
解禹行拍拍他的肩膀,鼓勵道:“好好干。”
池業峰激得眼淚都出來了。不怪乎他那麼失態,房子啊!是房子啊!他在京都有房子了嗚嗚嗚……
完獎后,年會也進了尾聲。大家羨慕的眼神不在林綰上了,轉而落到池業峰上。
最后散場時,大家還緒高昂,其他部門不管悉的不悉的,紛紛跟池業峰道恭喜,順便蹭蹭運氣,希來年被中的是自己。
林綰想和歐一起走,等將禮服一起還回去,但是解先生又不見蹤影了,找半天沒找到,方特助也沒在。
林綰又不放心將小寶給其他人,便沒和他們一起行。
林綰在休息室等了一會兒,然后取出手機給解先生發消息,問他在哪兒?
解先生可能在忙,一時沒回消息,便繼續等著。
穿這麼高的細跟站了那麼久,還跳了舞,早就累了,才不出去找人呢!
左右休息室沒人了,便將高跟鞋了。
“小寶累不累呀?”
小寶的說道:“累呀!”要保護媽媽好累好累的。
林綰頓時心疼的親一口。
已經到小寶睡覺的時間了,累壞了的小寶歪著子靠在林綰上,頭一點一點的,林綰就將小寶摟懷里,蓋上大,哄他睡覺。
Advertisement
單手拿手機看信息,連發好幾條過去,怎麼這麼久還不回消息?不會把他們忘在酒店了吧?小寶要回去睡覺了!
這時門被敲了下,林綰先是問:“誰?”
門外的人答:“我。”
林綰一聽,是悉的聲音,連忙喊道:“請進!”
解禹行推門進來,他剛要說話,林綰就示意他輕聲點。
解禹行一看,小寶已經躺在林綰臂彎里,睡得噴香了。
他走過去,將小寶抱過來,“走吧。”
林綰卸了重任,這才穿上高跟鞋,往前走幾步,頓時被后背出的一大片晃花眼。
解禹行看一瞬,果斷將大出來,批在肩上。
林綰回頭,頓時道:“別冷到小寶了。”說著就要將服遞過去。
解禹行沒接,而是將自己的大下,把小寶包一個小繭,只出小臉,然后開門往外走。
林綰便順手將大搭在手上。
瞅見走廊沒有沒有人,才走出來,跟在解先生旁邊不遠不近的距離。
“……把外套穿上了。”解禹行忍不住道,“下次別這麼穿出門,不好看。”
“哪里不好看了?”林綰不爽,今晚閃亮出場,被迷倒的男子沒有三百也有一百,解先生這是什麼眼。
“你說哪里不好看嘛?”
“背得太多了。”整個背部都出來了,還不難看?料那麼。
“不好看嗎?”林綰扭頭往后看,只看到雪白一片,也沒有長疙瘩啊?歐說的蝴蝶骨可漂亮了!
也不想穿背的,但是小姐姐們讓選,前面還是后面……對比一下,當然是選后面了。
林綰的禮服,前面是水滴形狀,脖子上圈了一圈,白如雪,在燈的照耀下氤氳一層朦朧的圈,多麼漂亮啊!
“把大穿上。”
“不懂欣賞的男人!”林綰嘀咕,不過還是乖乖套上大。
酒店供暖足,還想著等差不多出去再穿上的呢!
常雪麗:“……”
常雪麗并不是故意聽他們講話,只是找半天才找到解禹行,剛追上去,拌正拌得歡的兩人并沒注意的接近。
然后就聽到解禹行說林綰穿得太的話。
常雪麗:“……”看了眼林綰那稱得上保守的禮服,再低頭看看自己半的前,神復雜。
之前林綰的話恰好踩到常雪麗擇偶的雷點,功把勸退。
事后想想又覺得不甘心,甚至覺得那個人是故意這麼說讓知難而退。
常雪麗本想趁這次年會再找解禹行好好談談。好不容易開尋了空找到人,結果就聽到解禹行的話。
沒想到,解禹行不僅僅直男癌,還大男子主義,這簡直了,就算對方有有錢,也掩蓋不了他到所有的雷點。若是功嫁過去,也是離婚的下場,既然這樣,為什麼還要執著追求這麼個人?
或許眼中完的解禹行,是在這麼多年一天天的不甘中,不斷的化了對他的記憶。
常雪麗剛到解禹行附近的腳步一轉,優雅的轉離去。
這邊解禹行和林綰沒注意到常雪麗的到來和離開,林綰還在那里糾結這件禮服到底好不好看的問題。
林綰想了想,還是覺得一百個不服,說服不好看,不就是說不好看麼?
“那你說我好看不好看?”林綰問道。
解禹行完全不想回答這麼稚的問題。
“老解!綰綰,等等我啊!”
林綰回頭一看,竟然是聞哲。
解禹行并不是只和小寶來,他旁邊還跟著穿得極為氣的聞哲。
但是聞哲甫一進場,就隨手拿起一杯酒去尋找合眼緣的聊天了。
為了躲避媽媽的催命式相親,聞哲以解氏集團有很多優秀的才得以逃今晚的相親,跑來年會。
他一直待到散場,本想和老解一起離開,但是人一轉眼就不見了。
他正準備自己走人呢!就看到老解和林綰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果然是個有異沒同的人,聞哲偏不讓老解這麼得意。
“綰綰,你今天很漂亮啊!驚艷全場!呆了!”聞哲站在林綰面前,夸贊道。
林綰頓時心花怒放,“謝謝,你也很帥啊!”
“那是!”聞哲氣的一劉海。
林綰斜眼看解禹行,哼,不和品位特立獨行的人計較。
解禹行:“……”
猜你喜歡
-
完結1690 章

重生后,渣總追妻火葬場
雲桑愛夜靖寒,愛的滿城皆知。卻被夜靖寒親手逼的孩子冇了,家破人亡,最終聲名狼藉,慘死在他眼前。直到真相一點點揭開,夜靖寒回過頭才發現,那個總是跟在他身後,笑意嫣然的女子,再也找不回來了。……重生回到18歲,雲桑推開了身旁的夜靖寒。老天爺既給了她重來一次的機會,她絕不能重蹈覆轍。這一世,她不要他了。她手撕賤人,腳踩白蓮花,迎來事業巔峰、各路桃花朵朵開,人生好不愜意。可……渣男怎麼違反了上一世的套路,硬是黏了上來呢……有人說,夜二爺追妻,一定會成功。可雲桑卻淡淡的應:除非……他死。
215.7萬字8 322367 -
完結1890 章

許你情深深似海
為了得到她,他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將她拉入他的世界。 他是深城人盡皆知的三惡之首,權勢滔天,惡跡斑斑,初次見面,他問她:「多少錢?」 ,她隨口回答:「你可以追我,但不可以買我」 本以為他是一時興起,誰想到日後走火入魔,寵妻無度。 「西寶……姐姐,大侄女,老婆……」 「閉嘴」 心狠最毒腹黑女VS橫行霸道忠犬男
342.7萬字8 29518 -
完結77 章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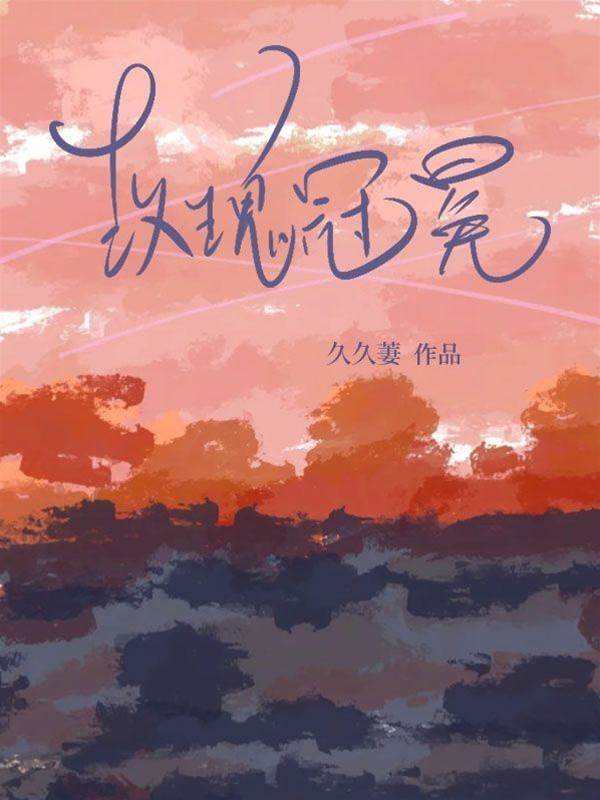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66 章

思餘如潮
孤冷學霸孤女VS冷漠矜持霸總父母雙亡的孤女(餘若寧),十一歲被姑姑接到了北城生活。後來因為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餘若寧嫁了沈聿衍。有人豔羨,有人妒忌,有人謾罵;當然也有人說她好手段。殊不知,這是她噩夢的開端。
15萬字8.18 2415 -
完結159 章

情疤
【落魄千金VS黑化狗男人】溫家落敗后,溫茉成為了上流圈子茶余飯后的談資。 橫行霸道慣了的千金小姐,一朝落魄成喪家敗犬。 是她應得的。 傳聞圈中新貴周津川手段狠辣,為人低調,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 無人知曉,當年他拿著溫家的資助上學,又淪為溫家千金的裙下臣。 動心被棄,甚至跪下挽留,卻只得來一句“玩玩而已,別像只丟人現眼的狗。” …… 溫茉之于周津川,是他放不下的緋色舊夢,是他心頭情疤灼灼。 既然割不舍,忘不掉,那就以愛為囚,相互撕扯。
28.6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