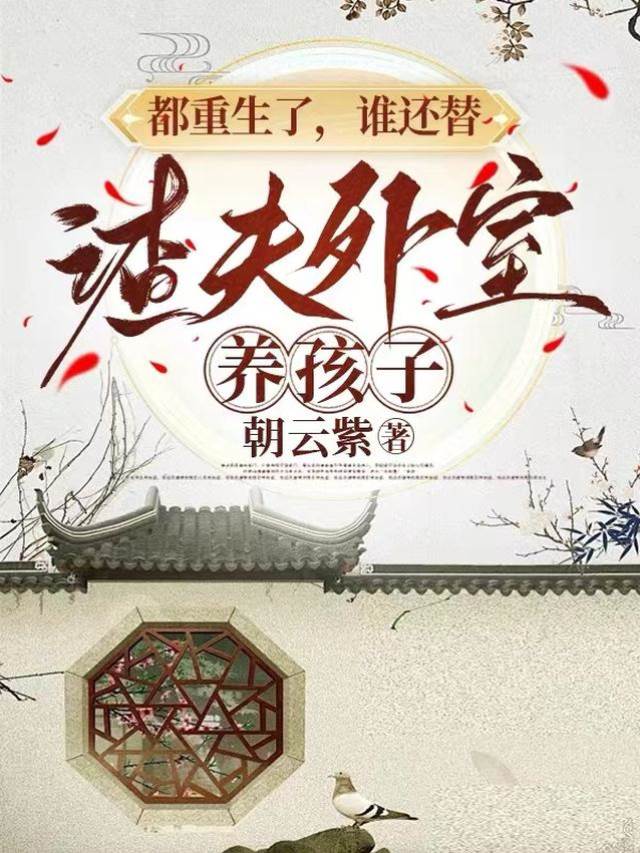《朕和她》 第42章 春蛹(四)
信尚未拆開,便聽城樓上的人道:“趙將軍讀完信,切要遵行。”
趙謙摳掉火漆,迎著風衝岑照抖開信紙,明快道:“你又看不見,怎麼知道中書監寫了什麼,況如今是我領軍,他管不了我。”
岑照含笑扶垣:“憂你赤忱。”
趙謙笑道:“聽不出來這話是誇我還是罵我。”
說著,撐平信紙,低頭掃看,不過幾眼,果真立了眉,一把將信拍在馬背上:“這過河拆橋的無賴!”
城門開,戰俘們被鐵鏈串拷著,從城門魚貫而出,岑照青衫素行在他們旁,徑直走到趙謙的馬下。趙謙耳廓漲紅,有些不願看他,半晌,方遲疑地問道:
“先生……是不是猜到了信裡的事。”
岑照立在馬前,仰頭道:“大致知曉。”
趙謙扼腕:“此次霽山夾道伏擊,之所以能生擒劉必,兵不刃重取雲州,全仰賴先生。我趙謙不過獻匹夫之勇,如今要我將先生視為俘虜鎖拿,我做不到!”
岑照搖了搖頭,鬆紋青帶輕拂於麵。聲平容靜,坦然無畏。
“中書監尚不信我,趙將軍不需為難,遵行即是。”
趙謙恨道:“他還執念十年前被腰斬的那個人。”
岑照向趙謙出手臂,含笑道:“其實也好,中書監尚算有個畏懼。”
趙謙低頭看向岑照手臂。
素袍寬袖垂落,出一雙手腕。
那種蒼白的皮,在男人上並不多見,如同重傷之後大喪元氣,羸弱,卻自風流。
趙謙欣賞岑照這一雅素的氣質,和張鐸的鬱孤絕全然不同。
他人如春山英華。
即便是在堆山的城關外,仍然不染一腥之氣。
“彆回去了。”
“趙……”
“你聽我說!”
趙謙翻下馬,急道:“劉必是謀反的叛臣,押解,必五馬分之刑,你是他僚臣,如果中書監不肯給你一個在曹營心在漢的份,你必將下獄問罪。一旦廷尉獄,張退寒要殺你易如反掌,先生,不是趙謙不自量力,在我的軍中,軍令大過詔書,他這封破信算不上什麼,我今日就可以放你走,你不要再回。如今世道混,各王擁兵自重,各懷心思,你名聲在外多年,不怕冇有容之地。”
Advertisement
他說得言辭懇切,又看了一言呈信的軍士,添道:“你能說一句‘憂我赤忱’,那中書監對我也應該有所防範。這樣,雲州後麵是彙雲關,今夜我親自送你出關,出了關,中書監就鞭長莫及了。”
岑照搖了搖頭:“將軍實不需為岑照違逆中書監。”
“違逆?”
趙謙斥道:“他又不是陛下。說什麼違逆他?”
這話他也就在雲州城敢說,說完還掃了一眼那個呈信的軍士。
“你……退下。”
軍士應聲退走。
岑照欠了欠,抬頭道。
“岑照多謝趙將軍,然,吾妹尚陷。”
趙謙還在心虛,聽他這樣說,旋即喝道:“你也這般英雄氣短?”
岑照笑了笑:“算是吧。殘圄於樊籠,所念之人,隻有那個丫頭。亦孑然一,我若不回去,豈不是難過。”
“我……”
趙謙在馬背上一拍,憤懣道:“唉!我是真不在知道怎麼勸你。你不瞭解張退寒那個人……”
“不是,岑照明白。”
這一句明白,到令趙謙愣了。
要說這世上瞭解張鐸的人,除了他趙謙之外,幾乎都死了。
他一時背脊惡寒。
“我……我勸不了你,不過先生,即便你回了,你家那塊銀子,你未必能見到。我跟你說,張退寒稀罕銀子得很。”
岑照疏朗笑開。
“我知道,若中書監不喜歡阿銀,阿銀活不到如今。”
趙謙抓了抓頭。
似乎明《周易》,擅推演之人,都過於冷靜坦然。
當年的陳孝是如此,如今眼前的這個盲眼人也是如此。比起那些前途未卜的戰俘,他一眼看穿自己的前途命數,窮途末路也好,柳暗花明也好,總之瞭然於,以至於趙謙覺得,自己考量淺而多餘。
“來人。”
“在,將軍。”
Advertisement
趙謙朝後退了一步:“拿下,與叛首劉必一道,押送回”
說完,翻上馬,低頭對岑照道:“了,我就幫不了你了,隻能再徒道一聲珍重。”
“是,也請將軍保重。”
他說完,拱手深作揖。
趙謙見此,口鬱悶,卻也再無可說,索打馬舉鞭,前奔高喝:“大軍城!”
***
雲州城在收編鄭揚與龐見的餘兵,押解戰俘,修繕房屋,安百姓。
則仍然因為張奚之死,而陷在一種士人自危的悲慼之中。
六月,張奚已下葬月餘,依照他的命,以及張鐸的意思,隻用法裹,而後覆亦青席,封木棺。薄葬於北邙山下輝亭旁。張府的大門,直至七月初,才重新開啟,張熠,張平淑等子,嚎啕墓前,大斥張鐸不孝,私行葬儀,囚張奚妻親子,不準後輩親奉老父西歸。
城的個大士族,雖對此頗有微辭,奈何張奚一死,其嫡子張熠並無職在,而張鐸借主喪儀之事,攏理起了整個張氏在的勢力,張氏的各大姻族,包括張平淑的夫家王氏,都為張鐸指摘是命。
加上趙謙在雲州大勝,朝中正由張鐸起頭,議如何迎大軍班師,及一應封賞之事。
張奚鄭揚雙雙死之際,張鐸在朝,已無人可出其右。
一時之間,城中,除了張奚之妻餘氏,以及的幾個子之外,無人敢質疑張鐸行事。
六月底,天氣燥熱。
席銀手執團扇,陪著張平宣在石階上靜坐。
頭頂榆楊鬱鬱蔥蔥,風盈廣袖,木香鼻。
張平宣靜靜地靠在席銀的肩頭,地閉著眼睛。
席銀側頭輕道:“郎主不關著郎了,郎為什麼還是不肯吉見他。’”
張平宣搖了搖頭:“我不知道如何麵對他。也不知道如何麵對母親,餘夫人,還有二哥他們。”
Advertisement
說著,額頭滲出了細細的一層薄汗,席銀忙抬起手中的團扇,替遮日。
“阿銀,彆這樣對我。我也是個罪人。”
席銀搖了搖頭:“奴在這裡容,不就是要照顧好郎主和郎嘛,不然就該被拿去當柴燒了。”
張平宣閉著眼睛笑了笑:“也就你,還肯照顧他。”
“從前,郎不也照顧他嗎?”
“那都過去了。”
說著,睜開眼睛向庭門。
“我和他,再也做不兄妹了。他是一個……”
得牙齒齟齬,肩膀抖。
“是一個冇有心的人。”
席銀順著的目看去,庭院寂靜,半開的庭門外,落著半截影子。
張平宣在病中時候,胡地吐過心裡的事,席銀在旁照顧,也就聽了個七七八八。但並不敢明問張平宣。然而,當張平宣說起‘他是一個冇有心的人。’時,卻忍不住想出聲去駁。
“他……有心的。”
“你懂什麼。”
“奴看他哭過。”
張平宣恒笑了一聲:“我已經有十年,冇有見過他的眼淚了。你怕不是……嗬嗬,看錯了吧。”
席銀垂頭道:“不是,奴看過他上的傷,之前張大人的那一場杖刑,真的幾乎將他打死……郎,奴是一個愚笨的人,奴也不知道,郎主究竟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罪行,要被張大人如此對待。張大人為人父,未免也太不近人了。”
張平宣一怔,隨即直喝道:“住口,不準汙衊我的父親!”
席銀瑟了瑟肩,卻冇有因張平宣的喝斥止聲,反而續道:“即便是奴這樣低賤的人,被犬類撕咬,也想要反擊,被人陷害也想要報仇。可郎主那樣一個權柄在握的人,卻甘願屈辱,承重刑,甚死。奴不覺得,郎主有什麼對不起張家……”
話未說完,席銀隻覺耳旁“啪”的一聲脆響,臉上結結實實地捱了張平宣一掌。
的肩膀原著張平宣的子,原本就冇有坐穩,此時被這麼一扇,便偏撲在地,眼眶頓時紅了。
張平宣看著自己發紅的手,又看向臉頰紅腫的席銀,一時愣住了。
張奚治家森嚴,張家家學傳承百年,上行下效,無一人敢違逆。張平宣雖是流,卻也是自承張奚之教,視父親的言行為圭臬,這麼多年來,雖然心疼自己的大哥,卻也是出於手足之,從來不能認可張鐸在的行徑,是以,也從來冇有真正質疑過父親對張鐸的狠刑。
如今,是第一次聽人這樣大聲的質問張奚。而這個人還是一個份低賤的奴婢。
極怒之下,竟然了手,自己也難免錯愕無措。
“你給我出去!”
席銀忍著眼淚站起,朝行了一個禮。
“是奴放肆,還請郎……”
“出去!”
張平宣抬手指向庭門。
門後那半截人影,微微一晃。
席銀不敢再出聲,隻得退了幾步,捂著臉頰朝庭門外走去。
剛行至門口,卻見張鐸,一素孝立在門後。
作者有話要說:謝在2020-01-2003:10:30~2020-01-2116:29:04期間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哦~
謝投出地雷的小天使:葡萄柚綠茶2個;
謝灌溉營養的小天使:Double2瓶;小蠍、352516381瓶;
非常謝大家對我的支援,我會繼續努力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48 章

穿成極品婦,靠著系統脫貧致富
大淵朝三年干旱,地里的莊稼顆粒無收,吃野菜、啃草根等現象比比皆是,許多人被活活餓死。錢翠花剛穿來,就要接受自己成了人嫌狗惡的極品婦人的事實,還要帶著一家人在逃荒路上,艱難求生。好在她手握空間農場,還有系統輔佐,不至于讓家里人餓肚子。可是這一路上,不是遇到哄搶物資的災民,就是窮兇極惡的劫匪,甚至還有殘暴無能的親王……她該如何應對?歷經艱難險阻,得貴人相助,她終于帶著家里人逃荒成功,在異地扎根。但,瘟疫,戰亂等天災人禍接踵而至,民不聊生。無奈之下,她只能幫著整治國家,拯救人民。最后,竟然陰差陽錯的...
26.1萬字8 16090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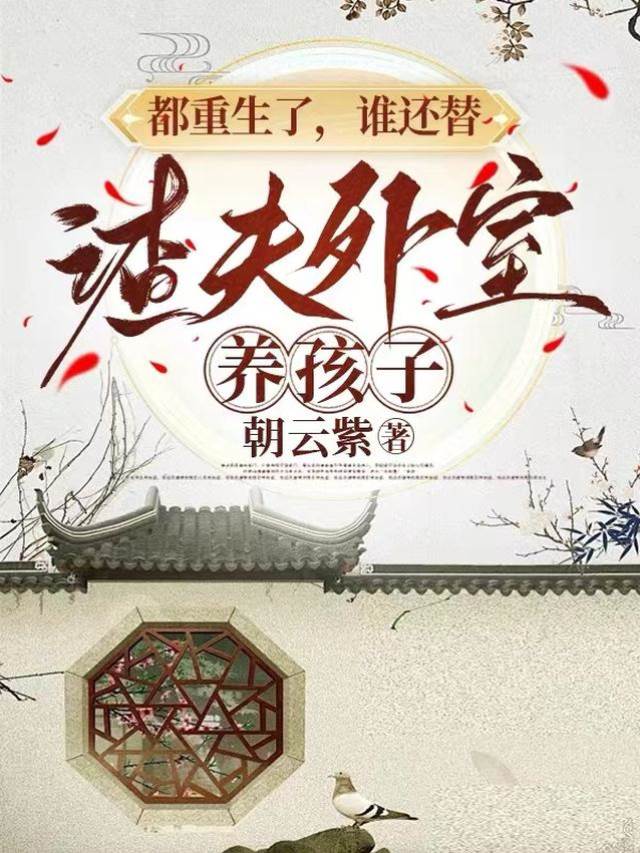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
完結208 章

美艷通房茶又嬌,撩完世子她就跑
全京城都覺得靳世子瘋了!清冷孤高的靳世子,竟然抗旨拒婚,棄權相嫡女於不顧! 坊間傳言,全因靳世子有一房心尖寵,不願讓她受委屈。權相嫡女聽聞,摔了一屋子古董珍玩,滿京城搜捕“小賤人”。 沒人知道,世子的心尖寵,已經逃了。更沒人知道,自從那心尖寵進府,燒火丫頭每晚都要燒三次洗澡水。 遠在揚州的蘇嫿,聽聞此事,在美人榻上懶懶翻了一個身。你幫我沉冤昭雪,我送你幾度春風,銀貨兩訖,各不相欠,你娶你的美嬌娘,我回我的富貴鄉! 至於牀榻上,哄男人說的什麼執迷不悔,非卿不嫁,都是戲談,不會真有人當真吧? 揚州渡口,一艘小船,低調靠岸。靳世子面冷如霜,眼裏波濤暗涌。 蘇嫿!你勾引我時,溫言嬌語,滿眼迷醉。你拋棄我時,捲走黃金萬兩,頭也不回! 這一次,我誓要折斷你的羽翼!把你鎖在身邊!夜夜求寵!
36.3萬字8.33 101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