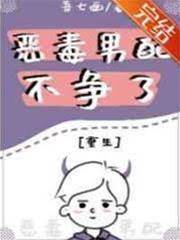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望門男寡》 128
他的直覺告訴他,那個人就在那里,他要找到。
尤銘聽見了張先生的腳步聲,他把扯下來的那顆頭扔在地上,然后一腳踩上去,把頭骨踩碎。
踩碎第一顆頭的時候,尤銘明顯覺到整棟大樓都晃了晃。
他皺著眉,一顆顆的把頭扯下來,每扯下來一顆頭,其它的頭顱就咬得更。
扯下來,只會讓尤銘的皮也被連著扯下來一塊。
尤銘皺著眉,指尖火重新在指尖跳躍,忽明忽暗,他口念咒語,這簇火焰跳躍到最近的人頭上,將這顆人頭燃燒起來,藍綠的火焰格外妖冶,鼻尖還有一腐燒焦的惡臭味。
幾顆腦袋全部燒完,屋里的氣瞬間消散。
“不在這里。”尤銘看了眼云瞳,“你能找到指揮這些人頭的鬼在哪兒嗎?”
云瞳的眼睛里冒著綠,像一頭狼。
他飛奔了出去,尤銘跟在云瞳的后。
走廊上只有他們倆的腳步聲。
而原本應該在門外的張先生現在已經消失了。
追逐著哭聲的張先生現在站在窗臺上,人背對著他坐在欄桿上,一副要輕生的模樣,的很單薄,似乎風一吹就會掉下去,強忍著哭聲,絕中又帶著說不出的凄涼。
張先生此時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一定要安這個可憐的孩。
“你沒事吧?”他的聲音從沒有這麼溫過。
孩穿著深紫的連,在黑夜中有些看不清,一頭黑的長發又長又直,沒有一點澤,幾乎和黑夜融為一。
的聲音很小很輕,聽上去就很可憐,啜泣著說:“沒人在乎我。”
張先生的心臟一揪,好像他也能到孩的緒,那種被所有人無視,不被和期待的覺讓他忍不住屏息,但他還是堅持地說:“不會的,你會遇到在乎你的人,快下來,上面很危險。”
Advertisement
孩沒有回頭,看著夜空:“我好想死啊。”
重復了一句:“好想死。”
“還是活著好。”張先生連忙說,“死了就什麼也沒有了,你連死都不怕,害怕活著?”
孩的聲音輕:“死有什麼可怕的,痛過之后就沒有意識了,活著的話,要日復一日,每分每秒重復那種痛。”
張先生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他只覺得說的真有道理。
“你覺得痛嗎?”孩忽然問他,“活著難過嗎?”
張先生想說不難過,他有自己的事業,雖然跟妻子離婚了,但兩人還是朋友,兒子很懂事,現在在國外深造,畢業后就能到公司幫他的忙,他前面的幾十年把酸甜苦辣全都品嘗了一遍。
但是忽然之間,他想起了很多東西。
和妻子離婚前無休止的爭吵。
最信任的下屬拷走了公司顧客的資料被對手公司挖走。
兒子叛逆期的時候經常離家出走。
事業不能再給他滿足。
破裂的家庭關系讓他心力瘁。
公司七八糟的事讓他覺得不如甩手不干了。
疲憊、勞累和絕一擁而上,讓他忽然覺得孩說的對。
活著太累了。
孩還是背對著他,卻把手出來,也不管得方向對不對,問道:“你要上來嗎?”
“這里的夜景也很好看。”
張先生迷迷糊糊地邁,朝孩的方向走過去。
就在他要邁上臺階的時候,忽然被后的一記手刀敲暈了,一的倒下去。
尤銘手扶住張先生,再把他緩緩放到地板上。
孩依舊沒有回頭,好像半點不為自己失去了費盡心思引來的獵被截胡生氣,溫溫地問:“你也是來看我的嗎?”
Advertisement
云瞳想直接沖上去把孩撕碎,卻被尤銘阻止了。
“沒有害過人。”尤銘輕聲說,“沒有氣。”
這樣的鬼,沒有害過人?
云瞳不太相信,他更愿意相信鬼用什麼手段把氣藏起來了。
有些厲鬼修煉的時間夠長是可以做到的。
孩似乎沒有聽見他們說的話,而是幽幽的問:“活著哪里好呢?”
的聲音里似乎有一力量,能把人帶進最不堪的回憶里。
尤銘站在原地,目有些恍惚。
那是他很小的時候,尤爸爸和尤媽媽幾乎整天整天的不在家,唯一陪伴他的只有一個亞古的玩偶,他也不能下床,只能躺在床上看電視。
在一個節目放完之后,他手去拿放在柜子上的遙控。
遙控有些遠,他把手臂到了極限卻依舊沒有拿到。
他一用力,就從床上摔了下去。
他以一種狼狽又稽的姿勢倒在地上,轉頭只能看見高高的窗戶。
早的尤銘有那麼一刻在想,如果他沒有出生就好了,他活得很痛苦,父母為了維持他的生命也很痛苦。
電視上忽然放起了新聞節目,一位患病三年的絕癥患者選擇了自殺。
當鏡頭對準患者家屬的時候,所有人都哭得撕心裂肺。
但是好像那撕心裂肺當中,又帶著些許輕松。
那個病患只病了三年,而他從出生起就這樣。
病患的家庭況還比他家好,能賣兩套房子去治病。
而為了買藥,他爸要一個人打兩份工,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他媽為了照顧他只能打零工,這樣才能趕回來給他做飯。
他好點之后能去學校,但同學們一開始會因為同而照顧他。
時間久了,同學們就把他當做形人,誰也不想出去玩的時候還要照顧別人。
Advertisement
看著窗戶的那一瞬間,尤銘有種爬上去,然后跳下去的沖。
這樣就不用拖累父母了。
等尤銘回過神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一只腳已經邁出去了。
只要邁上這層樓梯,下面就是川流不息的大馬路。
孩還是沒有回頭,靜靜地坐著,又輕輕地說:“活著太累了。”
然后哼起了曲子,不是尤銘知道的任何一首歌的曲子,更像是隨口哼來的,在寂靜的夜里的聲音很清晰,也很空靈,像一位天賦異稟的歌唱家。
尤銘轉頭去看云瞳,卻發現云瞳表猙獰,但眼淚卻不停地從眼眶中流下來。
他的一張一合,似乎是在祈求什麼。
云瞳這樣的鬼也會被鬼蠱?
尤銘:“為什麼?”
鬼潔白的在欄桿下晃,的子也隨著風而搖擺,
鬼沒有說話,只是這麼坐著。
尤銘開始手決,他要把送到間去。
鬼此時卻突然轉過頭——
并不是尤銘預想中的猙獰面孔,這是個死相很漂亮的孩。
皮蒼白,五平淡,眉也很淡,但五組合在一起,卻人覺得有無數說不出的哀愁。
“我不想去間。”鬼憂愁地說。
尤銘:“你 為什麼會有傀儡?”
鬼抬起頭,看著尤銘的臉,帶著一贊嘆,更多的是悲傷的口吻說:“它們以前陪著我,現在也陪著我。”
尤銘:“它們都被我燒干凈了。”
鬼也不難過,而是充滿了羨慕地說:“真好。”
鬼又問他:“你剛剛那麼難過,為什麼不跳下去呢?跳下去就解了。”
尤銘的臉上忽然勾勒出一個笑容。
就好像一瞬間冰雪消融,綠芽爬上枝頭,他輕聲說:“我死了,我的人和我的人都會難過。”
鬼看著尤銘,確認他沒有說謊,依舊是那副充滿了哀愁的模樣:“真好……”
只是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寒風忽然吹來,氣溫瞬間下降,鬼抬頭向夜空。
黑的旋渦在夜空中型。
一個人從旋渦中走出來。
——江予安來了。
他來的時候,引眼簾的就是尤銘一污的模樣。
江予安面無表,看向鬼。
鬼也看著江予安,然后轉頭問尤銘:“這是你的人嗎?”
尤銘一愣,第一次有人問他這樣的話,于是他笑著承認了:“是。”
鬼輕聲說:“真好。”
鬼閉上眼睛。
就在江予安要出手的時候,尤銘忽然說:“把送到間去吧。”
江予安看著尤銘,黑的眼睛里有說不出的怒火,他看著尤銘上的傷,眼睛更加暗沉,像是一眼不見底的深潭。
尤銘看著江予安。
江予安抿著,本來就不厚的抿了一條直線。
江予安的手一揮,鬼和云瞳就憑空消失了。
他們被送去了間。
尤銘還有些事沒有問鬼,估計只能換個時間再去問了,當務之急是要哄江予安。
腳踩在地上,江予安看也不看尤銘就朝前走,語氣冷:“回去。”
說得很冷酷,但還是轉把尤銘抱起來:“一傷。”
尤銘現在還是不覺得痛,他說:“不疼,我能自己走。”
江予安的角了,有時候他覺得尤銘很可,但這種時候又覺得尤銘很可惡。
江予安沒有放下尤銘,尤銘只能靠著江予安的脯上。
說實話,他的屁被江予安的手臂勒得有點不舒服,也不是疼。
幸好這個點街上沒什麼人,只有掃大街的大爺多看了他們幾眼。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