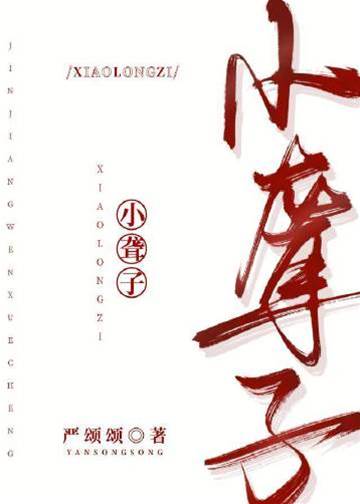《我來自平行時空》 20.20
這離過年宰豬的日子還早,兩頭豬正是長膘的時候,
突然就死在圈裡,
眼珠子還被挖掉了。
趙村長的老伴咽不下這口氣。
哪兒也沒去,就一屁坐在大門口的門檻上,
扯著嗓子又是哭又是罵的,
大都給拍腫了。
村裡傳的沸沸揚揚。
狗不是新鮮事,年年有,豬的極,沒別的原因,
就是不好。
要先想法子把豬給弄暈了才能扛出去,打開鐵欄桿的時候還得輕著點,
靜大了就會逮個正著。
但誰也沒聽過廢那麼大勁兒進豬圈,放著豬不,就眼珠子的。
那眼珠子能吃嗎?
幹那事的人要麼是腦子有問題,不是正常人,要麼就是那人的目的不是豬,是讓村長不痛快。
趙村長的老伴鬧完,這事兒也就過去了。
別說死兩頭豬了,就是最近死了兩個人,村裡也沒砸出多大的水花。
冤有頭,
債有主,
心裡有鬼沒鬼,
自己清楚,
要是行得正坐得端,
走葬崗都不帶怕的。
況且死的又不是自家圈裡的豬,說兩句客套話就差不多行了。
在小飯館裡吃飯的時候,楊志一時興起提了一句。
封北夾的作一頓,筷子放了下來,“豬送去解剖了?”
楊志咬一口油膩的,口齒不清的說,“頭兒,只是死了兩頭豬。”
封北不跟他廢話,“沒有就立刻聯系趙村長,他先不要豬,你帶人過去把豬運回局裡解剖。”
楊志聽明白了,又不明白,他咽下裡的事,“頭兒,挖豬眼珠子的事兒就是村民的普通糾紛,跟劉龍的兇殺案沒關系的吧?”
封北搖搖頭,前言不搭後語,“你還不如他。”
說完就走了。
楊志扭頭,一臉不敢置信,“葉子,我被頭兒嫌棄了嗎?”
Advertisement
呂葉反問,“不然呢?”
楊志到了暴擊,“為什麼?”
呂葉挑著蘿蔔吃,“自己琢磨吧。”
楊志把頭往呂葉跟前湊,“頭兒說的是哪個啊?字旁的,還是單人旁的他?”
呂葉嫌疑的把他推開,“我又不是頭兒肚子裡的蛔蟲,哪知道他的想法。”
楊志胃裡一陣翻滾,他不怕模糊,肝髒掉一地的車禍現場,也不怕爬滿蟲的腐。
就怕蛔蟲。
楊志還小的時候,從裡拽出來過一條白白的大蛔蟲,有十三四厘米,當場嚇尿。
心理影至今沒消。
“葉子啊,不是我說你,你雖然一直留的短頭,也不穿子,長得不可,也不溫,但你是個貨真價實的孩子,吃飯的時候提蛔蟲這東西……”
呂葉打斷他,言辭簡潔,“豬的眼珠子被挖,意圖多半是警告,這裡頭要是沒名堂,鬼才信。”
楊志“騰”地一下起離桌。
呂葉慢條斯理的吃著飯菜,終於清靜了。
楊志火急火燎的聯系趙村長,還是慢了一步,兩頭豬都找人拉去賣了,這會兒豬豬油豬大豬腰子什麼的都被切掉賣的差不多了。
豬都不知道怎麼死的,有沒有毒,就拉去賣。
楊志在電話裡的語氣很不好,他了火,說那樣是在害人。
趙村長覺得他大驚小怪,“楊警,豬是我養的,有病沒病,我還不清楚嗎?”
楊志搔搔頭,“不是,村長,你家那兩頭豬的死因還不曉得……”
趙村長在那頭吃著飯,聲音模糊,但能聽出來不高興,“就是眼睛被挖掉了,脖子上紮了個放掉了,其他地兒沒病。”
楊志氣的把話筒一摔,哎喲臥槽,老頭子真固執,不講理!
他抹把臉,轉頭走到辦公室門口,做了個深呼吸敲門進去,垂頭喪氣的說,“頭兒,豬沒法解剖了。”
Advertisement
封北早料到了,這個悶熱的天氣,死豬放不住,趙村長急著理也是人之常,能將損失減到最小。
兩頭豬全死了,趙村長那心裡頭鐵定疼著呢。
楊志,“頭兒?”
封北倒點兒風油太,“給劉雨打個電話,就說我請吃飯。”
楊志提醒道,“頭兒,你剛吃過。”
一記眼刀掃來,他臉上的抖了抖,“我馬上去聯系人。”
封北把煙盒拿出來,現裡面空了,一煙都看不到,他往桌上一丟,“沒一個省心的。”
不到半小時,封北出現在“有意思”裡面,劉雨坐在他對面,桌上放著一壺鐵觀音,杯子裡的茶水散著陣陣清香,熱氣騰騰。
封北打量著面前的人,面容蒼白,人消瘦了很多,氣非常差。
劉雨沒茶杯,“封隊長,你找我來是有什麼事嗎?”
封北的目裡帶著審視,“你媽媽的口供有假。”
劉雨聽不明白,“不是全都招了嗎?”
封北吹吹幾片還沒完全展開的茶葉,“是故意殺人。”
劉雨的眼睛睜大,“不可能!”
封北喝口茶,“劉士,現在你媽媽只有一條路,就是自,將所有的事全部一五一十的說出來,這麼瞞著,對沒有好。”
劉雨的哆嗦,“不可能的,我媽不可能殺人,只是一時慌了,才會犯下大錯。”
封北說,“為了你弟弟,你媽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關於這一點,我想這世上沒人比你更清楚。”
劉雨張張,沒有反駁。
半響的肩膀,捂著臉泣不聲。
封北瞇了瞇眼,人的反應都很合理,沒有異常,“當初你跟我說,你懷疑你弟弟接活那天有回來過。”
劉雨哭著說,“我只是猜測……我什麼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外地工作,上班上的好好的,接個電話回來就接連出事……”
Advertisement
的緒有些崩潰,“對不起,我失態了。”
封北把紙巾盒遞給,“世事無常,劉士,你多保重。”
下雨了。
不是傾盆大雨,可也不是細雨,劈裡啪啦的敲在磚路上面,出一串串聲響。
悅不悅耳,看聽雨的人。
街上冒雨出行的不,車輛跟行人穿梭在大街小巷,雨點裡的世界變幻莫測。
封北拉下雨披的帽沿,站在巷子裡敲門。
裡頭傳來問聲,是劉秀,問是哪個,聽到封北的聲音,一張臉登時就變得難看起來。
人心複雜。
有時候明知道是那個理,心裡卻不舒坦,不能接,怨這怨那,有點兒不明是非。
劉秀曉得鄰居是職責所在,目的是查出案子的真相,但事關自己的親姐姐,理就只有芝麻大小。
也許過段時間能慢慢接。
但現在不行,一想到姐被關押了,要做好多年的勞改,就沒法笑臉相迎,客客氣氣端茶倒水,真的做不到。
這麼遷怒,確實很不講道理,劉秀心裡明白,在屋簷下了眼睛,“小燃已經睡了,有什麼事改天再說吧。”
封北後退幾步抬頭往上看,二樓有亮,睡個屁。
二樓就一個房間亮著燈,高燃靠在床頭畫畫,邊上放著數學作業本跟草稿紙,他瞧了眼自己畫的櫻木花道,自的覺得很不錯。
雨聲讓一切雜音都變的模糊。
封北進來時,高燃剛在床上找到橡皮,他嚇了一大跳,“靠!”
“封隊長,你這是私闖民宅,知法犯法啊。”
“還不是跟某個小混蛋學的。”
封北了雨披掛在臺的門把手上面,“我在外頭說話的聲音你沒聽見?”
高燃搖頭,“我在畫畫呢。”
封北拿起年上的寫本,“這畫的什麼?”
高燃說,“櫻木花道。”
他補充,“一漫畫裡的主角,打籃球的,特酷。”
封北語重心長,“你以後千萬別學畫畫。”
高燃問道,“為什麼?”
封北認真的說,“會死的。”
高燃,“……滾蛋!”
封北調侃道,“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不過你的畫法不是一般的有特點,怎麼做到的?”
高燃把寫本合上不給他看。
封北坐在椅子上,了上有點的褂子,“你媽說你睡了。”
高燃看過去,男人的線條分明,腹實,那些傷疤讓他看起來很有男人味,又充滿了滄桑,羨慕。
“這段時間看到你,心裡有氣,不過心虛,知道我大姨的事跟你沒關系,你不用管的,過些天就好了。”
封北手撐著膝蓋,上半前傾,誇張的歎道,“你什麼都知道啊。”
高燃,“廢話,我有眼睛,有耳朵。”
房裡靜了會兒,封北隨手拿起數學作業本翻開,“這幾題都錯了。”
高燃想也不想的說,“假的,我不信。”
封北說,“你還是信了吧。”
高燃還是不信,“我回頭找賈帥對對答案。”
封北往後翻,“不怕告訴你,數學是你哥的強項。”
高燃狐疑的盯著男人,“你是學霸?”
封北說,“還行吧,年級前三。”
高燃,“……”
這語氣太欠了。
封北提起了趙村長家死的兩頭豬,包括死法。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喜歡跟年討論案,覺得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專心思考的樣子很可。
其實在非必要的況下,不該把案出去,也不允許。
“你們那邊狗是怎麼弄暈的?下藥?”
“沒聽說有下藥的。”
高燃說,“鄉下有一種草,只長在山裡,樣子看起來跟打豬草差不多,呀鴨呀鵝呀都不能吃的,吃多了會暈過去,大家都知道。”
封北問他,“什麼草?”
高燃說的方言,“三麼子。”
“普通話不知道怎麼說,反正那草我們都不的,鴨鵝也不吃,除非是急了,也有可能是混在其他食裡面。”
封北沉不語。
高燃也不說話,想著事兒。
村長家那兩頭豬死的太蹊蹺了。
他想的出神,不小心倒了床頭櫃上的瓷缸子,水撒了一地。
樓下傳來劉秀的喊聲,“小燃,這麼晚了你怎麼還不睡?”
高燃從房裡出去,打開玻璃窗沖樓下喊,“馬上睡!”
他回脖子,瞥見隔壁張絨那屋的燈還亮著,很用功。
人學習績好是有原因的。
見封北要回去,高燃不假思索,鬼使神差,“晚上你在我這兒睡吧。”
一到下雨天就容易傻。
封北拿褂子的作一頓,“在你這兒睡?”
高燃打哈哈,“什麼?”
封北,“別那麼笑,像個傻子,你哥我沒耳背,聽的清清楚楚的。”
高燃的臉扭了扭,笑嘻嘻的說,“小北哥,我是看外面在下雨,牆壁很,你歲數大了,萬一爬牆的時候摔著,那可就要疼死了。”
封北坐回椅子上,“說的也對,我不該冒那個險。”
高燃點頭,“就是啊。”
封北抬眼瞪他,“就是個頭。”
“我不認床,在你這兒睡不是不可以,問題是我上都是汗,不洗澡沒法睡。”
高燃揮揮手,“那你還是回吧,替我把門窗拉上,拜拜,晚安。”
封北不,“我接了你的提議,安全第一。”
高燃抬頭看著封北。
封北也在看他。
高燃先收回視線,“今天白天的天氣不錯,太能有熱水的。”
封北挑眉,“呢?”
高燃給他建議,“你先湊合一晚上,明早回去再換就是了。”
最後封北穿的是件大衩,掛的空擋。
衩不知道是高燃猴年馬月穿的,腰的皮筋扯壞了,松松垮垮的,他穿著往下掉,就塞櫃子裡面了,翻出來時滿是歲月留下的味道。
封北把衩套上去,腰還行,就是小,繃著。
高燃沒憋住,噗嗤笑出聲。
封北撈起被子蓋在年頭上,“祖宗,你小點聲,不然你媽又要喊了。”
被子裡傳出哈哈大笑聲,人還在。
封北額角青筋一蹦,媽的,有那麼好笑?
他拽拽衩,空間太小了,堵得慌。
高燃的黑腦袋從被子裡出來,臉紅彤彤的,眼裡有水霧,笑的。
“小北哥,你睡哪頭?”
封北,“嗯?”
高燃換了個問法,“你有腳臭嗎?睡覺磨不磨牙?說不說夢話?會不會踢被子?夢遊不?”
封北沒好氣的說,“我只是跟你睡一晚上,不是跟你睡一輩子,嫌這嫌那的,沒完了還。”
猜你喜歡
-
完結178 章
湯家七個O
在这个Omega稀缺的年代,汤家生了七个O。 老大:每天都在闹着要离婚 老二:PAO友还没忘掉白月光 老三:炒cp炒成真夫夫 老四:**的老攻让我给他生孩子 老五:被死对头标记后的幸福生活 老六:ALPHA都是大猪蹄子 老七:老攻今天也在吃醋。 1v1,HE,甜甜甜。
56.5萬字8 9841 -
完結148 章

我死后,成了渣A前夫的白月光
“杭景,離婚吧!”“我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杭景唯一一次主動去爭取的,就是他和宗應的婚姻。可宗應不愛他,所謂的夫夫恩愛全是假象,三年來只有冷漠、無視、各種言語的侮辱和粗暴的對待。只因為宗應不喜歡omega,他從一開始想娶的人就不是杭景,而是beta林語抒。從結婚證被換成離婚證,杭景從眾人艷羨的omega淪為下堂夫,最后成為墓碑上的一張照片,還不到五年。杭景死了,死于難產。臨死前他想,如果他不是一個omega而是beta,宗應會不會對他稍微好一點。后來,杭景重生了,他成了一個alpha…..更離奇的是,改頭換面的杭景意外得知,宗應心里有個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是他一年前英年早逝的前夫。因為那個前夫,宗應決意終生不再娶。杭景:???宗先生,說好的非林語抒不娶呢?我人都死了,亂加什麼戲! 下跪姿勢很標準的追妻火葬場,前期虐受,后期虐攻,酸甜爽文。 完結文:《我養的渣攻人設崩了》同系列完結文:《[ABO]大佬學霸拒婚軟心校草之后》
40.6萬字8 13205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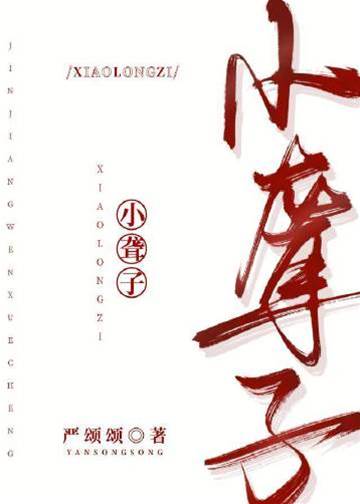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