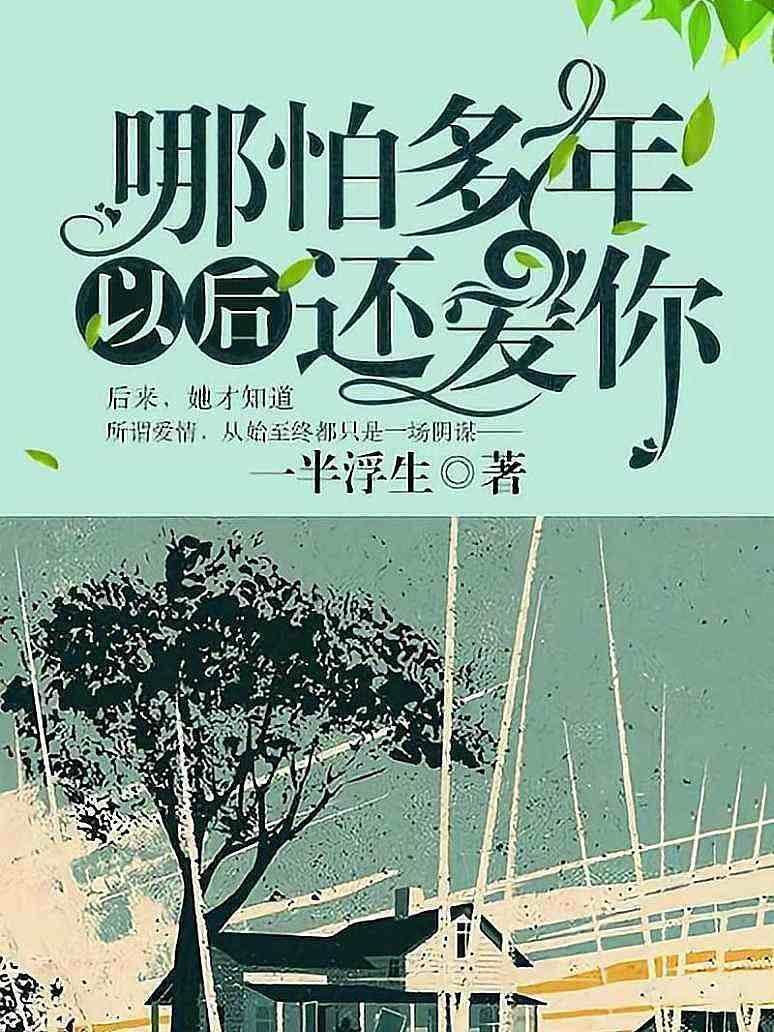《上心》 第60章 正文完
60
沈恕并不擔心許炳章的報復,雖說這人不折手段,但政客最識時務,要是沒辦法永絕后患,不會輕易得罪。
但同樣這樣的人做事過于狠絕,無需沈恕收拾他,遲早也會多行不義必自斃。
對于他來說,他只是想拿回郁松年想要的東西。
那日郁松年坐在小木屋下茫然的表,他至今想起來,都會覺得心臟痛。
不同他還有沈道昌,郁松年在外公也去世后,就真的什麼也沒有了。
好在現在的郁松年,有他也有家。
從公司下班的時候,沈恕將大和紅的圍巾拿起。洗過的圍巾而溫暖,郁松年上常有的氣味,順著圍巾涌進鼻腔。
因為過于明亮,書看出他的圍巾與本人風格不符,卻還是笑著說:“很合適你。”
“謝謝。”沈恕準備離開時,書又補充了一句:“老板,平安夜快樂。”
沈恕這才想起今天原來已經平安夜了,難怪公司今日氛圍有種的歡樂。
從公司走出,街邊的裝飾已經盡數亮起了燈,巨大的圣誕樹立在公司大堂,連保安的脖子上,都掛了一條紅的小圍巾。
沈恕拉著圍巾掩住臉,回到車上后,才想起來他應該準備一份禮。但是今天郁松年他去學校找他,從時間上來看,好像也來不及了。
郁松年現在每日還是騎機車上班,不知為什麼,他就是不喜歡開車。不過自從跟沈恕在一起后,沈恕覺得機車的安全不夠高,往往都是自己接送郁松年。
如果實在沒有空,便會讓司機來送。
從前他會在公司把工作都理完再回家,現在則是把工作帶回家中理。
書房是他和郁松年相最多的地方,哪怕什麼話也不說,一個辦公,一個畫畫看書,也怡然自得,氣氛和諧。
Advertisement
開車來到母校,沈恕下車的時候,只覺得鼻尖一涼,一點雪花在他臉頰上化開。
他抬頭一看,原來是下雪了。
沈恕拿出手機,看著他和郁松年的聊天消息,車上不方便回復,郁松年便發來了語音。
他喜歡重復聽郁松年說話的聲音,也喜歡看郁松年發來的文字。
拿著手機邊看,邊不自覺地微笑,來到校門口時,便被人抓住了胳膊,輕輕地往一旁拉去。
沈恕抬頭,是撐著傘的郁松年。對方用指腹抹去他臉頰上被雪打過的痕跡:“看什麼呢,這麼專注?”
“在看你啊。”沈恕如實回答。
他們之間的來往,好似從數個月前換了過來。
現在總是表現得很直白的是沈恕,而郁松年往往都會被沈恕的直白,鬧得面紅耳赤。
好比現在,郁松年紅著耳垂:“明明就是在看手機。”
沈恕亮著手機屏幕,讓對方看清頁面,正是他們兩人的聊天記錄。這下郁松年就不只耳朵紅了,連臉也紅了。
他們并肩而行,往教室的方向走。
“怎麼出來了,不在教室等我?”沈恕問道。
郁松年說:“看天氣預報說今天會下雪,雨夾著雪太冷。又想起你早上出門沒拿傘,就過來接你。”
外面雪逐漸大了起來,冷風刺骨,直到進開了暖氣的室,沈恕才松了口氣。
他解開圍巾的時候,看著郁松年一直著圍巾笑,不由莞爾道:“你手藝很好,志鈞說他大學的時候也收到過一條,戴不過一個冬天就散開了,還很冷。”
掉外套,搭在了門口的椅子上,沈恕穿著黑的高領,挽起袖口,出蒼白的手臂:“你今天讓我過來幫忙,是需要我做些什麼?”
Advertisement
郁松年站起,走到了最中央那座被明塑料裹住的雕塑前,他手扯落了塑料袋,雕塑的全樣,便猝不及防地落了沈恕眼里。
金屬和石膏的結合,荊棘與人像的糾纏,窗口化作枷鎖,鹿角纏住軀,而這雕塑的臉頰模樣,一眼便能知道是他。
只是這座雕塑的臉頰,被一抹紅料勾勒了眉眼,就像蒙住視線的紅綢。
沈恕被其中藏又骨的給沖擊得臉頰滾燙:“這……你什麼時候做的。”
郁松年道:“結婚之前吧,還差一點需要完的東西。”
“是什麼?”沈恕并不認為自己能夠幫助郁松年完雕塑,他甚至沒畫過畫,如何能夠幫忙。
但是郁松年端出磨好的瓷泥,示意沈恕用手出一個心的形狀時,沈恕這才確認,郁松年是認真的。
他是真的要沈恕胡作出來的東西,為自己作品中的其中一環。
即使沒弄過,但郁松年的要求沒什麼技含量,沈恕很認真地完,非常嚴格地按照比例,將心得很勻稱。
一個心并不難,沈恕很快就完了,他看著郁松年把那顆心放好后,便帶著他出了課室。
在學校的走道上,他們還遇到了一些學生,見到沈恕和郁松年手拉著手,皆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樣。
鬧得沈恕幾次都想把手回來,卻被郁松年死死攥住。
他轉過頭來:“躲什麼?他們都知道你是我老公。”
沈恕被一聲老公給震住了,手心瞬間都出了不汗。
只因昨天他在床上幾乎被弄暈過去的時候,郁松年也在他耳邊喊了聲老公。
大概與他聯想到同樣的事,郁松年手掌的溫度也上升了不,不過他卻沒對沈恕做任何事。
Advertisement
一來場所學生太多,影響不好。二來走廊溫度不高,他怕沈恕冒。
沈恕當然不知道郁松年在想什麼,他以為這人好歹是在學校,為人師表得作出模范,應該不是他想的那樣,故意喊他老公。
“那顆心是得放進窯爐了嗎?”沈恕也是看過電影,多知道些。
郁松年樂了:“還要等它風干,上,最后才能放進窯爐里,還需要看上一整晚的火,直到第二天才能知道不。”
聽到這繁雜的步驟,沈恕為難地想了想自己的行程:“其他的步驟我倒是能空來,不過我不確定能不能熬得夜。”
郁松年笑著了他的手指頭:“不用這麼急,瓷這種東西,本來就越慢越好。”
“而且,有我在呢。”他怎麼舍得讓沈恕熬大夜。
來日方長,他們多的是時間,把這顆心制。
即便第一次不功,也還有很多很多次的機會。
雪已經停了,學校的樹上掛滿了燈,可能是因為節日的緣故,校園里熙熙攘攘的,相當熱鬧。
郁松年把沈恕帶到了學校的小禮堂,雕塑系和其他幾個藝系策劃了平安夜的活。
說是活,實則也是派對。
臺上有樂隊和歌手,臺下有舞廳和啤酒。
郁松年在學生里玩得很開,不多時便被學生們起哄上臺唱歌。郁松年很大方地上了臺,唱的是一首粵語歌,張敬軒的《靈魂相認》。
唱歌的時候,目錯也不錯地著臺下的沈恕。
低沉地唱,安靜的歌曲中,用曲和詞,聲音與目,將這滿腔意傾瀉。
郁松年并未在臺上表白,而是唱完歌后,就快速地回到了沈恕邊。
他總是很說或喜歡,但每一次擁抱,每一記落在沈恕上的目,都好像在說著我你。
在學生們起哄更多之前,郁松年拉著沈恕躲了出去。
學校里能逛的地方,也就那麼點,到底還是來到了場,他們就如每一個校園人般,在場的走道上漫步。
時猶如倒錯,沈恕又似回到了當初大學時期,不同的是,現在邊是他最想要的人,他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雪又下了起來,這一次他們兩人都沒有傘。
但有兩個人的溫度,好像雪也沒那麼冷了。
郁松年吻去沈恕鼻尖的雪,將一封信塞進了沈恕的口袋里。
“現在不要看,等回家再看吧。”郁松年低聲道。
沈恕說好,同樣的,他知道郁松年給他的是什麼。
是他等了許久,又來得剛好。
是過去漫長歲月里的,又是如今以及未來時間里,會不斷獲得的事。
是封書,也是場。
是最浪漫的事。
沈恕將手里的東西藏進了西裝口袋的側,住心臟。
在平安夜的鐘聲里,郁松年彎著眼睫,雪花從他笑起的眼尾落下,被風卷著送到沈恕邊。
“走吧,我們得去更好的地方。”
【書】
那是一副畫,字句倒是不多,紙張泛黃,打開時殘留著墨水的香氣。
鋼筆描繪著沈恕的正臉,是十九歲的,笑著的沈恕。
或是繪者帶著無盡意的遐想,又或者是他親眼見過,沈恕對他笑的模樣。
字句也很平實,不像封書,倒似封信。
十九歲的郁松年寫下的信,二十九歲的沈恕收到了。
“買了前往你城市的機票,希貿然出現在你面前時,你不會被嚇到。
前幾日我第一次嘗試做雕塑,以為練你的模樣,就能做得像你。
可惜都失敗了。
我在想,如果能夠看著你,會不會做得更好。
思念中的廓總有差錯。
想見你。
哪怕只有一面都好。”
完。
--------------------
到這里結束了,高中生的郁松年和沈恕,婚后日常的甜甜,還有副cp林志鈞許慕深,盡在番外,敬請期待。
猜你喜歡
-
完結87 章

明天去看雪好嗎
新婚不久,朋友們來暖房。有人喝多了,問新郎:“喜歡一個人喜歡了那麼久,就這麼放棄了,甘心嗎?”正要進門的顧南嘉呼吸一滯。門縫裡,孟寒舟慵懶浸在月光之下,俊朗的半張臉風輕雲淡,半晌沒應聲。顧南嘉心寒,回想在一起的諸多細節,通通都是她主動。他從來都只是一個字:“好。”溫柔的背後竟是隱情。顧南嘉學不會矯情,瀟灑轉身。算了,人先到手,來日方長。-結婚幾個月後,某一天,孟寒舟忘記了她大姨媽時間。顧南嘉默默掉眼淚:“你果真愛的不是我。”她把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推到他面前。孟寒舟放下手中的杯子:“想清楚了嗎,小哭包。”小哭包?“除了昨天,我還有什麼時候哭過?”顧南嘉跳腳。某人溫柔地撕掉離婚協議:“暖房酒那天。”朋友醉話而已,他根本不走心。她卻站在門口哭了。於是他認真回答:“沒放棄,就是南嘉。”可惜她轉身了,沒聽到。
12.1萬字8 14588 -
完結202 章

嬌寵!小孕妻被醫生大佬寵上天!
【甜寵 先孕後愛 爹係男主 年齡差】“請問打掉孩子需要多少錢?”竺語語小心問道。坐在對麵的醫生卻急了:“敢把我的孩子打掉試試!”一周後,領證。一個月後,坐在腿上抱著查成績。兩個月後,晚上在車裏親親抱抱。三個月後,吃醋當眾要親親竺語語捂住他的嘴:“你人前那副高冷的樣子去哪裏了?”宋耀之表示不懂:“我在老婆麵前不當人”
35.6萬字8 57674 -
完結2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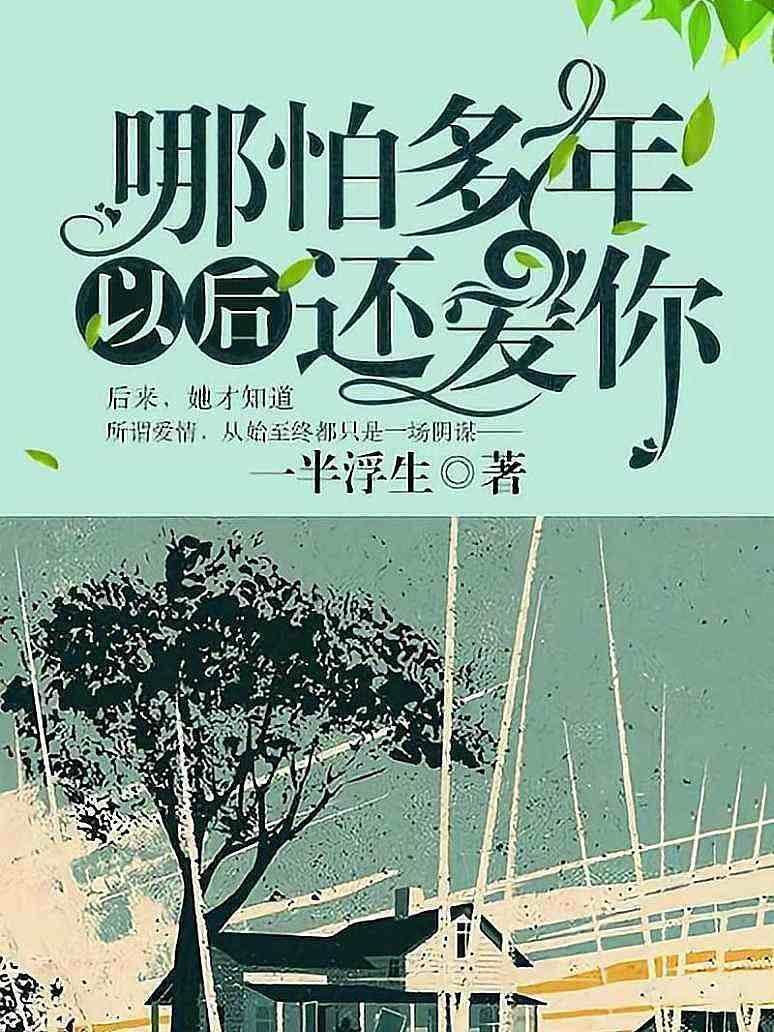
哪怕多年以后還愛你
“生意麼,和誰都是談。多少錢一次?”他點著煙漫不經心的問。 周合沒有抬頭,一本正經的說:“您救了我,我怎麼能讓您吃虧。” 他挑眉,興致盎然的看著她。 周合對上他的眼眸,誠懇的說:“以您這相貌,走哪兒都能飛上枝頭。我一窮二白,自然是不能玷污了您。” 她曾以為,他是照進她陰暗的人生里的陽光。直到最后,才知道,她所以為的愛情,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陰謀。
107.8萬字8 3589 -
連載214 章

離婚冷靜期?鹿小姐上訴凈身出戶
【先婚后愛+追妻火葬場+雙潔】【霸道毒舌財閥太子爺vs清醒獨立大小姐】 季司予遭遇車禍,重傷腦子成了白癡,是鹿晚星頂住壓力嫁給他,不離不棄護了他三年。 鹿晚星一直以為季司予愛慘了她,直到季司予恢復了心智,她才明白,他的偏愛自始至終都是他的初戀白月光。 她不再奢望,搬出婚房,決定離婚。 所有人都嘲笑她,“鹿晚星瘋了吧,這時候公開上訴離婚,她以后活得下去嗎。” “她硬氣不了多久的,估計沒幾天就得后悔死,然后灰溜溜跑回去。” 眾人等啊等,沒等來鹿晚星后悔離婚,倒是等來了季司予一步一跪,再次跪上真清寺的直播視頻。 視頻里,男人每一次屈膝叩首,都紅著眼圈,哽著聲線,重復一句當年誓言。 “鹿晚星是季司予的全世界。” “鹿晚星和季司予,生生世世不分離。” 他一雙膝蓋浸了血,終于跪上真清寺山頂,卻看見他的死對頭溫硯禮,手捧玫瑰,正在向鹿晚星表白。 矜傲如他,卑微地抵著女人的手指,“他要做你男朋友,我可以……不要名分。” “鹿晚星,這一次,你玩死我都行。”
39.8萬字8 47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