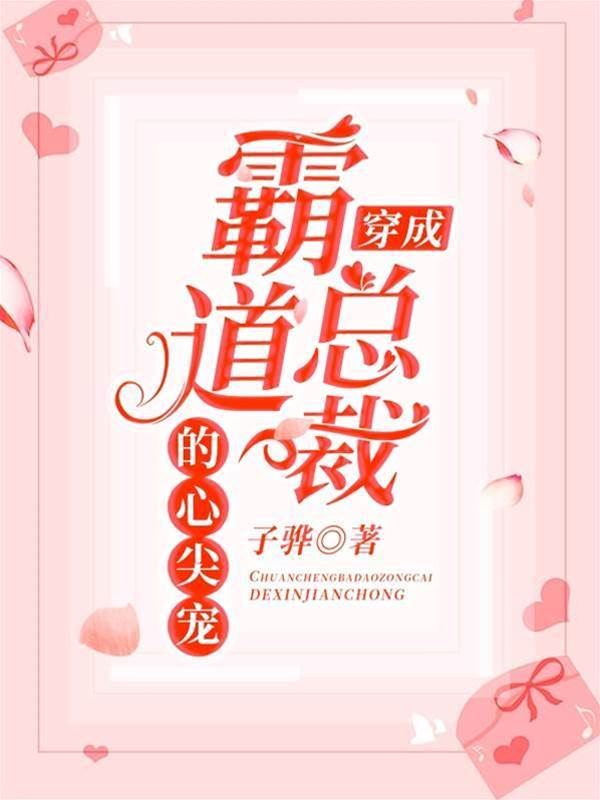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黑蓮花攻略手冊》 第66章大地裂隙(一)
夜深了。
窗戶開著條,窗欞上還夾有打卷的落葉。冷風吹進來,吹得那落葉咯吱作響,懸起的紗帳鼓了起來。
側躺著的十娘子睜開眼睛,臉灰白似鬼,額頭上布滿細的汗珠。
慢慢地息著,每息一下,都發出艱難的嗬嗬聲,口起伏劇烈,那白皙滿的,幾乎掙出低垂的坦領。
那雙纖長麗的手向上索著,扶著床頭,掙紮著坐起來,腳上胡蹬住了地上的鞋。
窗外夜清寒,照得屋一支細細的蠟燭愈加慘淡。
扶著額頭,天旋地轉地走著,像一個酩酊大醉的人左搖右擺地走在街頭。
“呼……呼……”一路走,一路著氣,麵容灰白,分離的雙眼凸出,布滿了。
慢慢繞過了繡青竹的屏風,屏風後是一張小床,床頭還擺著一隻紅漆撥浪鼓,幾隻小布偶。
床上沒有人。
頭痛驟然增加,猛地扶住屏風,才沒讓自己倒下,軀卻靠得那屏風“咯吱”向右推移了幾米。
“母……”倚著屏風,艱難地出手,似乎想喊些什麽,“阿準……”
用力地喊,卻沒發出什麽聲音,自然沒有人答的話。
李準和娘都不在,這座空屋,是專為一人準備的牢籠。
兩眼死死地瞪著那空的小床,良久,視線下移,落在床旁邊的牆麵上,再轉,見了閉的門。
窗欞裏卡著的落葉被風吹得哢噠作響,門上著的澄黃符紙,在風中卷起一個小小的角。
製香廠裏燈火通明,遠遠去,星星點點的紅燈籠宛如赤紅的遊蛇,蜿蜒到了遠方。
妙妙有些震驚:“李準不是說,製香廠隻在白天開工嗎?”
柳拂麵警惕,雙眼盯著前方的燈火,將手指在上,無聲地比了一個“噓”。
Advertisement
懷裏的小孩睡得正香。
主角團放輕腳步靠近,沿著草叢中鋪好的石板路來到製香廠前。
晚風將木屋上懸掛的盞盞燈籠吹得左右搖晃,燈籠發出暗淡的紅,燈下有無數散的人在忙碌地走,在地麵上投下晃錯的影子。
詭異的是,人們來往忙碌,卻沒有談聲,甚至連腳步也難以察覺,一切悄無聲息地進行著,靜得能聽見風過樹叢的聲音。
慕瑤抿,抬手指向了角落,順著的手指看去,紅的黯淡燈籠下,四五個人圍聚一堆,拿著鐵鍬和鏟子,飛速地上下揮舞,影子虛化無數道,一時間群魔舞。
飛揚的塵土帶著草、泥屑一起堆了一座小山丘,未幾,地上被挖出一個大坑,挖土的工人們飛速地扔掉鏟子蹲下來,七手八腳地從裏麵抬出了什麽。
一團濃重的黑氣從土坑中向上湧去,幾乎遮蔽了他們的臉。
“這是什麽?”妙妙瞠目結舌。
“是死人的怨氣。”慕瑤盯著那一團向上漂浮的黑氣,眉頭皺。
那一團烏雲似的黑氣,轉瞬分了四五飛速消散在空中,出工人們的臉。燈下,那幾張臉麵無,鼻孔還慘存著幾縷未散的黑氣。
……他們居然將死人的怨氣吸走了!
幾個人手一鬆,那被刨出來的摔落在地上。
經年風吹雨打,被泥土掩蓋,那上的服已經看不出,幾乎和土地混為一,從袖口、下擺叮叮當當地掉出幾森白的白骨。
沒有那一怨氣支撐,死人也隻能腐化為普通的白骨,就此而散了。
工人將地上白骨攏好幾堆,幾個人用下袍兜著站了起來,像兜水果一般輕鬆地兜了回去。
Advertisement
慕瑤跟了幾步,雙目在月下閃著亮:“看看他們去哪裏。”
柳拂蹙眉看著懷裏睡的楚楚。
慕瑤補道:“拂在這裏等吧,看顧好楚楚,別嚇著了。”
此距離製香廠還有十幾米距離,那些詭異的景象看不真切,還有幾叢矮樹作為遮蔽,進可直製香廠,退可遠觀防,是個較為安全妥當的地方。
柳拂點點頭,看著慕瑤囑咐道:“你們小心。”
幾人跟著工人的腳步向前挪了幾步,恰看到他們閃進了屋,彎下腰,將懷裏的白骨一腦兒倒進火燒得正旺的灶膛裏,那些骨頭殘渣如同進了油鍋的酪,迅速融化了。
——這實在是挑戰現代理。要知道,即使是火葬場焚化爐,也至是從兩百攝氏度開始升溫的,要想將堅的人骨骼焚化,至需要將近一千度。
淩妙妙指著爐子下不斷散落的灰燼:“慕……慕姐姐,這個也是因為沒有怨氣支撐嗎?”
的聲音有些抖,旁的慕聲突然站得離近了些,幾乎是在了邊,一眨不眨地觀察的臉。
旁是火,上還穿著秋天的襖子,妙妙讓他靠得熱乎乎的,反手將他往旁邊推:“我聽慕姐姐說話呢,你別搗。”
“……”慕聲確認臉上沒有毫畏懼,完全不需要安,剛才問話,說不定隻是興地抖……
他沉著臉退到了旁邊。
慕瑤嚴肅地點點頭:“這些上所有的怨氣已經被吸走,便一活氣也沒有了,這樣的,與地上的落葉和塵土沒有分別,輕易便可瓦解。”
淩妙妙點點頭,心中慨,浮舟的世界設定真是天馬行空啊……
灶上還熬著中藥。
Advertisement
李準曾經說過,他的製香廠生產香篆,不單要用最好的檀香樹皮,還要加安神靜心的中藥,眼前這些藥,想必是需要整宿熬製以備翌日使用的。
灶膛裏的骨頭越堆越多,燒的灰塵越堆越厚,不一會兒便塌了下去,末從隙裏跌了出來,灑在了地上。
看守爐火的約可見是個年邁的老婦,遲鈍地低下皺紋布的臉,裏嘟囔著什麽,似乎在抱怨這些灰塵弄髒了地麵。
慢慢彎下佝僂的背,將地上的骨灰攏了攏,抓在了手心,隨後,掀開砂鍋蓋子,倒進了正在咕嘟的中藥裏。
幾人麵一變。
香篆裏的骨灰,原是這麽來的……
月從窗口出來,如冷霜般打在牆上,一隻纖細修長的手抖著扶著牆壁,隨即是一個高挑滿的影,彎著腰,跌跌撞撞地扶著牆靠近房門,每走幾步便要停下來,氣籲籲。
另一隻手上,抓著一張撕下來的符紙,符紙被手心上的汗水浸了,皺一團,褶皺的纖薄符紙上還有約可見的跡。
掙紮著,東倒西歪地扶著牆壁,丹蔻在牆上拓出深深的印子,指甲因為用力而發白。
還有幾步,就可以走出房門了。
“慕姐姐……”
“阿姐!”
一個沒注意,慕瑤已經滿臉嚴肅地走上前去,徑自推門進了屋。
妙妙頭皮一陣發麻,跟著慕瑤闖進了屋裏。
慕瑤已經站定在燃燒的火爐前,定定盯著。那老婦守著爐子,似乎渾然沒有覺察到來人,還在不斷地彎腰從地上攏起多餘的骨灰,撒進砂鍋裏,作遲緩而機械。
“請問……”
試探著開了口,可眼前的人沒有一點反應,就好像他們之間,隔了一層厚厚的牆壁。
慕瑤一把抓住老婦不停作的胳膊,抬高了聲調:“看著我!”
老婦抬起滿臉皺紋的臉,渾濁的眸中沒有焦距,胳膊被慕瑤抓著,可手指還在重複著機械的作,就好像一個被設定好程序的機人。
慕瑤猛地撒開手,老婦跌在地上,又一聲不吭地爬起來,接著重複撿骨灰、倒骨灰的工作。
“……”
慕瑤冷靜地轉過臉來,一左一右往外推著跟在後麵的慕聲和妙妙,低聲音:“這些確是白天在製香廠勞作的工人。他們都被人控製了,我們走。”
甫一出門,果然又有幾個人兜著新的骨頭殘渣進門了,匆匆的影與他們肩而過,就好像不存在於同一個時空。
不遠,三三兩兩聚攏的工人,無聲地揮舞著鐵鍬,一朵朵暗淡的紅燈籠搖曳著,牆上地上充滿紛的影子。
邁出了房門,先左腳,後右腳,隨即立刻撲倒在門口,靠著牆劇烈息著,散的鬢發被汗水沾,打了卷兒,淩地在額角。
仿佛一個溺水的人,掙紮到了岸邊,貪婪地呼吸著久違的空氣。
走廊裏空無一人,月微弱至極,幾乎坐在濃重的黑暗中。
手中團的符紙滾落到了地上,徹底變了普通的廢紙。
“阿準……楚楚……”喚著,終於可以發出聲音,扶著牆站起來,沒有注意地上幾點閃爍著淺淺的銀。那幾個點,恰好連一個圈,圈縷縷的線若有若無,像是捕魚的網,又像是看不到底的深淵。
腳上繡鞋掉了一隻,狼狽不堪,著一隻腳,拖著擺,無聲踏了那一個圈,喊道:“阿準,你們在哪裏?”
隨即,李府燈火一盞接一盞亮起,夜也開始有了窸窸窣窣的聲音。
娘披著服最先跑進來,手裏端著一隻燭臺,睡眼惺忪,見了眼前人,嚇了一大跳:“夫人,您這是怎麽了?”
“楚楚不見了……”十娘子分得極開的雙瞳中出一恐慌,向前踉蹌了幾步,彩旗般鮮豔的擺掃過了銀亮的圈。
慕瑤跑得越來越快,後跟著妙妙和慕聲,三人幾乎是拔足狂奔,遠遠地看見了樹叢背後柳拂抱著小孩的影。
柳拂正皺眉頭,方才,布在十娘子房門口的七殺陣傳來應,有人毫發無損地踩過了陣。
七殺陣是捉妖人嘔心瀝發明的手段,專為大妖準備,妖氣越重,困得越,七步之必殺其銳氣,不可能對十娘子毫無反應,除非……
慕瑤的臉剎那間煞白,連都失去了,慕聲形如同一道黑的閃電,幾乎瞬間移到了柳拂邊,依然晚了一步。
熱的,淅淅瀝瀝,順著他的袍流下去。
柳拂緩緩低下頭,小孩纖細的手臂已經穿他的膛,雪白的小臉滿是點,總是發紫的此刻是詭異的紅。
寶石般的黑眸裏閃爍著冰冷的酷,慢慢地牽拉角,出一個甜的微笑:“柳哥哥,謝謝你一路抱著我。”
猜你喜歡
-
完結896 章
紈絝王妃要爬牆
風清淺這輩子最為後悔的是自己為什麼喜歡爬牆,還砸到了不該砸到的人!大佬,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就放過我好不好?某王爺:嗬嗬,調戲了本王就想走,小流氓你太天真。招惹了他,就是他的!直接將人搶回家!風清淺:以為我會這樣屈服?哦嗬嗬嗬,王爺你太天真!爬牆的某女一低頭,就看見某男溫柔笑臉:“王妃,你要去哪裡?”風清淺:“……”將人抓回來,某王當即吩咐:“將院牆加高三尺!不,加高三丈!”某王爺看著加高的院牆,滿意的點頭。
153.6萬字8 49481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3730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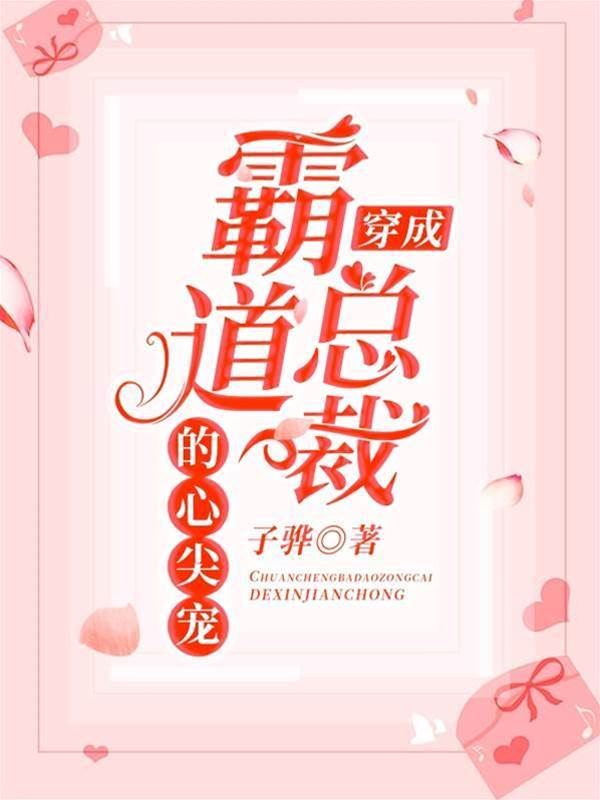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