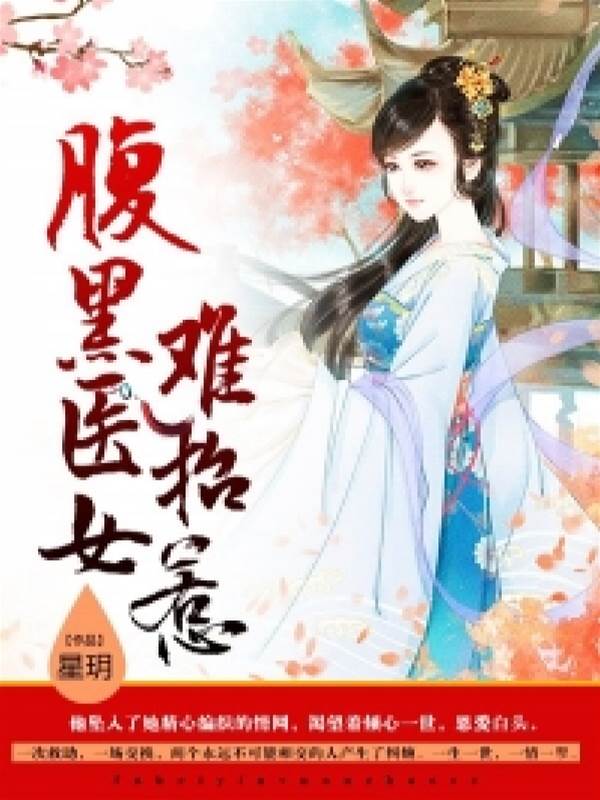《麻煩》 第137章 搬家
袁長卿卻忽地一把攥住了手,且還皺起了眉頭,將他的額又抵到珊娘的額上。珊娘想要往后撤,卻他兜著后腦勺按住,道了聲:“別。”
“怎麼了?”盯著近在咫尺的那張臉,珊娘不解問道。
袁長卿抬起頭,又以手代替了他的額,覆在的額上,皺眉道:“你在發熱。”
“是嗎?”珊娘撥開他的手,了自己的腦門兒,卻是一點兒都沒覺到有什麼異常。
袁長卿翻過的手腕,替號了一會兒的脈息,道:“有點快。是不是昨兒晚上凍到了?還是累的?或者……是我傷到你哪里了?”
珊娘的臉又紅了。猛地回手,“沒有的事!你什麼時候又懂得給人看病了?!”
袁長卿卻再次拉過的手腕,一邊按著的脈門一邊皺眉道:“當初只跟我師父學了一點皮。現在倒有點后悔沒能堅持下來了。”
Advertisement
在的那個“夢”里,就是病死的。雖然理智的一面令他并不怎麼信的那個夢,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認,若他倆真是在那樣一種況下的親,他和十三兒很有可能就是那樣的一個結局。因此,雖然上說著不信,他心里卻有種說不清道不明地覺,總覺得他似乎真欠了,負了一般,甚至連帶著也忌諱起“夢”里那人心痛的結局來……
他再次以額抵著的額試了試的溫度,心里暗暗做了個決定,等考完科舉后,得把當初放下的那些醫書再重新撿起來。
“不行,”他將從梳妝臺前抱起來,重又送到床邊上,一邊道:“我李媽媽去熬些姜湯,你去上床捂著……”
“什麼?!”珊娘大驚,忙揪著他的襟掙扎道:“別胡鬧了,不是說今兒搬家嗎?這可是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機會,不趁著這時候趕搬出去,萬一中間出點什麼差錯,我倆不都白忙活了?!”
Advertisement
“你正病著……”
“一點發熱而已,且我自己都沒覺!”珊娘掙扎著從他懷里跳下來,“大不了我穿得厚實一些,路上再多加個炭盆,難道還能凍著我。”又道:“總之,我在這里是一天也不想多呆的!”
袁長卿看看,忽地彎一笑,著的臉道:“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我?我是那種沒算計的人嗎?我說你可以去床上捂著,你就盡可以去捂著。”又道:“搬家自然是要搬家,且還要正大明的搬。”頓了頓,又笑道:“只是我沒料到你竟會病了。這倒正好了。”說著,湊到珊娘耳旁,將他已經做下的安排,以及要怎麼做,全都小聲說了一遍。
珊娘一側頭,瞇著那雙眼兒把袁長卿一陣上下打量,撇著道:“我剛才就想說了,虧你被人作‘高嶺之花’,多清冷高潔的一個人模樣!偏了那層皮,背后盡冒壞水兒!”
Advertisement
袁長卿一抬眉,“不喜歡我這主意?”這主意確實不怎麼正大明。
“嗯,我得說……”珊娘先是拉長了音調,忽地又掂起腳尖,在他的上飛快吻了一下,笑道:“我死你這一肚子壞水兒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94 章

神偷王妃
二十四世紀天才神偷——花顏,貪財好賭,喜美色,自戀毒舌,擅演戲,一著不慎,身穿異世,莫名其妙成為娃娃娘,還不知道孩子爹是誰……“睡了本殿下,今后你就是本殿下的人了。”“摸了本世子,你還想跑?”“親了本君,你敢不負責?”“顏兒乖,把兒子領回來…
125.5萬字8 377563 -
完結775 章

覆手繁華
她是個瞎子,在黑暗中生活了二十年。最終被冠上通奸罪名害死。當她重新睜開眼睛,看到了這個多彩的世界。——翻手蒼涼,覆手繁華。一切不過都在她一念之間。PS:他知道那個殺伐果斷的女子,一搶,二鬧,三不要臉,才能將她娶回家。還不夠?那他隻能當一回腹黑的白蓮花,引她來上當,要不怎麼好意思叫寵妻。虐極品,治家,平天下,少一樣怎麼爽起來。
148萬字8 15908 -
完結637 章

醫妃傾城王爺又失寵了
二十一世紀的醫學博士,穿越成了容顏盡毀、一無是處的寒王府棄妃。庶母登門叫罵,綠茶姐姐矯揉造作,渣男冷眼旁觀。開什麼玩笑?她斗極品、虐白蓮,拳打綠茶,腳踩渣男,打得那些宵小跪地叫姑奶奶。廢材逆襲,一路開掛。直到某位冷酷王爺欺身而上:“女人,你有點意思!”某女冷笑:“王爺,咱們彼此彼此!”
111.9萬字8 23451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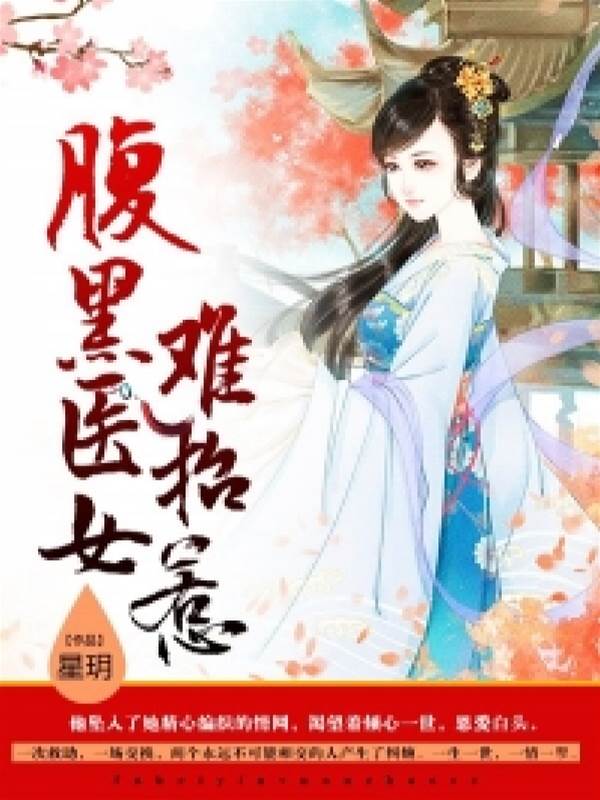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1667 -
完結262 章

侯府主母
翁璟嫵十六歲時,父親救回了失憶的謝玦。 謝玦樣貌俊美,氣度不凡,她第一眼時便傾了心。 父親疼她,不忍她嫁給不喜之人,便以恩要挾謝玦娶她。 可畢竟是強求來的婚事,所以夫妻關係始終冷淡。 而且成婚沒過多久永寧侯府來了人,說她的丈夫是失蹤許久的永寧侯。 情勢一朝轉變,怕他報復父親,她提出和離,但他卻是不願。 隨他上京後,侯府與京中貴眷皆說她是邊境小城出身,粗俗不知禮,不配做侯府主母,因此讓她積鬱。 後來謝玦接回了一對母子,流言頓時四起,她要謝玦給她一個說法。 可恰逢他要帶兵剿匪,他說回來後來後再給她一個交代。 可沒等到他回來給她交代,卻先傳回了他戰死的消息。 她心有疙瘩的守寡了多年後,卻莫名重生回到了隨他初入侯府的那一年。 * 謝玦近來發現妻子有些怪異。 在他面前不再小心翼翼。且吃穿用度也不再節儉,一切都要用好的貴的。打扮更是不再素雅,而越發的嬌豔。 就是對他也越來越敷衍了。 這種奇怪的跡象不得不讓謝玦警惕了起來。 他的妻子,莫不是移情別戀了……?
41萬字8.09 507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