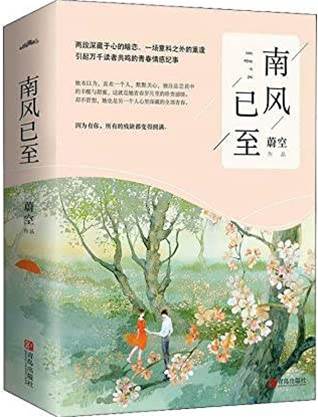《親昵》 第36章
秦崢罵了句, 眉擰,躬彎腰,咬牙,一把將打橫抱起來,語氣低得發冷:“生著病還瞎他媽跑。”
說著, 轉頭大步往哨亭外走。
天黑得像浸了層墨,之前豆大的雨珠已經變雨, 風一吹,斜斜飛到人臉上, 涼涼冰冰。
秦崢臉上云布, 走到亭檐下, 稍頓,看了眼天, 又垂眸看向懷里的人:雪白的雙頰上浮著病態紅暈, 大眼通紅迷離,淚汪汪的, 小手抓住他大手,哭不說話, 嚶嚶嗚嗚, 活像只被主人拋棄的小花貓。
弱弱的子, 本就發燒, 哪兒還能淋雨。
秦崢薄抿一條線,須臾,朝邊兒上的哨兵扔去幾個字, 寒聲:“有傘麼?”
魏濤的小戰士連忙立正敬禮,站得筆直:“報告秦營長!有!”
“拿一把過來。”
“是!”
魏濤朗聲地應,回從哨亭的門背后翻出一把傘,撐開,舉高,然后跑到秦崢旁邊兒站定,“首長,傘來了。”
秦崢大步往外走,“跟上。”
部隊和各軍區軍分區一樣,駐地部通常都配有駐軍醫院。由于條件限制,大部分駐軍醫院的醫療水平和醫療設備都無法達到一流,但理一些小病小痛不問題。
秦崢把余兮兮抱進醫院,正好,走廊上過來一個人,穿白護士服,年齡在四十歲左右,前的工作牌上印著幾個正楷小字兒:護士長,張霞。
“秦營長,”張霞打了聲招呼,視線下移,注意到那個小聲泣的人,不由萬分驚詫:“這個孩兒……”
秦崢面極沉:“在發燒,估計是淋雨了寒。”
護士長點了點頭,上前,手去探余兮兮的額頭溫度,隨后皺起眉,“是在發燒,而且燒得還厲害。”說著便轉大步走出去,“今晚是謝醫生在值班,您快跟我來吧。”
Advertisement
科室里,白熾燈通亮。
護士長帶著秦崢往前走,剛到門口便高聲說:“謝醫生,有病人。”
話音落地,老軍醫收起報紙抬起頭,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鏡。
眼前站著個高大冷峻的男人,穿迷彩T,布料被雨水打了,嚴地包裹著一副剛勁軀;他懷里抱了個姑娘,二十出頭的年紀,纖,眉眼楚楚,十纖細的指頭牢牢攥著男人手臂,在小聲嗚咽。
男人擰著眉,低聲斥:“再哭收拾你。”
小姑娘呆了呆,像被嚇住,幾秒后瓣兒一咬,淚花兒流得更洶了。
“……”軍醫蜷手咳嗽了聲,拿出筆和本子,道:“秦營長,把放下來吧,我得登記一下病人的信息,然后還要給做檢查。”
秦崢點了下頭,沒說話,弓腰便準備把懷里的人放椅子上。
不料那小東西竟掙扎起來,扭了扭,兩只白生生的細胳膊勾他脖子,摟得死,里還發出幾聲不滿的咕噥。
護士長:“……”
軍醫:“……”
秦崢有點兒好笑,大掌輕輕拍余兮兮的背,薄近右耳,嗓音低:“干嘛呢。乖,松手,醫生給你檢查。”
搖頭,聲音小小又可憐,“要你抱。”
“……”
他瞇了瞇眼,約意識到不對勁。
這丫頭臉皮薄,換平時,他隨便一句葷話都能得面紅耳赤,本不會當著外人與他太親近。
須臾,秦崢住的下,抬高,目盯著的臉審度。姑娘這會兒倒不哭了,睜著雙大眼看著他,眼神霧蒙蒙,毫不見往日清亮。
他低聲:“知道我誰麼。”
沒猶豫,語氣格外認真地說出他名字:“秦崢呀。”
他接著問:“知道這地方是哪兒麼。”
Advertisement
這次想了想才說:“家里……”說完卻連自己都覺得奇怪,恍恍惚惚的,“你不是回石川峽了麼?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連自己在哪兒都不知道,果然燒糊涂了。
秦崢咬牙,心疼加冒火,大掌懲罰地掐了把那圓翹的。力道不重,但細皮仍覺得疼,嗚了聲,小臉埋進他頸窩,就是不肯松手。
磨磨唧唧耽誤時間,他不耐煩,索抬眸看向軍醫,道:“的事兒我清楚,有什麼就直接問我。”
老軍醫姓謝,六十多歲,白大褂里頭是一棕綠軍裝,頭發花白,笑起來時眼角細紋深深,看上去和藹可親。
謝醫生笑了下,點頭,鋼筆在紙上游走:“什麼?”
“余兮兮。”
醫生筆一頓,“哪個西?東南西北的西?”
秦崢沒什麼語氣:“傻兮兮的兮。”
護士長:“……”
謝醫生:“……”咳了聲又才接著問:“那多大年紀?”
“二十四歲。”
謝醫生記錄著,繼續:“和秦營長你是什麼關系?”
秦崢答得簡潔明了:“夫妻。”
可話剛說完,他懷里的姑娘卻抬起了頭,大眼瞪圓,盯著他,紅撲撲的臉蛋上滿是驚訝同疑:“咦?可是,可是我們不是未婚夫妻嗎?還沒……”
他垂眸看一眼,淡淡打斷:“這會兒怎麼不糊涂了。給我老實待著。”
接著便聽軍醫再問:“到駐地來是探親麼?”
“對。”
“提前跟你說過麼?”
“沒有。”
謝醫生抬頭,鏡片背后的眸子里略過一詫異,旋即笑笑:“姑娘家一個人跑這麼遠來探親,不容易啊。”說著,拿起耳溫槍給余兮兮測了個溫,端詳須臾,道:“三十九度二,算高燒了……什麼時候開始發燒的?”
Advertisement
“……”余兮兮沒搭腔,乖乖巧巧地窩秦崢懷里,懨懨的,垂著眼簾雙眸無神,明顯神不佳。
秦崢低頭,近,耳聲重復了一遍:“乖一點。跟醫生說,什麼時候開始發燒的。”
呆呆的,愣半晌才搖搖腦袋,很困的樣子:“……我不知道。”
軍醫聽后皺眉,收起筆,轉頭吩咐一旁的張霞護士長,說:“病人況不太好,需要輸退燒。去安排床位。”
“好。”護士長轉離去。
秦崢問軍醫:“大概什麼時候能好?”
謝醫生道:“看癥狀應該只是普通的細菌冒。輸見效快,燒應該很快就能退下來,你不用太擔心。”說完起,去里間拿藥去了。
余兮兮此時暈暈乎乎的,神思混沌,完全在狀況之外。眼睛能看見兩人的在,想知道他們說什麼,腦袋卻怎麼也反應不過來,不由眨眨眼,手,指尖兒輕輕去撓橫過小腰的手臂,“秦崢……”
這嗓音又又,微微啞,跟小貓似的。
男人看向,冷眸中的目不自覺就了下來,“怎麼?”
迷迷糊糊,扭頭左右看看,像是張:“是要……要給我打針嗎?”然后不等他答話便撅起,地跟他撒:“人家怕疼,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打針呢?”
秦崢好笑,堅下頷蹭蹭的臉蛋兒,嗤道:“你多大了,嗯?二十幾歲還怕打針,給我丟人。”
余兮兮一雙迷離大眼著他,咬瓣,可憐:“可我就是不想打針呀。”
他逗,語氣淡漠:“你說不打就不打?不行。”
話說完,那人小臉一垮,癟癟,眸子里登時便浮起層晶瑩水汽,瞬間就又要哭了。
“……”真他媽服。
秦崢無語,臂彎下勁兒給往上一摟,狠狠吻的,咬牙:“哭哭哭。小東西,就知道怎麼讓老子心疼。”
余兮兮輸的床位安排在一樓,單間單人房,干凈整潔,部還配有獨立的衛生間。
秦崢弓腰把放床上,可剛要起,那人便又開始鬧騰,小手勾摟他脖子,的,怎麼也不。他沒轍,看出這姑娘無論喝醉還是生病都是個小無賴,只能還是把抱起,放上,耐著子又親又吻,好一陣兒功夫才把哄到床上躺好。
“你不可以走,要守著我呢。”纖細的指尖勾勾他擺,小聲道。
“事兒多。”他里不是好話,卻俯下,溫親吻眉心眼角,“輸了,不許。”
兩人一個撒一個寵溺,親昵得旁若無人,邊兒上的年輕護士一不留神兒就看完全部,忍不住抿笑,一邊掛吊瓶一邊打量病床上的姑娘,由衷嘆:“秦營長,您夫人長得真好看,白皮大眼睛,和您特般配。”
部隊醫院不面向社會招人,護士幾乎都是醫學護理方面能力突出的兵,有軍籍,上過訓練場。和城市里滴滴的孩兒不同,們吃苦耐勞,能扛得住日曬雨淋,白皙的皮也在年復一年中變了小麥,變得糙。
秦崢略勾,極淡地笑了下。
那頭護士長已經給余兮兮的手背消完毒,太白的緣故,淡青的管清晰可見。旋開針頭,對準,迅速扎進去。
手法嫻,疼痛只短短瞬間,余兮兮幾乎沒什麼反應。
藥有安神效用。
不多時,沉沉睡去,淡的小臉陷進的黑發和枕頭里。
秦崢安靜坐在床邊,護士長收拾完東西后回過頭,蹙眉,著嗓子道:“秦營長,你這上又是泥又是雨的,干脆先回宿舍換件兒裳?”
男人的臉和語氣都很淡,“沒事兒。”
年輕護士也接話,“您今天帶隊野外實戰訓練,累一天了,還是回去休息會兒吧。您夫人這兒有我們呢。”
他說:“不用。你們歇著去吧。”
兩人見狀相視一眼,也不好再說什麼,轉過,拿著東西出去了。
腳步聲漸遠,最終徹底消失。
秦崢垂眸,大掌住纖的小手了,嗓音低低沉沉,自嘲似的笑,“敢走麼,醒了要看不見我不得哭死。”嘀咕句,“真是個小祖宗。”
不知是藥原因還是其它,余兮兮這一覺睡得極好,甜甜沉沉,半個夢也沒做。
閉著眼,皺著眉,仍覺得有點暈。約約想起來,自己從基地出來后,神思恍惚頭痛裂,想起前一晚和余衛國的爭執,想起那記打在心上的耳,想起陳梳端莊清貴卻無比令惡心的臉……
然后又忽然想起,秦崢走之前對說,“如果可能,我把命到你手上”。
那一刻,像在孤獨黑夜里看見了一道。
想見他的沖猛然便蓋過了所有,包括病痛,包括理智。
按照之前查找的路線前行,火車倒大,大倒的士,忍病顛簸整天,十點不到出發,將近傍晚才看到石川峽的影兒。可縣城還是太大,沒有地址,到了也只能靠一張問,輾轉打聽,終于在一個好心大爺的指引下趕到駐地。
之后的事,記憶卻都模糊了……
忽的,有人啄吻的,低沉微啞的嗓音從很近的地方傳來,仿佛著白的耳垂:“醒了?頭還疼不疼?”
“……”眼皮沉重,余兮兮掀得吃力,試著了,這才發現自己全都被裹在一副火熱堅的膛里,暖得幾乎滾燙。
微微呆愣。看見頭頂上方是一副棱角分明的下頷,堅,糙,帶著些許的胡茬,剛味兒十足。
幾秒后,下頷的主人低頭,糙修長的手指臉蛋兒,黑眸含笑意,“不認識了?”
“……你……”余兮兮瞪眼,視線往下掃一圈兒,驀的臉通紅:“你、你怎麼不穿服!大清早就耍流氓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432 章

總裁強勢愛:染指,小甜妻!
「看過,睡過,還敢跑?」堵著她在牆角,他低吼。「家有祖訓,女孩子隻能和自己的丈夫同居。」她絞著手,瞎謅。「家訓沒教你,吃完必須得負責?」「……」他是薄情冷性的軍門權少,唯獨對她偏寵無度,染指成癮。蘇晨夏,「我還是學生,娶了我,你就沒點摧殘花骨朵的罪惡感?」他鄙夷,「二十歲的花骨朵?我這是在灌溉!」
127.4萬字8 96880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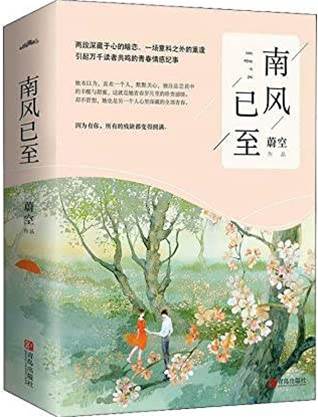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1748 章

錯嫁成婚:總裁的私寵新妻
被閨蜜設計,本以為人生毀了,誰料卻陰差陽錯進錯房間。一夜醒來,發現身邊躺著一個人帥腿長的男人。而且這個男人還要娶她。這就算了,本以為他是個窮光蛋,誰料婚後黑卡金卡無數隨便刷。引得白蓮花羨慕無比,被寵上天的感覺真好。
316.1萬字8.18 94776 -
完結434 章

離婚後冷她三年的陸總膝蓋跪穿了
【誤會賭氣離婚、追妻火葬場、豪門團寵、真千金微馬甲】確診胃癌晚期那天,白月光發來一份孕檢報告單。單向奔赴的三年婚姻,顧星蠻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民政局離婚那天,陸司野不屑冷嘲,“顧星蠻,我等著你回來求我!”兩個月後——有人看見陸司野提著一雙小白鞋緊跟在顧星蠻身後,低聲下氣的哄:“蠻蠻,身體重要,我們換平底鞋吧?”顧星蠻:滾!陸司野:我幫你把鞋換了再滾~吃瓜群眾:陸總,你臉掉了!
43.2萬字8 210740 -
完結138 章

沈總,太太說你不行去排隊離婚了
傳言,沈氏集團繼承人沈晏遲,爲人高冷,不近女色。只有江迎知道,這男人私下是個佔有慾及強的色批!*江迎暗戀沈晏遲多年,最終修得正果。結婚一年裏,沈晏遲從不對外公開。直到他所謂的白月光回國,出雙入對豪門圈子都知道沈晏遲有個愛而不得的白月光,看到新聞,都嗑着瓜子看江迎笑話,說這勾引來的婚姻,註定不會長久。…江迎漸漸清醒,...
27.8萬字8.18 280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