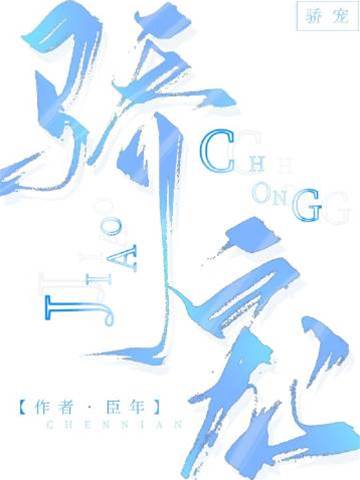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粥與你可親》 第14章 成婚
顧文瀾洗完澡回到臥室, 看見站在書桌前收拾課本和一塌試卷, 看樣子是準備睡覺了,他走過去, 稍微靠著桌沿,說:“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說了。”
手上作未停,輕聲問:“什麼?”
屋子里亮著暖黃的, 襯得的廓溫雅氣,他手地想,事實上也沒忍著, 抬手上去, 皮得手。
倒是他指腹上的薄繭刮得不舒服, 推開臉上的手,又問:“你想說什麼?”
顧文瀾悻悻地放開, “我明天休息, 明晚把兩家長輩約出來吃頓飯, 方便麼?”
溪言點點頭,“知道了,我爸媽那邊很好安排。”
他笑了笑, 想也不想就說:“就跟你一樣?”
溪言微微一愣, 道:“對, 很省心吧?”
他不置可否。
不是省心, 是舒心。
確切地說,是安心。
溪言把試卷豎起來在桌面上對齊了,擱到了桌邊, 收拾完東西準備回床上睡覺,被他一攬腰給帶他懷里,吻像細雨,纏纏綿綿落在上,頰邊,頸窩里……
“你不累麼?”到他襟的料抓著,“今天回來比平時還晚。”
“沒,”他湊在頸窩里,含糊道:“今天早下班,跟朋友在外面喝酒。”
忽然沒吭聲。
顧文瀾頓了頓,抬起臉來說:“放心,沒有花天酒地。”
溪言說:“只怕是有心無力。”
一個當醫生的,沾一滴酒都得深思慮,哪還敢花天酒地這麼放肆。
他笑著近的瓣,喃喃說道:“你倒是把我了。”
溪言:“……”
你個大西瓜的。
他這話很平常,但他作曖昧,腔調也曖昧,跟調似的,聽起來也就顯得別有深意。
Advertisement
經反覆驗并確認,溪言發誓,顧文瀾的絕對是金剛石材質的,咬牙忍了半天才說:“你……要不要……”
他低著回應:“要。”
“休息一下?”補充。
“不要。”很干脆。
“……”
第二天他自己睡得跟居山林似的雷打不,溪言一早醒過來準備早餐,期間進來了他三回他才起來,進洗手間洗漱完出來,看見在臺里晾服。
他走出去,彎腰在放服的籃筐里拿了件東西玩。
溪言轉一見到他,正想讓他進屋吃早餐,忽然發現他手里的,急忙搶回來,說:“你干什麼?”
有點兇……
顧文瀾撇,“我研究一下,每次你的服,一到它那一關就卡住了,我倒要看看它多大本事,居然再三地把我難住了。”
溪言:“……你,消失。”
他只好回屋。
顧文瀾進屋之后,經過茶幾,蹲下來敲了敲魚缸,嚇小金魚玩,嚇完小金魚再走到餐桌邊坐下,開始揪桌上的百合花的花瓣……
溪言晾完服進來,看見他無所事事地坐著,走過去問:“早餐吃了麼?這麼快?”
他靠向椅背,“沒,桌上又沒東西,吃什麼?”
“你……”溪言氣得瞪他,抱著籃筐走了,邊說:“懶死你算了!”
“冤枉我了,”顧文瀾沒事就喜歡逗,看見從洗手間出來又說:“李老師不親自把早餐端上來,我吃了也不開心呢。”
溪言進廚房把粥盛出來給他,自己又進屋收拾東西去了,再出來時到廚房一看,他倒是把碗給洗了,正覺得滿意,出來就看見他蹲在茶幾旁跟小金魚較上勁了,指關節把魚缸敲得鐺鐺響,兩條小金魚被嚇得四竄。
Advertisement
發現顧文瀾真的很稚,稚,稚!
溪言過去把魚缸端起來,進洗手間給小金魚換水。
顧文瀾對著的背后說:“不就敲了幾下麼,看把你給心疼的。”
回:“就要心疼。”
顧文瀾坐在沙發上看了一會兒文獻,做筆記,等給小金魚換了一缸水出來,他把書往沙發一扔,說:“換服,咱們出門。”
溪言扔了幾顆魚食下去,抬起頭問:“要去哪。”
“給你買個梳妝臺。”他一臉闊氣。
“哇,好大的恩賜呢。”說完轉進屋換服。
“別裝可,”他起跟著進屋,倚在柜門邊上說:“大白天的又想把我騙上床?”
“神經病。”海嘯都浪不過他,覺得。
從柜里拿了件白的高領羊衫和牛仔出來,見他賴在這里似乎沒打算走,忽然笑著對他說:“我給你唱首歌怎麼樣?”
他不咸不淡地應著:“嗯——”
著嗓子扭著脖子,唱:“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
顧文瀾:“…………”
溪言調戲完他,笑著走開,去洗手間換服。
顧文瀾啞然失笑。
不僅僅是簡單的舒心,是安心。
像溪水,放什麼容就呈現什麼姿態,他把放到自己邊來,就擺出了讓他最安心的姿態,站在跟前,他就想抱。
或許找個人過日子安心一點,重點不在人,在于安心。
這種安心的來源是什麼尚且不知。
……
顧文瀾帶著繞遠一些,去了居家商城。
溪言看了個大概,選了個和臥室柜的風格相似的,白。
顧文瀾似乎不太滿意,覺得規格小了,他指了指旁邊那個,同系列三面鏡的梳妝臺,看起來確實比挑的這個高了幾個檔次。
Advertisement
導購員上來先贊了一下兩位真是獨慧眼,然后說:“這款北歐實木梳妝臺是我們店里最歡迎的一款,目前存貨不多了。”
顧文瀾看過去,問:“最歡迎?”
導購員趕點頭說:“是的是的。”
顧文瀾點點頭,淡淡道:“那獨慧眼這個特質還是大眾化的。”
溪言:“……”
導購員的微笑跟上了502似的僵住了,看向旁邊的顧客求助。
溪言笑著說:“就要這個。”
導購員聽了,樂呵呵地開票據去了。
溪言說了他一句:“無不無聊?”
他著鼻梁,笑笑沒說話。
接著溪言還挑了一面全鏡,和梳妝臺一起讓人送貨上門。
結賬的時候,他出錢包掏了一大疊紅大鈔……
溪言小聲問:“你帶那麼多現金在上不嫌麻煩麼?”
他湊到耳邊低聲反問:“你不覺得男人掏錢包為人砸現金的時候特別帥氣麼?”
溪言:“……”
這是什麼一擲千金的土豪想法?
回到家安置完所有東西,差不多下午一點鐘,顧文瀾這才帶出門吃飯,就在離家半個小時車程的廣場里找了家茶餐廳。
顧文瀾今天沒有戴領帶,領口的紐扣敞著,模樣隨許多,平時他去醫院一定會系領帶,西裝革履,營造出一不茍又風度翩翩的形象,到欺世盜名……
誰能想到他在家里能稚到那個程度,浪那副德?
兩人吃完飯出來,溪言看見廣場外面的噴泉邊上有一伙兒人圍著不知道在干什麼,好奇之下多看了兩眼,忽然就發現了個悉的影。
周禹?
停下來,發現那伙人圍著他,似乎在互相對峙著,有兩個手里還拎著子,兇神惡煞的樣子,溪言怎麼看怎麼覺不對勁,趕跑了過去。
顧文瀾聽見高跟鞋噠噠噠的聲音,一回頭發現自己老婆一聲不響跑了……
帶頭的那個滿臉戾氣,“周禹我告訴你,我們這兒不是慈善機構,欠債就得還錢,這就是社會公道!今天還不上卸胳膊卸!隨你挑!”
周禹倒是無于衷,說話比討債的人還拽,就一句話:“今天沒有。”
帶頭的擼著袖管就要過來,“我他媽給你臉了是不是?”
溪言及時趕到,把周禹攔在自己后,“你們干什麼?”
一出來,把周禹嚇了一跳,他直接皺起眉,把拽到旁邊,“你來干什麼?”
帶頭的忽然擺出個下流臉,說出來的話也不上檔次,“哎喲,可以啊,你小子欠著債,不花心思還錢,居然玩人?”
溪言沒見過這種陣仗,盡量保持著鎮定,轉過去說:“我是他老師,你們干什麼的?”
“干什麼的?討債的!”那人冷笑,“你能替他還錢麼?還不上趕滾,在這兒耽誤功夫!”
“欠多?”溪言直接問。
那人和旁邊的人對視一眼,看笑話似的看著,說:“8萬!”
溪言:“……”
周禹臉沉。
其實溪言聽到這個數目時還是稍微松了一口氣的,就怕聽到對方說個幾十幾百萬的……
那人笑完了繼續說:“一個月還3000,媽的跟牙膏似的夠仁慈了,就這他媽還能拖一星期,今兒我們是來卸他胳膊的!”
旁邊人補充:“或者卸!”
溪言趕道:“我替他還。”
周禹把拉開,已經烏云照面,“你發什麼瘋?”
那人刺耳的笑聲又傳過來,“對了,我們只收現金!”
“溪言?”
周禹循著聲音過去,不遠的男人步履從容,不不慢的樣子,正往這邊過來。
溪言幾步迎了上去,對他說:“你還有現金麼?”
忽然覺得顧文瀾上帶現金真是個好習慣。
顧文瀾往那邊了一眼,差不多能明白怎麼回事,手出錢包,把所有現金拿出來給,“就這麼多了,應該有2000,夠不夠?”
溪言把自己上的現金也拿出來,一共也才2500……
還是得跑一趟銀行。
顧文瀾開車去了一趟銀行取現金,來回半個小時,最后把3000塊錢給對方,對方當面數了數,這才吆喝一聲,離開了。
溪言松一口氣,轉看周禹的時候,他已經轉走出一小段距離了……
剛要追上去,被顧文瀾一把拉住,“別過去。”
“為什麼?”不放心地回頭了好幾眼。
“這小子自尊心強,你追上去他一下子擰不過彎來,可能還會給你臉看。”顧文瀾淡道。
溪言看著周禹的影消失在拐角,一下子思緒萬分。
顧文瀾問:“他就是你上次跟我說的,青春期叛逆年?那看來不是一般的叛逆年,一般叛逆的年欠個800不能再多了。”
溪言:“……”
也覺得,8萬,是不是這臭小子有什麼?
顧文瀾見沉默,又問了句:“回家麼?”
溪言回過神來,說:“那個錢,我會還給你的。”
顧文瀾似笑非笑,“這麼見外?你跟他親,還是跟我親?”
溪言看著他,憋了半天才說:“他是我的學生,我負責,你不需要摻和。”
“是麼?”顧文瀾估計又被氣到了,了煙出來,沒點火,他咬著煙說:“家里的梳妝臺和全鏡還是你用呢,不也用我的錢買?”
“這不一樣。”說。
他把里的煙拿下來,冷著臉挑眉,“你倒是公私分明。”
溪言:“……”
顧文瀾接著面無表地扔了一句:“李溪言,別三天兩頭惹我生氣。”說完往泊車位去了。
溪言心想,你怎麼那麼容易生氣?
==
作者有話要說: 顧醫生這……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清的,明天會把顧醫生家里的事代一下
猜你喜歡
-
連載1741 章

先婚後愛,大佬要離婚!
許星辰和邵懷明結婚的時候,所有人都說她瞎了眼,好好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找個建築工,除了那張臉,一窮二白。後來,邵懷明搖身一變,成了商界大佬,所有人都說許星辰眼光好,嫁得好。許星辰:可我想離婚。邵大佬:..
357.1萬字8.33 16013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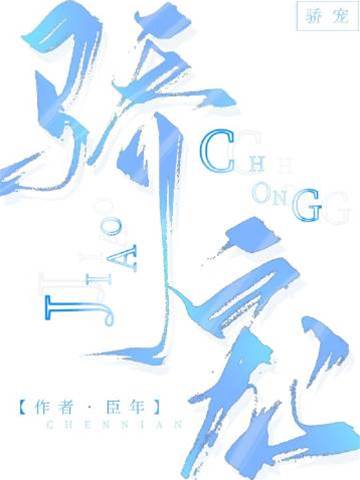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450 章

重生后大佬媽咪馬甲掉了
睜開眼,沈知意重生回到兩年前。這一年她的雙胞胎兒女還沒有被惡毒妹妹一把火燒死,她也沒有成為人們口中蛇蝎心腸的毒婦,丈夫晏沉風更沒有為了救她而丟掉性命。沈知意發誓,這輩子她一定要做一個人間清醒的好妻子,好媽媽,把前世虧欠晏沉風和孩子們的全部彌補回來!“阿意,不許逃。”晏沉風目光陰鷙,牢牢扣住沈知意的手腕。沈知意一把抱住晏沉風,在他唇上輕啄:“放心,我不逃。”后來,事情開始漸漸變得不對勁。小叔子發現他的偶像“黑客S”是沈知意,大姑子發現她欣賞多年的金牌編劇是沈知意,就連婆婆最崇拜的神醫團隊里都寫著...
92.1萬字8 65203 -
完結102 章

獨寵梨梨
【商界大佬X乖乖女】【甜寵 年齡差 嘴硬心軟 輕鬆愉悅 結局HE】丁梨十七歲時寄住進裴家。高高在上的男人一襲深色西裝靠坐於黑色皮質沙發上,瞳孔顏色偏淺,冷漠嗤笑:“我不照顧小朋友。”-後來。嚴肅沉悶的裴京肆,火氣衝天的走進燈紅酒綠的酒吧街裏,身後還跟著個乖軟白淨的小姑娘。他壓著火氣,訓斥說:“你還小,不許早戀,不許來酒吧!”丁梨眨眨眼,無辜看向他:“可是裴叔叔,我成年了。”裴京肆:“……”-再後來。裴京肆和程家大小姐聯姻的消息傳出,丁梨當晚收拾行李搬出裴家。向來運籌帷幄的裴京肆第一次慌了,紅著眼睛抱住那個他口中的小朋友,卑微討好說:“梨梨,我隻要你,一起回家好不好?”注:男女主無收養關係,無血緣關係,且女主成年前無親密行為,寄住梗。
14.3萬字8.18 38332 -
完結654 章

新婚夜,殘疾大佬站起來了
被人陷害後,她代替妹妹嫁給輪椅上的他。都說傅家三爺是個殘廢,嫁過去就等於守活寡。誰知她嫁過去不到三個月,竟當眾孕吐不止。眾人:唐家這個大小姐不學無術,生性放蕩,這孩子一定是她背著三爺偷生的野種!就在她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時候,傅景梟突然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怒斥四方,“本人身體健康,以後誰再敢說我老婆一個不字,我就讓人割了他的舌頭!”感動於他的鼎力相助,她主動提出離婚,“謝謝你幫我,但孩子不是你的,我把傅太太的位置還給你。”他卻笑著將她摟進懷中,滿心滿眼都是寵溺,“老婆,你在說什麽傻話,我就是你孩子的親爸爸啊。”
98.3萬字8.18 487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