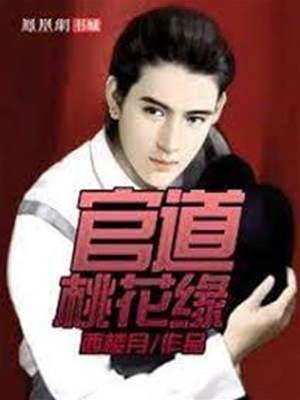《為民無悔》 第兩千一百五十五章 張鵬飛被抓
服照樣埋汰,頭發仍舊蓬,但在警方幫助下,臉頰上汙漬已經洗掉,出本來麵目,邋遢男人正是張鵬飛。
曾經的張大公子,曾經的張大老板,曾經的功人士,今日卻這等模樣,想來也真是讓人歎,正應了那個字——作。
坐在特製椅子上,張鵬飛雙眼閉,腦中卻一刻也沒閑著。別看他表麵故作鎮靜,其實心怕的要命,關鍵這不是小事呀,鬧不好要掉腦袋的。正因為害怕,正因為擔心麵臨滅頂之災,張鵬飛才豁出命來耍著頭陣,從進到這裏就不發一言,已經過去四個多小時了。
“張鵬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也是我們一貫的政策,希你不要執迷不悟,更不要心存僥幸。”對麵高強說了話。
來這一套,什麽都沒有老子命重要。心裏這樣想著,張鵬飛本就沒有要接茬的意思。怪隻怪自己鬼迷心竅,放著班車不坐,怕什麽暴目標,偏偏選了個破農用車,直接來了個自投羅網。想到這裏,張鵬飛不由得搖搖頭,心中暗歎了一聲。
高強聲音再次傳來:“張鵬飛,你是不是後悔坐了農用車,認為應該坐班車呀?告訴你吧,那幾輛車上都有我們的人,坐哪那個你也跑不了。當然了,就是你不坐車的話,我們也隨時能逮你,你的一舉一都在警方監控中。”
啊?張鵬飛驚的張大,也睜開了雙眼。
“沒想到嗎?你應該能想到吧?”高強語氣中帶著譏誚,“你在學院路拐向建設街的路口停留了九分鍾,用垃圾桶裏的東西弄髒了臉,弄了頭發,腳上破的鞋也是從那裏邊撿的。剛才這地方是有監控的,你難免不信我們隨時跟著你,那我就再說一。在從城邊舊外貿大院旁經過的時候,你哈著腰,在北側那個渠裏解了大手。在解手的時候發現了那塊破布,你就拿起來圍到脖子上,擋住了和下。還有,你服上的口子是你在……”
Advertisement
無話可說,無話可說。沒錯,人家說的一點兒沒錯,自己的確被警察一直跟著,可他們為什麽會跟著呢?啊,對了,一定是讓人把我賣了。
在講說了許多跟蹤細節後,高強又說:“張鵬飛,還有瞞必要嗎?老實待吧。”
“他娘的小諸葛,竟然出賣老子。”張鵬飛終於說了話,罵了他自認為的叛徒。
“小諸葛?”高強顯得很驚訝,“小諸葛在哪?”
張鵬飛就是一楞:怎麽回事?不是他?
“他在哪?快說。”高強又催促起來。
“沒,不,我,我隨便說的。”張鵬飛支吾起來。
高強冷聲道:“都這時候了,你還撐個什麽勁?說。”
“我,我,我要是說了的話,能不能算戴罪立功?”張鵬飛尋找著希。
“看況。”高強回複的很含糊。
“好吧,臥龍先生,對不住了。”張鵬飛做過自我表白後,又說,“小諸葛就躲在雁雲大街二百零……”
高強接了話:“雁雲大街二百零六號整個大院都沒人,隻在後門門衛房發現了你換下去的服,商貿路三十九號院十五號樓三單元四零一也沒人。”
不明白,真的不明白。警察是怎麽找到這些地方的,小諸葛為什麽又不在屋子裏,難道他發現自己不在了?
“行了,說點重要的,別這麽打太極了,也沒意思。”高強提醒著。
腦中快速運轉著,盤算著。過了一會兒,張鵬飛忽然道:“我沒雇人打黑槍,我沒想著害楚……”
“你都說的什麽?我怎麽不明白?”高強顯得很是疑。停了一下,又說,“咱們也別繞彎子了,說說你是如何稅稅的,又是如何強*婦的,為什麽要打斷合作夥伴高老板的左?還有好多,你自己說吧。”
Advertisement
糊塗,張鵬飛真的糊塗了。滿以為是說殺人害命,怎麽現在又扯上這些事了?這些事固然需要承擔很重的責任,可是比起雇兇殺人的罪名來,那就真不算事了,關鍵要殺的可不是一般人呀。
盡管糊塗不已,但張鵬飛顯然明白避重就輕,於是講說起來:“好吧,我都待,老老實實的待。打斷那個姓高的狗,既有我的責任,也有他的責任。當時他……”
看著監控屏幕上的畫麵,聽著耳機中傳來的張鵬飛待,楚天齊轉頭看向周子凱,衝著對方出了笑容。這個笑容裏更多的是無奈,還有濃濃的不甘。
……
首都的一套宅子裏,一名中年男子正在接打手機。
手機裏是一個人的聲音:“我問你,你讓我給我弟打電話,言說我爸不好,到底有何居心?”
“這什麽話?家裏老頭子不好,當然首先得告訴兒子了,人家畢竟是家裏繼承人,你隻不過是個外人罷了。我這完全是一片好心,你怎麽反倒質問起我來了?真是狗咬呂賓。”中年男子語氣中帶著不滿,也不無譏誚之意。
對方“哼”了一聲:“算了吧。你明知道我弟剛到地方上,又有上邊領導在那,不可能立即趕回來,勢必要讓那小子來,你的目的就是把他調回來。”
“他?誰呀?你是說那個家夥?調他回來有屁用,你以為我的綠帽子沒戴夠呀。”中年男人咬牙道。
“這就太不實誠了,敢做不該當,算什麽好漢?你就是想讓他趕回首都來,結果他沒回來,卻把他的司機兼保鏢派回來了,他才被別人追殺,甚至刀槍。”對方斥道。
中年男人角掛上一抹笑意,但語氣中卻滿是無奈:“我怎麽聽著這麽糊塗?他被人追殺,跟我有屁關係?還不是他壞事做盡,得罪的人太多了,想殺他的人沒有上百,也有大幾十了吧。再一個,他本就對你家老爺子不關心,否則要是趕到首都來,自然就躲開省城的追殺了。”
Advertisement
對方並不買帳:“快算了吧,你已經算出他暫時不會回來,才讓人對他……”
“等等,等等,據聽說那些追殺他的人都是亡命之徒,我可是政府員,跟他們有什麽關係,會幹那樣的事嗎?”中年男子矢口否認。
“不是你還有誰?當然了,就憑你那麽,肯定不會留下把柄的,自會有替罪羊,但我相信這事絕對和你有關,否則你不會那麽鼓我給我弟打電話的。”手機裏人說的很肯定。
“哎,狗咬呂賓,不識好人心呀,好心當做了驢肝肺。聽說你家老爺子不好,我才隨口說了句讓他兒子回來,不曾想到你這,倒給我派上了一堆不是。早知如此,我何必犯賤,多那幹什麽?”中年男人搖頭晃腦的歎著氣,忽的語氣一轉,“不對呀,你可是一直對他不冒的,今兒個怎麽跟他又是一夥了?你倆該不會……姨媽和外甥婿鬼混也太……”
“放什麽狗屁?”對方沉聲打斷,“主要是老爺子過問了,懷疑我打電話有問題,那話說的特重,從來就沒有這麽警告過我。要不是老爺子這麽問的話,我還沒想這麽多呢,後來越想越覺得你有問題。”
“你總是這麽疑神疑鬼的,這都過去好幾天了,才來找後帳。”停了一下,中年男人疑道,“誒,我就奇怪了。他不就是你家的外甥婿嗎?外甥都不是親的,外甥婿更談不上親了。怎麽我聽這意思,你爹簡直把他當了孫子,否則怎麽會對親兒惡語相向?”
“你,你別胡說。”對方否認著,然後又說,“做事得有個尺度,不能玩大了,否則你會吃不了兜著走。”
“真沒法跟你們徐家打道,都是什麽人呢。”中年男人“哼”了一聲,直接摁了掛斷鍵。
握著手機,中年男人疑起來:“怎麽回事呢?”
“咚”的一聲響過,屋門應聲而開,一個老者走進屋子,氣呼呼的說:“我問你,張天凱兒子意圖槍殺楚天齊的事,到底是不是你指使?”
中年男人一下子站了起來:“爸,你怎麽這麽說,誰說的?”
老者雙眼盯住對方,追問著:“到底跟你有沒有關係?張天凱兒子可是跟你走的很近的,真應了那句話,臭味相投。”
“跟,跟我有什麽關係?你怎麽這麽看自己兒子?”中年男人矢口否認,“誒,不對呀,不是說張鵬飛被抓是因為稅、流氓,還打擊合作夥伴、同行嗎?”
“你信嗎?”反問過後,老者警告著,“我告訴你,如果你要是摻和了,我也救不了你,也本不會救你,明家絕不做這樣的事。”
“沒有,沒有,絕對沒摻和。”中年男人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
“沒有最好,否則你就等著坐大牢吧。”老者說過以後,盯了對方一會兒,氣咻咻的出了屋子。
看著老者離去的影,中年男子眉頭皺了起來,眼珠不停的轉著,心中忐忑不已:怎麽會這樣呢?老頭子為何有此一問?
猜你喜歡
-
完結164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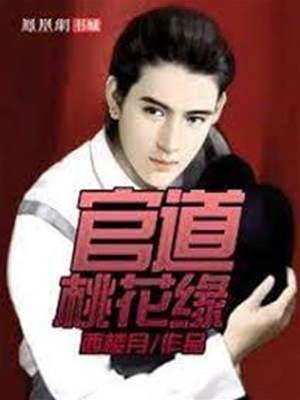
官道桃花緣
大學生顧秋畢業被分配到貧困縣城,意外拯救了美女主任從而獲得好感,仕途愛情兩不誤,辦公室裏曖昧傳送,風騷的仕途令他無法自拔……
368萬字8 97451 -
完結1165 章

神瞳狂醫
意外獲得神醫傳承,走向人生巔峰
210.2萬字8 49797 -
完結749 章

隨身一個桃花源
吊兒郎當的小農民馬小樂,放羊時偶得一殘破瓷片,意外偶遇獲得神秘空間桃花源,自此開啟了他逆襲翻盤之路,鄉村歡樂多,直播帶貨農家樂,養羊養雞種水果,抓蝦捉鼈掏鳥窩,從一個鄉村放羊娃玩到了各界傳說。 啥商界巨賈,古玩大鱷,咱就是個玩兒......
128.6萬字8 22445 -
完結1875 章
飛針神醫
老頭子發神經病,要我在熱鬧的地方練功。 好嘛,整天對著杯子練習隔空攝物,不被當成神經病才怪! 神經病就神經病吧,又不是找不到女朋友,我照樣有春天……
483.5萬字8 515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