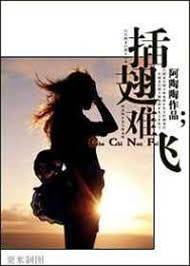《我又不是你的誰》 096 人在塵中不是塵
我顧不得心裡這會噁心自己,手就要去奪,陳浩東用力把我的手機往外丟,那種暴怒的力量令我一個激靈,咔咔拉拉的聲音,我猛地爬起來,手機竟然斷了四塊,陳浩東剛剛的力道有多重可想而知。
回神時,陳浩東已經站起來,他輕輕拍打服上的灰塵,語氣頗淡地說:“扶三歲,你不仁我不義,你說得對,就我和你的關係這輩子都怕是好不了了,乾脆就更壞!”
他向我走來,我悄然往後退,錄音是我的第一手準備,現在錄音被毀了,我自然還有第二手準備,要是陳浩東真弄走了我,姚叔一定會報警,從我的失蹤案手,我不信他做的事還能真的天無。
約他見面的那一刻開始,我把這些前前後後都想清楚了。
“陳浩東,你想幹嘛?”我的雙腳依然跟隨著他往前的腳步一直退。
“把你栓我邊。”他死死盯著我,很沉然地說。
聽見這句話我心裡一陣發酸,我自覺已經太久沒給過他一張好臉,說出口的話也是哪次都不留。要是沈寰九被以嫌疑人的份被帶走,或許我還會欺騙自己說,陳浩東不是喜歡我,只是要膈應沈寰九,可很顯然到了這一步,我沒辦法再安自己讓心裡頭好些。
而我只要一天著沈寰九,就註定要把這個男孩子傷得模糊。就像現在一樣,我會跟他走,完全是因爲挖好一個大坑等著他去跳。
思索間,陳浩東一把住我的手,拖著我往外走。爲了避免他懷疑,我還特地掙扎著,裡罵著讓他放開我。
陳浩東並不理會,後來乾淨彎下子把我扛在他肩膀上,順便警告了句:“扶三歲,你嫁給沈寰九可是人盡皆知,我要是你這會就把臉好好遮著,老子這麼扛著你看得人可多了,不想讓你家男人丟臉,最好他媽的給我老實點!靠!”
Advertisement
我正好也喊累了,他這一警告倒是來得正好,我老實閉。他穿了小路,一直把我扛到他家,那兒離沈寰九的別墅步行也就十幾分鐘的路。
陳浩東扛著我,用腳踢門。
“誰啊?”門裡有人態度並不好的問著。
陳浩東狠狠拍了下我的屁,我別,然後悶沉地回道:“我。”
門很快就被麻溜地打開了。
一陣滔天的煙霧薰過來。
“大哥,你剛去哪了?胖頭說你準下樓買菸了,怎麼扛回來一姑娘?嘿,真稀奇了。不對啊,臉怎麼了?怎麼掛彩了?誰敢打你,這會我們哥幾個正好都在,直接卸了他去。”
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因爲陳浩東扛著我,所以我整個人都倒掛著。
“廢話真多。”陳浩東進了門,他的小兄弟很快把門給關上。
我垂著兩條胳膊看見客廳裡七八糟,七八個人圍在一張桌子上,個個手裡都拿著牌。
我擡眼看的是時候,他們都盯著我,其中有個機靈的小年輕趁這會往出過的牌堆裡換了張牌,自顧自笑起來說:“這局還沒結束呢,東哥的事管。這是咱嫂子看不出來呢你們!”
就這樣,這些人最終消失在我眼底,我被陳浩東丟進臥室,他腳一勾輕而易舉就把門關上。
雖說外頭有人,可真正和他到了房間,說一點都不怕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害怕沒有用,更何況我找他見面的時候就想過,他要是真敢我一下,我寧可咬斷自己的舌頭,所以後來心也就漸漸平復下來了。
陳浩東站在落地鏡前面,輕輕彎著腰,手擡起上了我用石頭砸他的額角。
“扶三歲,你到底要在我上落多傷口才夠?上次你捅我肚子那一刀結了疤,現在又砸我臉上。呵,雖說我不是靠臉吃飯,不過老子對自己這張臉還他媽喜歡的。”陳浩東一邊說,一邊扯著落地鏡旁邊桌上的紙巾,大喇喇地著。
Advertisement
我後背著牆,兩隻颳著牆皮,指甲裡約有末嵌著。我仔細瞧著房間,眼神盯在一副畫上差點把眼珠子給瞪出來。竟然是我的臉,可子卻不是我的,穿著很暴的服,哦,不對,哪裡還有服,幾乎等於沒有,很大的和屁,皮的也是黝黑的,偏偏上面卻卡著我的腦袋,還是結婚證上的那廓,我簡直和被雷劈到沒什麼倆樣。
對著鏡子整額頭的陳浩東大概是從鏡子裡瞧見我眼神了,一下就出現在那副面前面,手一撕就給撕下來,著一團隨便找了個地方塞。
這下我覺得就更雷人了。
他轉臉看我的時候臉真是紅了個通,輕咳一聲道:“你剛看錯了。”
我沒搭話,死死盯著他,雖說看不見自己的表,可我還是能覺得這會看他的眼神有多兇。
“扶三歲,你結婚了,現在老子了第三者。”陳浩東的眼神移開,咬了下脣輕聲說:“這會還把你弄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幹什麼。是,沒人有義務給傷心的出局者發獎牌。但又能怎麼辦?”
我眼睛一睜,從沒想過有一天陳浩東會慢條斯理,條理清晰地說出這番明事理的話來。
打你幾個掌讓你明白痛,然後看懂別人的真心。但又有什麼用?一切都回不來頭了。
我沉了沉呼吸,直截了當地說:“既然不知道把我弄來幹嘛,你還扛一路,嫌自己年輕力太好還是怎麼著?”
陳浩東靠在牆上點了菸,沒有說話。
很久之後,陳浩東才慢了一個世紀地說:“我總覺得你還是我老婆。這家裡天一羣老爺們進進出出的,就是缺個人。”
Advertisement
聽見這句話,我嚨裡更是有句不形的話卡著,上下不能。當年他能把向小帶回家裡來睡覺,離婚後他了單漢,睡誰都不需要和別人代,我不信他有多幹淨。可心裡的這些想法我都沒有說出口,一來是我們離婚了,我沒必要也不想了解他的生活。二來,往事一旦提起,基本就會和開了閘門的水庫一樣止都止不了。
所以我屁都沒放一個,下意識看了眼牆上那隻灰的大鐘。
陳浩東恰時說道:“沈寰九這次沒那麼快出來,你別指他會和神仙似的來找你。”
我也明白這事牽扯太大,不會和一般打架的案子一樣容易,警察大早上來帶人,肯定是因爲存在疑點。就算是問話,估計也得待上一天。
好死不死的是沈寰九還讓時赴明天手宰了陳浩東,也不知道時赴會不會因爲現在的局面變化而等上一等。但時赴這時候要是再搞出命案來,說不準警察會對最近幾起事件產生新的懷疑,覺得和沈寰九沒關係,沒準就把人給放了呢?
心的種種矛盾讓我痛苦不堪。
我不希沈寰九犯罪,都說法網恢恢,我不信真有沈寰九說的那麼輕鬆。可我明白陳浩東一天不死,我和沈寰九就別想過還日子,陳浩東是那樣執拗又一筋的人啊,他什麼苦都吃過,到了現在應該已經百毒不侵無所畏懼。
我看了眼陳浩東,聲音放了問:“向小,霍培一,你幹掉他們找的人一定不一般吧。”
陳浩東吸著煙,聽見我這話,一口煙就卡在嚨裡,猛烈地咳嗽起來。
我還想說話,這時候房門卻被敲響。
外頭傳來一個聲音:“東哥,有幾個兄弟有事兒說先走了,牌局撐不起來,要不你給湊倆把。”
“滾,老子在做呢,打屁!”陳浩東不太耐煩地回道。
可我突然說:“我想打牌。”
他看我一眼,眼神裡意味深長。其實陳浩東在裡是個傻子沒錯,但也不是一點智商都沒有,我心裡盤算什麼他八是看出來了,要不也不可能用這種眼神盯我看。
“你想打啊?你會麼你?”他眼桀驁,角一挑,一副市井混混的樣子。
“我會比大小。別的,我好久沒打,都忘了。”我偏過頭。
噠噠的腳步聲傳來,陳浩東走向我,手掌翻過我的臉,沉地說道:“不會就不會,還忘了。老婆,你以前是遭人欺負的主,現在可是撒謊的一把好手,臉都不帶紅。十句話他媽還剩幾句是真的?啊?”
他的語氣特別惡魔,我也弄煩了,瞪著他問:“到底給不給打?”
“給。”陳浩東冰冷地吐出個字,然後又說:“你心裡有事兒裝著,想瞧瞧想探探。行,我讓你瞧瞧讓你探探。”
說罷,他抓我的手,大步往房門那走,手一扭,我很快看見客廳裡剩下的一窩子人。
煙氣熏天,吃過的可樂罐子和煙盒子,還有一次餐盒丟得滿地都是,真白瞎了這套三室一廳還算得上寬敞的套間。
“我說吧,真是嫂子,和海報一模一樣的。”說話的是胖子,我見過好幾回了。
胖子的手一指,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真想掐死陳浩東。
有幾個小年輕開始盯著我的看,繃不住笑得說:“嫂子別怒,我這就把這些都撕下來。”
我一眼橫向陳浩東,他雙手揣在兜裡,滿不在乎地輕輕晃著,可他的耳子已經紅得像臘腸。
他不不慢地說了句:“收拾一下,要打牌。”
猜你喜歡
-
完結71 章

就想把你寵在心尖上
許真真是南城公子哥沈嘉許寵在心尖上的小女友,身嬌體軟,長得跟小仙女似的。 許真真跟沈嘉許分手的時候, 他不屑一顧,漫不經心的吸了一口煙,略帶嘲諷的口吻說, 你被我悉心照料了這麼久,回不去了,要不了一個月,你就會自己回來,主動抱著我的大腿,乖乖認錯。 直到多日后,沈嘉許在校園論壇上,發現許真真把他綠了一次又有一次。 晚會結束后,沈嘉許把許真真按到了黑漆漆的角落里,鎖上門,解開扣子,手臂橫在墻上,把小女人禁錮在了自己的臂彎里,他的眼眸波光流轉,似笑非笑。 許真真的肩膀抖了抖,咽了咽口水,睫毛輕顫。 “當初不是說好,我們和平分手嗎?” 沈嘉許淡笑,手指劃過許真真柔軟馨香的臉蛋,陰測測威脅。 “要分手可以,除非我死。” PS:虐妻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19.5萬字8 18429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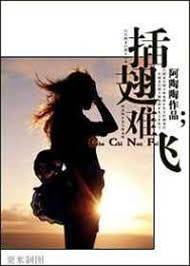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6913 -
完結1542 章

離婚吧,我要回家繼承億萬家產
結婚三年,沈初覺得,薄暮年再冷的心,也該讓她捂熱了。可當他逼著她在薄家祠堂跪下的時候,沈初知道,薄暮年沒有心。沒心的人,她還留著干什麼呢?所以,當薄暮年讓她在跪下和離婚之間二選一的時候,沈初毫不猶豫地選了離婚。她大好時光,憑什麼浪費在薄暮年這個狗男人身上,她回家繼承她那億萬家產每天風光快活不好嗎?
141.8萬字8.31 901684 -
完結1667 章

和腹黑三叔閃婚後真香了
林清榆被準婆婆設計,嫁給未婚夫病弱坐輪椅的三叔。 原以為婚後一定過得水深火熱,誰知道對方又送房子又送地皮,還把她寵上天。 唯一不好的是,這老公動不動就咳得一副要歸西的模樣。 直到某天,林清榆發現了這位覬覦自己已久病弱老公的秘密。 林清榆冷笑:“不是命不久矣?” 陸勳謙虛:“都是夫人養得好。” 林清榆咬牙:“腿不是瘸的嗎?” 陸勳冒冷汗:“為了咱孩子不被嘲笑,我請名醫醫治好了。” 林清榆氣炸:“陸勳,你到底還有哪句是真話!” 噗通一聲,陸勳熟練跪在鍵盤上:“老婆,別氣,打我就是了。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別傷了胎氣。” 曾經被陸三爺虐到懷疑人生的人:您要是被綁架了,就眨眨眼!
196.5萬字8.18 498144 -
完結1385 章
萌寶助攻:霸道爹地寵又撩
繼妹伙同閨蜜設計,她被一個神秘男人把清白奪走。五年后,她攜子回國,一個高貴絕倫的男人出現,揚言要報恩。“嫁給我,我替你養兒子。”她有錢有顏有兒子,表示不想嫁人。
253.1萬字8 432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