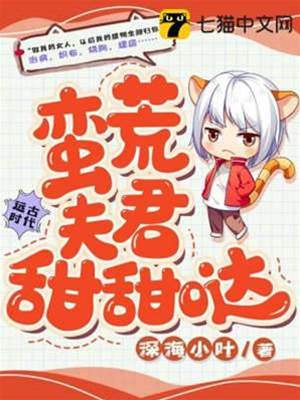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第63章 紅袈裟
場下嗡聲一片, 場上陳長老面凝重之,四個參賽者皆面面相覷,不明所以。
某位站出來說:“蘇俠平日起得最晚, 鄙人今日鳴起練劍, 竟見他榻上無人。”
陳長老沉:“你們今日可有誰看到過他?”
其余人皆搖頭,只說沒見過。
真是怪事, 蘇沉鶴的表現無疑是此次比劍大會最為優秀的,在這決戰的節骨眼上, 竟然不知何去了。
聯想到前兩日的風波, 不難會有些不妙猜測——
底下有人了聲:“沒見過?不是你們明凈峰把人故意藏起來了吧?”
“誰不知道蘇俠進前三甲是板上釘釘, 你們害怕劍譜之事敗, 現在終于用上些手段了!”
起哄一個個面上義憤填膺, 好似真為蘇沉鶴抱不平, 其中哪些是真心實意, 哪些是唯恐天下不, 泠瑯冷眼瞧著, 只覺得煩躁。
陳長老終于一錘定音:“一炷香的時間,若蘇俠還不出現, 那本次——”
“本次比劍,三甲就由你明凈峰包圓?”
一道沙啞蒼老男聲不知從何傳來,如被沙礫打磨過一般刺耳,在場所有人同時聽到了這句話。
眾人驚愕, 立即四張,卻不見那發聲者在何。
陳長老卻已有所, 他沉聲喝問:“閣下無需裝神弄鬼, 既然來了, 盡管現便是。”
那聲音于是惻惻地笑, 笑聲詭譎凄厲,如黃泉厲鬼般可怖。在會場四響起,仿若游移不定的孤魂。
明明是盛夏朗朗晴天,卻莫名刮過一圈圈風,人生生起了層皮疙瘩。
如此笑了半晌,它忽然止住,無聲無息,四周頓歸寂靜。
眾人大氣都不敢,而陳長老已經提了劍在手中,他怒目掃視四周,剛要開口說話——
Advertisement
那聲音說:“小兒,你們顧掌門出來。”
這句卻是從高臺之上傳來,仿若近在咫尺。
陳長老猛然抬頭,只見環繞著大象臺的四大石柱之上,赫然立了位著袈裟的老僧!
那老僧眉眼低垂,皮鶴發,形容干瘦,須眉皆是雪白。一袈裟卻鮮艷赤紅,同這干枯軀襯起來,顯得詭異至極。
場下一片桌椅翻倒之聲,經此風波,見識些的早已嚇破了膽,只后悔為何留得如此輕率,那可是層云寺,那可是空明!
層云寺最起初并沒有這般聲名,它甚至是一座有百年歷史,香火極盛的寺廟。當時空明叛出季室山后,前往層云寺,請求廟里當時的主持收留。
空明從前同該主持有,對方卻并無通融,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不說,還堂皇訓誡了一番,指責他心中已無佛。
空明于是大笑,手中佛珠往空中一拋,道:“我便是佛!”
于是那一天,鼎盛了百年香火的層云寺,全寺二百三十六名僧人,皆戮于空明之手。尸首從山門一路倒伏到佛堂,鮮流淌蔓延,煞氣沖天,數月不絕。
此自此被空明所盤踞,他甚至未曾更改寺名,就著原來層云寺三個字設壇,廣收門徒,傳授功法。
這些年,雖然他任由手下弟子為非作歹,自己卻極來江湖上面,是以雖然層云寺臭名昭著,但真正識得主持空明的人卻在數。
臺上幾名參賽者離石柱之上的空明最近,他們最先反應過來,已經縱躍出,不與這邪僧相接。
而那些想開眼界的看客,如今可算開足了眼界,他們心中只余驚懼,一時間作一團,爭相著想要離開——
只聽一聲利喝:“明凈峰眾弟子聽令!”
Advertisement
陳長老劍指石柱,面容沉肅:“此人不請自來,語出不遜,辱我宗門,我將他拿下,各位護住其余人等!”
場四周的明凈峰弟子紛紛拔出長劍,之前□□上的強壯僧人亦起,各自將佛珠在手中,臂上隆起塊。
局勢一即發。
有人在逃命,有人在對峙,有人正找地方躲著縱觀一切。泠瑯慶幸自己今早反復告誡幾位不通拳腳的婢留守在屋中,不要出來走,不然此此景,未免能將綠袖們一一護住。
一把抓住江琮的袖子,扯著他離開座位,后退到一方雕了仙鶴松柏的石屏風之后。這個位置注意了許久,既能觀察臺上狀況,又能蔽形。
江琮被扯得一個踉蹌,卻沒說什麼,二人繞到屏風之后,站在一靜觀其變。
高臺上只剩陳長老與空明二人。
一個震怒加,平日里溫和斯文的面孔如今沉似水,長劍凜冽,末端直指高。
一個蒼老詭,面容如干枯樹皮,堆疊了層層褶皺,一雙渾濁暗淡的眼珠子嵌在其中,一不,宛若定。
二人隔了十來尺的距離對峙,有弟子想跳上臺相助,皆被陳長老示意退下。
空明嘶啞地重復了遍:“你們掌門出來。”
陳長老目沉沉:“先問過這柄劍!”
語畢,他足下一點,使出輕功行云蹤,竟順著大石柱一路向上,手中劍鋒寒一閃,直直朝空明揮去!
這無疑是開戰之信號,有弟子高喊了聲:“護住明凈峰!”,淡青同深褐戰在了一,劍風拳風難分彼此。
而石柱之上——
他這招極為迅猛,而石柱并未太多翻轉騰挪的余地,眼看著空明必須接下這一劍——
Advertisement
只見深紅袈裟一甩,一卷,如一張蔓延詭詐的網,那剛勁劍勢瞬間被消弭化解,力道斜而地往別去了。
陳長老低喝一聲,順勢轉手腕將劍收回。氣沉丹田,行云蹤發揮到極,生生在空中借了力,挪移到石柱另一邊,再次換方向攻去。
迎接著他的,仍舊是漫天詭異的紅,那袈裟翻涌席卷,滴水不,將他劍鋒包裹纏繞。
握劍的右手一,劍柄幾乎手而出。
陳長老心中大駭,這袈裟竟不僅防守極為穩固,一旦被纏住,甚至能有奪他武之勢!
他催力,右臂全力將劍回,與此同時足尖在柱上一蹬,往后騰躍,落到與之相對的另一柱頂。
兩招已過。
陳長老氣息未定,心跳如擂。而空明仍是僵死寂,連足下位置都未變過一分。
雖然知曉難以取勝,但敵我之間差距之懸殊,仍陳長老心震不已。
空明方才化招,甚至只甩了兩回袈裟,連武都未現于人前。
下傳來短兵相接之戰聲,他緩緩收了手中劍柄,左足后撤半步,開始下一次蓄力。
石屏風之后,泠瑯的手指還牢牢攥著江琮右臂,一不地盯著石柱上的紅僧人,從那古怪袈裟,到因單掌禮而顯現的枯瘦右手。
江琮低聲問:“不去尋蘇俠?”
泠瑯輕輕搖頭,目仍盯原:“昨天雙雙說要同他坦白,二人定是有了些共識……空明已經手,還是此要些。”
江琮說:“陳長老打不過他。”
泠瑯說:“誰看不出來?只是——”
沉思:“這空明不像是要痛下殺手的模樣,不然陳長老早就不敵敗落,哪兒還能再三出招?”
如所言,石柱之上,陳長老凌空躍起,長劍震出無形氣波,一招“挽長風”如疾風過境,勢不可擋,朝空明直直激而去!
泠瑯頓了頓,認出這一招是雙雙經常用的,或許它是明凈峰宗弟子都會用的劍招?
雙雙走的是靈巧路線,而挽長風在陳長老手中,卻是截然不同的剛勁風格,各有千秋,難說孰優孰劣。
然而,這招依舊被化解。
空明形如鬼魅,不過右臂一抬,一揮,那袈裟宛若有生命的活,涌之間似是呼吸起伏,將這道罡烈劍風細包裹。
陳長老卻早有準備,一招挽長風不,他回一旋,生生踏上空明所立石柱,同時左臂一頂,要把老僧下這方寸之地。
空明渾濁沉的雙眼終于有了波,他形微,左手終于從袖中探出。
那是一只同樣干枯蒼白的手,它繃直為掌,又似一記佛印,朝著陳長老正靠近的軀去。
從泠瑯的角度,這一幕被看得分明,心中一,足下使力,就要朝大象臺奔去——
江琮卻一把扣住了,將拉了回來。
“此人多,不可——已經有人去了。”
簡單的一句,已經道盡利害。泠瑯咬牙抬頭,卻見那抹淡青影如斷翅紙鳶,直直往高臺上墜落。
是陳長老。
在即將地的前一瞬,一道影飛撲而出,將陳長老一把支撐住。
來人青馬尾,是個清秀年,正面焦急,扶陳長老坐定后立即按住經脈,為其度氣療傷。
杜凌絕!
泠瑯睜大了眼,他在此,那顧掌門——
連忙環視四周,哪兒有那位老人的影,難道掌門還未醒?
而陳長老顯然也有相同疑問,他掙杜凌絕的手,死死抓住年襟,一張,卻是一口鮮噴涌而出。
杜凌絕無暇拭面上跡,只快速地說了些什麼,只見陳長老面從震驚轉為喜,幾經變化,竟雙眼一翻暈了過去。
泠瑯卻從杜凌絕方才口型中看出,他說到了“顧凌雙”三個字。
看來,雙雙終于去坦白了一切,而現在正代替杜凌絕守著祖母。
旁邊立刻有幾個弟子圍攏上前將陳長老帶走,杜凌絕了面上沾染的漬,同樣出劍,用和陳長老起初一模一樣的姿勢,劍尖直指高柱之上的空明。
空明卻不似之前一般毫無容,他垂頭看著下首年,忽地咧開,出一個滲人至極的笑容——如果那可稱為笑容的話。
“明澈劍法竟被你們練這個樣子,”他嘶聲道,“暴殄天,不過如此。”
場下還在戰,嘶吼聲吶喊聲混一片,而空明沙啞奇異的語聲,卻一字不落地傳到泠瑯耳中。
他用了力,似乎有意讓在場所有人都聽見。
“缺了半本,終究是無用。霜風劍從前同我說,劍祖將劍譜一分為二,為的是制衡二字。如今看來,的確起到效用。”
“天下萬,合則分,分則合,現在,便又到了合之時——就由老代替霜風劍之勞,來行這‘合’字罷!”
泠瑯訝然,已經覺察到不對。
挽長風,不是宗人人都會的劍招麼?為何在空明口中變作明澈劍法之一?
難道——
只聽砰的一聲,不知從何甩上件事,在大象臺上彈跳滾落,最終停在杜凌絕腳邊。
那是一顆人頭。
一顆的,圓滾滾的人頭,因為沒有發,所以相比別人的更易滾一些。它臉上還有驚異表,微張,似在質問。
泠瑯認出來,那是風波最初,登臺狀告明凈峰殺人的層云寺和尚,似乎寂玄,那日過后,再沒見他現過。
而他顯然已經不再有耀武揚威下戰書的神氣,創口整齊利落,似乎是被人一擊削斷。
泠瑯來不及觀察這顆人頭是何人所扔,敏銳地覺察到,場上的氣變了。
準確地說,是空明起了些變化,他作為從始至終都在把控局勢的人,終于出些預料之外的怒氣。
“是誰?”他在質問,語聲平靜。
一個人跳上了高臺,認下了這份罪過。
年馬尾仍有些,臉上還沾了點,他輕松地笑著,同周遭你死我活的氣氛格格不。
他將劍扛在肩上,吹了聲口哨,滿不在乎道:“這和尚大清早來尋我,我同他糾纏了許久,想參加比劍而不得,只好出此下策。”
“大師——”他笑得有幾分邪氣,“您是出家人,不會怪罪于我罷?”
猜你喜歡
-
連載3527 章

九公主又美又颯
眾臣:世子爺,你怎麼抱著世子妃來上朝?世子咬牙切齒:娘子隻有一個,丟了你賠?她是戰部最美年輕指揮官,前世被渣男背叛,慘死斷情崖底。重活一世,開啟瘋狂稱霸模式。一不小心,還成了世子爺捧在掌心的寶。太監總管:皇上不好了,世子府的人打了您的妃子!皇上躲在龍椅下瑟瑟發抖:無妨,他們家世子妃朕惹不起!
310.1萬字8.46 854005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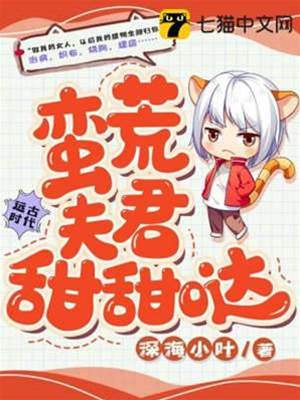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7320 -
完結290 章

吉時已到
于北地建功無數,威名赫赫,一把年紀不愿娶妻的定北侯蕭牧,面對奉旨前來替自己說親的官媒畫師,心道:這廝必是朝廷派來的奸細無疑——
74.6萬字8 7927 -
完結436 章

黑心王爺,跪安吧
眾人勸她:“王爺也就腹黑了點,變態了點,殺人如麻,但他文能安邦,武能定國,貌勝藩安,你嫁給他吧!”眾人勸他:“林姑娘也就野了點,刁鑽了點,坑人無數,但她智計無雙,家財萬貫,貌美如花,娶她不虧!”他:“本王娶狗也不會娶她!”她:“本姑娘嫁狗也不會嫁他!”一年後,兩人:“汪汪汪!”
76.4萬字8 236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