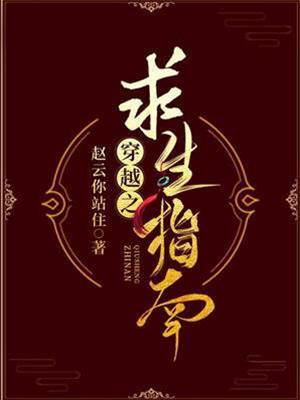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獨占金枝》 第18章 玫瑰花鹵子與舊詩
明白?明白個鬼!姜輝青著一張臉死死的瞪著面前的姜韶,那緩慢挪的軀,只是靠近便讓人有些不上氣了,莫名的力之下姜輝本能的閉了。
如今他腳不便,眼前這姜豬要當真對著自己下來,怕是摔斷的還沒好,手也要一同斷了。
姜輝恨恨的看著面前的姜韶:胖了不起啊!這麼丑瞧還得意的樣子!
姜韶放完狠話后便沒有理會他,而是招呼人把東西搬回去,免得放在西院磕了了。
香梨自是沒忘記那一罐牡丹花鹵子,奔上去就將桌角那罐牡丹花鹵子拿起來小心翼翼的揣回了前的暗袋里。
正揣著東西時,小丫鬟眼角余一掃瞥到趴在地上臉著地的姜輝正頂著鼻青臉腫的臉在看。
“看什麼看?”香梨嘀咕了一聲,狠狠的剮了他一眼。
連小姐的牡丹花鹵子都,真是不要臉!
香梨這護食的舉看的姜輝更疑了:那一罐白瓷瓶一樣的東西他先時還沒注意,只是順手拿了,可看香梨這丫頭的舉,這東西莫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寶貝吧!
姜輝沒有什麼鑒寶的才能,評判值錢不值錢全憑寶貝的主人是誰以及主人的態度,譬如姜韶的東西定是值錢的,再譬如這生了顆痣的刁蠻丫頭如此寶貝的定也不是凡。
沒看到那些珍珠首面看都未看一眼便徑直奔向了這白瓷瓶嗎?
難道是值錢的古?亦或者名家或者名窯出產的瓷?
姜輝挲著下盤算著:這東西應該值錢的很,說不準只這麼一只白瓷瓶就值個百八千兩了,夠他包幾次花船去無數次酒樓了。
Advertisement
如此啊,那得想個辦法把它,不,是弄回來。
姜韶清點完了件,瞥了眼臉著地還在神游天外的姜輝出了西院。
走出西院的那一刻,姜韶忍不住輕舒了一口氣,活了一下胳膊,頗有幾分意猶未盡之。
如此樸素的兄妹宅斗還是頭一回經歷,到底有些不習慣呢!
回到東院,將東西擺置回了原位,姜韶開始琢磨起了靜慈師太那位不日即將來寶陵的老友。求人辦事的態度自是要做足的,更何況這件事事關的家命,更是如此。
是以,姜韶也不吝于花費些力來投其所好,除了牡丹花鹵子之外,東院花圃里那幾簇開花早的玫瑰花也落了的眼中。
鮮花做的鹵子這種東西本質上來說各花均可做,不過姜韶最的還是玫瑰花、茉莉花以及桂花做的鹵子。
茉莉花與桂花花期未到,大部分玫瑰花亦是如此,不過姜韶花圃里還是有幾簇四月便開的玫瑰花品種,不過才欣賞了兩日的早玫瑰,姜韶便上演了“辣手摧花”的戲碼。賞過花了,那麼余下的自然就莫要浪費了。
玫瑰花鹵子的做法同牡丹花鹵子類似,一樣分了花瓣洗凈之后用石臼搗爛,混合了糖與腌漬起來。比起牡丹花鹵子的香味,玫瑰花鹵子的香味更為霸道,也更讓喜歡。
不過眾口難調,靜慈師太與那位靜慈師太的故友喜歡不喜歡還不好說。
姜韶將做好的玫瑰花鹵子封存了起來。
這里的早玫瑰也不過幾簇而已,做鹵子已然有些不夠用了,更別提其他了。姜韶做完玫瑰花鹵子走到花圃邊對著被“辣手摧花”拔的早玫瑰很有幾分慨。
Advertisement
若是多一些曬干玫瑰花干可泡茶,也可如梅、桃一般做餞果干,自有一番不同的味道。
在院子里走了一番,姜韶回到屋中,喚來香梨準備每一日的藥浴。
黑漆漆的湯藥水頗有些刺鼻,香梨鼻子里塞了兩團布將黑的湯藥倒木桶中看姜韶坐了進去。
漆黑的湯藥面上與如玉的形了鮮明的對比。
小丫頭看的呆了一呆,喃喃道:“小姐真真是玉雪一般的人兒。”
雖說有黑湯藥襯的緣故,可到底也是小姐本就白的緣故。
聽姜韶笑了笑,香梨吸了吸鼻子,又道:“那什麼秋水為神玉為骨大抵就是小姐這樣的吧!”
到底跟著喜歡作詩寫文的原主,香梨偶爾也能說出一兩句詩句來。
姜韶笑著搖了搖頭,不以為意,只是被香梨這一提倒是忽地想起了什麼,忙問香梨:“我記得先時我曾做過一些詠民間百姓的詩作,你可還記得?”
自己雖說記不錯,可原主記憶里記不清的東西也做不到無中生有,這一茬雖說有些記憶可那些詩作的去卻有些記不清了。
香梨聽罷忙道:“都在匣子里放著呢!小姐先前說那些詩作放到論辯館里也評不上什麼名次,便都放在匣子了。哦,只有幾首當年那季二公子……呵,是那不要臉的東西覺得太好謄抄了回去。”
姜韶聽的目一閃,問香梨:“我自己親筆寫的詩詞沒有給那季二公子?”
香梨搖頭,冷哼了一聲。先時瞧著那姓季的對小姐慕有加詩信不斷,勉強看他順眼了一些,料之后那季二公子以貌取人,背信棄義,反手還捅了小姐一刀,是以香梨徹底厭惡上了季崇歡,連姓名也懶得喚,干脆道:“那個不要臉的東西自大的很,小姐本想將詩送給他,他卻嫌小姐的字寫得太過清秀不夠遒勁有力,自抄了回去。”
Advertisement
姜韶點了點頭,“嗯”了一聲,待到泡完藥浴也未多言便讓香梨將匣子拿了過來,而后便將那些詠民間百姓的詩作挑了出來。
將每首詩作都看了一遍,姜韶神有些復雜。知曉原主是個難得的詩才,可原本以為原主因自被姜兆所護,不通外事,所作也不過是一些傷春悲秋的小兒長之作,只是沒想到原主還做過這等詩詞來。
“叢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姜韶默念著,也不知原主從哪里聽到的關于二十年前那些兵士的過往由此而作。雖未曾經歷過,卻因天生敏擅于共,這詩作確實寫得極好。
只是再好,也不能留!姜韶眼里閃過一厲:雖說原主作詩時不曾多想,只是其中幾首詩若是旁人有心,完全可以指借景喻人,留前朝,對天子有怨言。
先前之所以未曾鬧出什麼事來是因為知曉這些詩的除了原主以及半吊子本記不住幾句的香梨之外,也只有季崇歡了。好在季崇歡同樣不懂時政,這才沒有意識到什麼。
若是他稍稍于時政敏一些,單憑這些詩,只要稍作文章,東平伯整個伯府就足夠毀于一旦了,而不是如現在這樣只一人被趕到寶陵來。
姜韶將挑出的幾首詩作投到桌上的油燈里,看火舐著這些手作,直至化作灰燼。
想,姜兆若是看到這些詩作也會與做出同樣的選擇來
比起一時的有而發,整個東平伯府不傾覆自然更重要。
至于季崇歡謄抄的那些詩作,若是不拿出來,那便相安無事,若是要拿出來大做文章構陷于,那空口無憑,誰能證明那些詩作是寫的?而不是季崇歡本人寫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休夫
挺著六月的身孕盼來回家的丈夫,卻沒想到,丈夫竟然帶著野女人以及野女人肚子裡的野種一起回來了!「這是海棠,我想收她為妾,給她一個名分。」顧靖風手牽著野女人海棠,對著挺著大肚的沈輕舞淺聲開口。話音一落,吃了沈輕舞兩個巴掌,以及一頓的怒罵的顧靖風大怒,厲聲道「沈輕舞,你別太過分,當真以為我不敢休了你。」「好啊,現在就寫休書,我讓大夫開落胎葯。現在不是你要休妻,而是我沈輕舞,要休夫!」
65.8萬字8 77347 -
完結453 章

鳳回鸞
世人皆知太子長安資質愚鈍朝臣們等著他被廢;繼後口蜜腹劍,暗害無數。他原以為,這一生要單槍為營,孤單到白頭不曾想,父皇賜婚,還是裴家嬌女。那日刑場上,裴悅戎裝束發,策馬踏雪而來:“李長安,我來帶你回家!”.自此,不能忘,不願忘。
78.4萬字8 14187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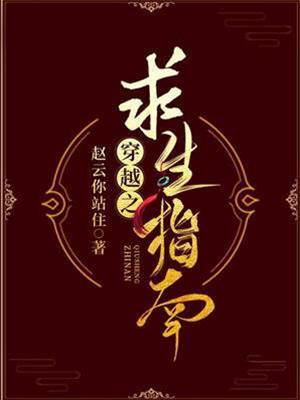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連載1300 章

家侄崇禎,打造大明日不落
魂穿大明,把崇禎皇帝誤認作侄兒,從此化身護侄狂魔!有個叫東林黨的幫派,欺辱我侄兒,侵占我侄兒的家產? 殺了領頭的,滅了這鳥幫派! 一個叫李闖的郵遞員,逼我侄兒上吊? 反了他,看叔父抽他丫的滿地找牙! 通古斯野人殺我侄兒的人,還要奪我侄兒的家業? 侄兒莫怕,叔父幫你滅他們一族! 崇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切都不存在的,朕有皇叔云逍,可只手補天! 李闖:若非妖道云逍,我早已占據大明江山......阿彌陀佛,施主賞點香油錢吧! 皇太極:妖人云逍,屠我族人,我與你不共戴天!
231.8萬字8.18 231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