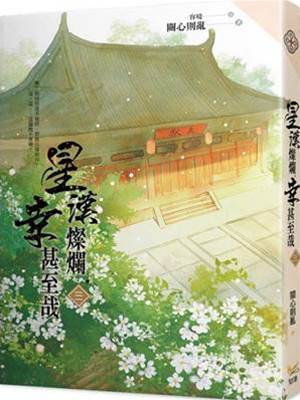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炮灰養包子》 125、第 125 章
“要不,還是找旬老問一問?”事有些發愁,因為旬老那邊不一定會說,他對于蒙家雖十分厭惡反,但關于孟家也是只字不提的。
然他等了半晌,并沒有等來沈夜瀾的答復,反而見他神嚴肅地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禹州這里拖不得了。”他始終不放心孟茯一個人在京城里,不早些將禹州拿下,他就沒有辦法去京城。
事頷了頷首,疑地問道:“那竹州耀州呢?”過了禹州便是此二州,這也是原大齊的舊土啊。
前兒三公子不是還說要將一鼓作氣,將這一片被金國占去的舊土都收復,然后一路往上連著其他數州也一并拿下麼?
沈夜瀾抬首指了指架子上掛著的地圖,“禹州便如同這三州的天然防盾牌,只要將禹州破掉,其他的兩個州府便是唾手可得,有謝老將軍在,難道還拿不下來麼?”
事聽得這話,心中忍不住想,三公子果然是要去京城找夫人。面上點了點頭,看著地圖道:“那三公子幾時回來?”
沈夜瀾指向梁州一帶,“等你們打通這幾個州府,我們便在梁州匯合,再一路往上,如何?”
京城往上,同樣是被金國占去了的梁州,不過此荒涼多黃沙,人煙稀。金國人也不太會治理沙地,所以那一片幾乎就沒什麼人煙了。
也就是剩下寥寥幾個原著人養著駱駝給路過的人提供些便途,賺取幾兩銀子討生活罷了。
事心說三公子倒是會打算,只是還不曉得戰事能不能如同他所預想的這樣順利?
而因沈夜瀾想早些去京城,這攻打禹州的計劃也提前落實了。
金國人還再猜想著,沈夜瀾他們還需得休養個三五日吧?他們也可也趁著這段時間將傷員送到后方,再等后方大軍到來,無論如何也會將禹州守住。
Advertisement
哪里曉得中原人用兵講究一個兵貴神速,趁你病要你命。
所以隔天凌晨,戰鼓喧天,金國人還在夢中,城門就被那該死的火星石炸開了。
他們原本還打算用這禹州城里原來的大齊老百姓做人質的,可都還沒來得及準備,城池就被破開。
是凌晨寅時一刻開戰的,然到了辰時一刻卻已就結束了。
預計以為怎麼也要一天的時間才能拿下的禹州城,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攻下來了。
城中一直著金國人欺辱的原大齊老百姓最是歡喜,幾乎金國人的殘兵剛逃走,他們便歡天喜地地給沈夜瀾的軍隊送了不東西來。
不是什麼好東西,論資他們一直被金國人剝削,自然是沒有什麼好的。但禮輕人意重,貴在一片心意。
而讓這麼快的時間能攻下禹州城,到底還是大齊一直被金國和遼國欺多年了,從來都只有俯首忍讓的選擇,所以在金國人看來,他們對大齊的印象還停留在當年奪取這些州府時候。
一個被欺的國度,怎麼可能會過得越來越好呢?所以即便南海郡那邊傳出怎樣的消息,比如說糧食翻倍收,或是吃不盡的鴨魚蔬菜,他們都是不相信的。
反而當時笑話一般,還給編了歌謠。
殊不知這一切都是真的。
只是他們沒有辦法去相信,一個弱小的國度,怎麼可能過得越來越好?按照常理他們沒有了大部分的資源,不是越來越差麼?
所以這一次完全是被打得措手不及。
原本被大齊朝廷拒絕賠償之后,他們是打算集結軍隊嚇唬嚇唬,倘若可以的話,也不是不可以順便將南海郡奪過來,到時候再給大齊朝廷提賠償,可不是現在那樣簡單了。
Advertisement
只是,過分的自信所迎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屈辱。
自從在九龍海沙溪島附近第一次開戰后,他們就節節敗退,對方就像是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一般,剛打完一場還沒休息半個時辰,第二場又接著開始。
讓他們金國軍隊連個氣的時間沒有。
不但如此,對方更是讓人覺得恐怖,似乎這海里一個從海水里冒出頭的礁石,他們都能清楚地知道位置一般?
金國的幾艘載滿了援軍的船只,就被他們的人引導著撞在了那礁石上,白白掛穿了船底。
所以援軍本就沒有辦法按照原本的時間所支援,這勝利自然是無了。
因此只得一路退,退到了禹州城,想著這里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應該是可以放心了。
這禹州城外雖然沒有像是南海城一樣,被星盤山像是天然屏障一般保護著,但是那城門口卻有著比任城池外的護城河都要寬數倍的護城河。
上面的橋被毀掉后,對面想要大批量地攻打進城,除非有足夠的大船。
不然若是乘坐小船的話,他們在高高的城墻上,輕而易舉就能讓其全軍覆沒。
但是大船他們在短時間里,怎麼能從海里拖運到此?
這里離海邊還有一定的距離呢?
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大膽地做準備。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司馬家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就混這城里了,可載數萬人的船只當夜就拼湊起來,駛護城河中。
本以為可以守下去的禹州城就這麼被破開了。
金國人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本來又只剩下些殘兵敗將,落魄逃走。
而此刻占據于禹州城,將這原本的州府衙門作為軍機要出的沈夜瀾等人,正在商討如何進行下一步,趁著這口戰氣,繼續將竹州耀州收復。
Advertisement
制定了計劃,他也開始以金蟬殼之計直接離開禹州,往京城而去。
開展前夕,軍中主帥不在是大忌。
不過如今禹州已經攻破,竹州耀州謝老將軍志在必得,也有那個自信,加上邊還有這麼多沈夜瀾留下的能人異士,資又富不短缺半分。
手底下還多的是搶兵悍將,收復竹州耀州也就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更何況收復舊土山河,這是他多年來的夢想,如今沈夜瀾將這機會留給自己,心中更是激。
再有沈夜瀾往京城去,也不單只是看孟茯,如今他份特殊,陛下對于孟茯這個兒又十分寵,到時候指不定他真能得到其他的幾支兵權,直接帶人到梁州,與大家匯合,一起將剩余的大齊山河給收復。
所以沈夜瀾離開的三天,他們就開始準備攻打竹州。
京城之中,也收到了直接從南海郡發出的捷報。
自從蒙家軍之后,大齊還沒有這般揚眉吐氣過,如今不但直接將禹州給收復,如今還繼續打算攻進竹州耀州。
齊皇自然是高興不已,下了朝便來到這玉簪宮,直接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孟茯。
孟茯聽到禹州在這麼短的時間里被收復,金人戰敗,自然是高興不已。于是忙問道:“那我幾時可以回南海郡?”就算不能馬上回南海郡也行,如果能出宮走一走也好。
但這話讓李尚不免是有些失落起來,“阿茯就這樣不愿意陪著父皇?”
其實孟茯對于李尚這個慈父的人設是認可的,而且對于自己的偏也有些無度了。
這些天里聽三嫂柯子瑾說,他如今是竭盡全力地支持九龍海灣的戰事,與當初將南海郡當作是孤兒一般不聞不問的態度正好截然相反。
這沒有與自己相認之前,除了給南海郡撥了五萬的大軍之外,什麼都沒有,半分多余的糧草軍資就更不要提了。
還要將自己當做人質。
而現在呢……
可對自己是好,這一點不摻假,那對于別的子呢?
孟茯現在還在犯愣,往后若是與李馥相見,是要怎麼個稱呼?
所以拒絕回答李尚這個問題。好在李尚也沒有多糾結,他今天心里高興,迅速轉過話題,“聽說有意繼續將竹州和耀州也一并收復,所以阿芙啊,你暫時走不了,你還得多在這宮里陪陪朕。”
孟茯其實一點都不意外,既然已經大干戈了,總不能就此歇戰了吧?只是這樣一來,多半是要數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了。
南海郡那邊來京城之時,雖都已經做好了安排,可是那里已經儼然被孟茯當做了故鄉一般的存在,如今離家久了,即便在夫君并未在家,但孟茯仍舊是掛懷得很。
忍不住擔心道:“我不在家這麼久,也不曉得孩子門口是聽話。”
李尚聽聞提起那些個孩子,卻是沒有一個是兒親生的,尤其是想到那三個孩子還是魏家的外孫,便道:“朕立即下旨讓魏家將人給接回來,你自此后就不用管了。”
孟茯連攔住,“不可。”
李尚一怔,兒這是隨了他,專門給人家白養孩子?看看那李兆,可不就是養了個白眼狼出來麼?本意是想著蒙家不管如何,雖說濫用藥,但那些功勞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所以他愿意給李兆一個份,讓他一輩子做個閑散王爺。
只是斷然沒有想到,卻是包藏禍心。
“阿茯,你何苦給人養孩子?往后人也長大了,也不一定能念著你的好。”他苦口婆心地勸著,斷然如何也不能讓兒走自己的老路。
卻見孟茯一臉自信道:“怎麼不能,我們共患難也共富貴過,如果真有二心,也不用等到將來,現在他們大可直接走。何況每一個孩子都是我悉心養大的,若還有那樣的好本事,我更舍不得放他走呢!”
說起這個孩子,李尚倒是想起來了,他的確是有天大的功勞。
從前也是想過授他爵,無奈還太小了。
如今不免是有些起心來,“這孩子的確是可造之材,將來等他大了些,朕給他許個好去。”
“這到犯不著,他自己有本事,便自己去爭取,沒本事繼續留在田間,也是一樣能造福百姓的。”何況他們已經被自己教育得不一定要求得功名利祿才算是真正的耀明楣。
所以功名這個事,孟茯覺得隨緣了。
李尚見這不要那不行的,心中想果然是自家的孩子,若是別家的只怕早就不得等著要求這樣那樣的。
于是看孟茯是越看越喜歡。
然后又想起從前的那些苦日子,越發憐惜,然后便開始琢磨著要替建造什麼公主府。
孟茯是隔天才曉得的,所以晚上李尚來陪吃晚膳,連忙勸道:“你莫要白浪費那些銀子,就算是建出來了,我也不可能去住,豈不是白白浪費?有那些銀子,您倒不如花費在別。何況禹州雖已經被收復,可是到要整頓,那里的老百姓們過得又十分凄苦,您將心思放在老百姓上,也算是積福。”
這明顯是在教皇帝做事啊。可是李尚看孟茯是帶著濾鏡的,不但不惱反而覺得這果然才是自己的親兒,一心為自己著想,說得又都是實話,一點奉承都沒有。
于是連記在心里,隔日上朝便與諸位大臣商討禹州重建。
大齊唯一一座可接納其他國家船只的碼頭,可就修建在禹州,如果大肆利用,可就是取之不盡的碼頭。
玲瓏從宮人們口中聽得此言,忍不住朝孟茯羨慕道:“你爹真聽你的話,你昨兒才提,他今兒就開始給你辦了,要我說不如你留一直留在這宮里算了,有你天天守著他,想來用不了十年八年的,咱們大齊各州府就跟南海郡并肩了。”
孟茯聽得這話,忍不住翻了個白眼,“你是嫌我活得太久了麼?若是有心人聽進去了,不知道多人要討伐我呢?”
“討伐你作甚?你又沒做什麼壞事。”玲瓏不解,這可都是為國為民的好事。
卻只聽孟茯說道:“又不是銀子,人人都喜歡,有人想做好,想為老百姓多謀些福利,可是有的卻只想從老百姓上多搜刮些錢財。”
猜你喜歡
-
連載337 章

獵戶農妻寵上癮
一覺醒來,竟成了古代某山村的惡臭毒婦,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就算了,還被扣上了勾搭野漢子的帽子,這如何能忍? 好在有醫術傍身,於是,穿越而來的她扮豬吃虎,走上了惡鬥極品,開鋪種田帶領全家脫貧致富的道路。當然更少不了美容塑身,抱得良人歸。 隻是某一天,忽然得知,整日跟在身後的丈夫,竟是朝廷當紅的大將軍……
58.4萬字8 5668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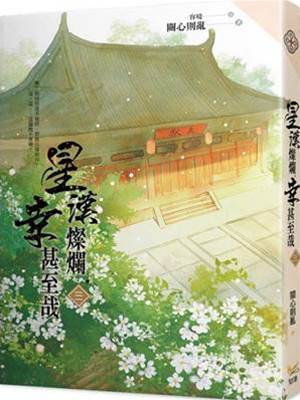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80 章

再嫁
破鏡可以重圓?她不愿意!世人皆說,寧國候世子魏云臺光風霽月,朗朗君子,明華聽了,總是想笑,他們怕是不知,這位君子,把他所有的刻薄,都給了她這個原配結縭的發妻。而她唯一的錯,就是當初定下婚事時未曾多問一句罷了。誰能想到,讓魏云臺愛慕至極,親自…
31.3萬字8.17 48598 -
完結331 章

寸寸歡喜引相思
她本是西楚國侯爺之女,因一碟芝麻糕與東陽國三皇子結下不解之緣。卻因一場府中浩劫,她逃生落水,幸被東陽國內監所救,成了可憐又犯傻氣的宮女。一路前行,既有三皇子與內監義父的護佑,又有重重刀山火海的考驗。她無所畏懼,憑著傻氣與智慧,勇闖後宮。什麼太子妃、什麼殿下,統統不在話下!且看盛世傻妃如何玩轉宮廷、傲視天下!
82.6萬字8 85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