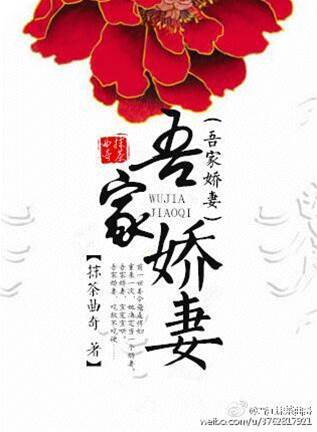《娘娘每天都在盼著失寵》 第三十五章 朕喜歡嘗試新事物
“不裝了?嗯?”宋燁坐在床邊,瞧著某人被抓包時的心虛之,面上出些許悅。
長安里還含著小半截脖子,腮幫子鼓鼓囊囊,明亮的眸子,直勾勾的盯著他,狗皇帝怎麼還沒走?
“滿屋子香味,打量著所有人都沒鼻子嗎?”說這話的時候,宋燁的視線落在晶亮的角。
吃不,還留下這麼明顯的證據,川河還真是慣得!
長安腦子里滴溜溜的轉,正想著怎麼把這尊瘟神送走,豈料宋燁忽然手。
溫暖的指腹輕在角,替拭去點點油花,下一刻,他兀的指尖輕佻,作嫻的鉗住的下顎,直接迫使長安張了一下。
長安驀地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的瞪著他。
只覺得口中一涼,含在口中的脖子瞬時被他的指尖勾出,他另一手托著帕子,正好承接住脖子,帕子一卷便擱在了床頭凳上。
宋燁的作一氣呵,幾乎沒有半分猶豫,臨了瞧著呆若木的,挑了桃花眼,溫聲叮囑,“親手洗干凈,再還給朕,懂?”
“懂!”長安咂吧著,扭頭瞧著床頭凳,倒是可惜了那截脖子。
宋燁眉梢微挑,兀的住的下顎,將的臉扳回來,“以后回答朕的時候,看著朕!”
Advertisement
“懂!”拂開他的手,嫌惡的著下顎。
手勁可真大,得有些疼。
“子好些了?”他將枕邊的帕子出,慢條斯理的拭著自己的指尖。
宋燁半垂著眼,長安瞧不清楚他的緒的變化,只看到他半垂的長睫,分明,如黑羽所制的小扇子,真真比子的還要纖長卷翹,倒是與他這個皇帝的份,頗為不符。
“沒呢!渾疼。”長安當即為自己掖好被子,眉心徐徐擰起,一副病怏怏的模樣。
宋燁隨手將帕子丟在邊上,子斜側,薄輕挽,合著那雙桃花眼,竟帶著幾分攝人的邪氣,“真的?”
“真的真的!”長安連連點頭。
宋燁深吸一口氣,“傷著何?”
“腳踝!”長安煞有其事,“傷筋骨一百天,大夫說了,我要靜養三個月!”
宋燁的視線落在面上,瞧著無比認真的雙眸,若不是知道的劣跡斑斑,怕是真的要信了。
下一刻,宋燁掀開被子一腳。
“皇上?”長安心驚,一把摁住他的手。
若是教他發現被窩底下藏著燒,肯定疑心裝病,會把逮回宮里去!好不容易有借口留在宮外,才不想回宮,去太學堂聽太傅念經。
宋燁斜睨一眼,眸中帶著清晰的警告。
Advertisement
長安脊背驟涼,下意識的回手。
輕輕掀開的腳,瞧著被繃帶纏繞的腳踝,淡淡的藥味迅速彌漫開來。
宋燁眉心微蹙,眸底似有什麼東西,一掠而過,他定定的瞧著的腳踝半晌,“傷著骨頭了?”
“扭著了!”長安不敢說得太嚴重。
斷骨這種事太嚴重,狗皇帝萬一心來去問大夫,那可就是欺君之罪,惹不起、惹不起!
室忽然安靜下來,宋燁沉默了。
長安懸心,若有所思的瞧著眼前的皇帝,不知道為何,總覺得皇帝心里藏著事,而且這事同有關。
“皇上?”長安突然笑嘻嘻的瞧著他,“您驗過貨了,現在相信了嗎?這段時間,臣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宋燁冷冷的打斷的話。
長安輕嗤,“臣都還沒說完呢,皇上如何知曉,臣要說什麼?”
“你的書房行走之職,是朕親封,而且你接了戶部尚書的案子,等同于立了軍令狀,若是查不出兇手,你覺得躲在丞相府便可行了?”宋燁起,負手而立。
長安啞然,論吃喝玩樂,委實行,但論起這朝廷之事,還真的懟不過狗皇帝。
“那臣可以提個要求嗎?”退而求其次總行吧?
宋燁沒回答,只挑了那雙桃花眼看。
Advertisement
“皇上別有事沒事往丞相府跑,免得不知的人以為,皇上有對恩寵于臣,到時候臣又得被人惦記上,鬧不好您后宮的那些妃嬪也得跟著吃醋,臣可擔不起這麼大的罪名!”別開頭。
宋燁輕呵,“若朕不答應呢?”
“皇上不會不答應!”仰著他,“大夫說了,臣需要靜……”
這“養”字還沒出口,宋燁的臉忽然在的視線里放大,下一刻,已近在咫尺,他的胳膊抵在的面頰兩側,可勁的往后靠,后的墊被得嚴嚴實實,再也無法后撤。
這世上的所有東西,越靠近越看不清楚。
如,似人。
就好像現在,長安本看不清楚宋燁的臉,模糊的只看到他長睫下,那雙幽邃如墨的瞳仁,清晰的倒映著自己的驚詫的容臉。
時間仿佛停止,呼吸一窒,一顆心已然蹦到了嗓子眼。
往常,都是風月樓的姑娘,戲弄打趣著們,如今搖一變,自己好似了們的一員,而那個占據主權的人卻變了宋燁。
宋燁的容臉離很近,鼻尖幾乎抵上了的鼻尖,溫熱的呼吸,就這樣毫無距離的,噴薄在面上,“別惹朕生氣,別總想著逃跑,乖一點,知道嗎?”
“皇、皇上?”長安眼神閃爍,不敢再去看他的眼睛,下意識的別開視線,“您這是作甚?”
宋燁勾,笑得妖冶而邪魅,“朕這人……喜歡嘗試一些新事,后宮三千有些膩了!”
膩了?
長安眉心突突跳,新鮮的事?
皇帝是指什麼?
難道皇帝是……
瞧著羽睫忽然揚起的瞬間,宋燁愈發笑得勾魂,一雙桃花眼,翻涌著灼灼之,他往前湊了湊,正好伏在耳畔,磁重的聲音極盡蠱,“安安……想明白了嗎?”
長安呼吸微促,腦子忽然清靈,狗皇帝……是個斷袖?
安安?
安你個鬼。
長安攥拳頭,揮手便是一拳。
宋燁眼疾手快,迅速抓住的皓腕,“挨一次就夠了,再來一次,那就是蠢!”
門外,驟然響起曹風的聲音,“丞相大人!”
宋燁心下一怔,當即松了手。
誰知……“啪”的一聲,響聲清脆。
震得剛進門的川河形一震,快速將邁進門的腳了回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