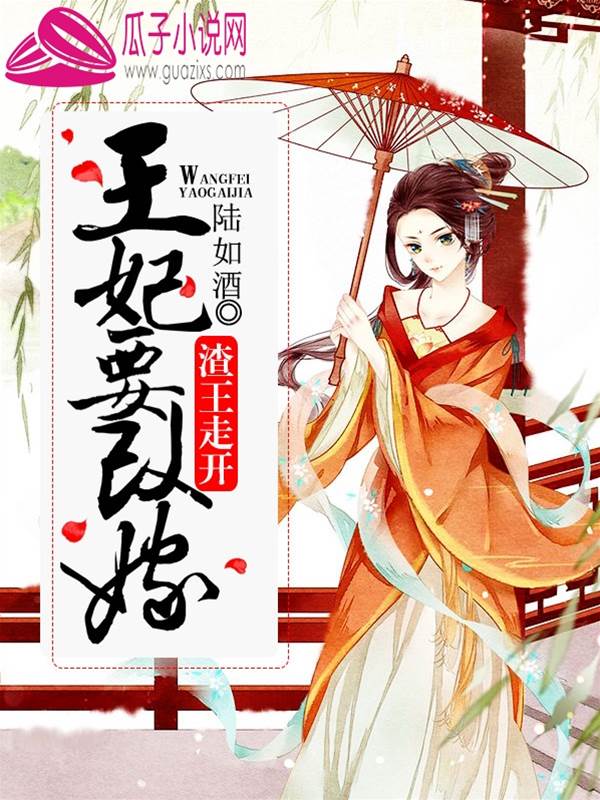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世子爺他不可能懼內》 第73章 被折騰的夠嗆
當白晝驅走黑暗。范坤略顯疲憊,頭重腳輕的出了正軒居,出府上朝。
他的臉上有些難看,眼底青明顯。想來是一夜未眠。
虛了。
除卻這一點,一切都如往常般。沒有鬧起半波。
可到底還是有不一樣的。
檀云繪聲繪撿著從廚房那頭聽來的消息道:“聽說昨兒夜里正軒居上下奴才都被折騰的夠嗆,屋里主子左右了不下五次的水。這是以往從來沒有的。”
“奴婢還聽說許氏慘了一夜。斷斷續續都沒帶停,如今這會兒還歇著,就連給老太太請安一事都落了下來。”
未經人事,大大咧咧說著這番話,毫不見意。
可……
慘了一夜!
想來被折騰的夠嗆。
葛媽媽當下臉一變,板著一張臉訓斥:“這些腌臜話,你當著姑娘提什麼提!”
檀云一臉迷茫:“我就是想問問為什麼慘一晚上,難不表公子還手打人不?”
說著,看向阮蓁。
葛媽媽氣:“你看姑娘做什麼?姑娘能知道些什麼!”
阮蓁卻是心尖一跳。
還真知道。
可未出閣的姑娘如何會懂這些?
子面容是一貫來的冷靜,聽到自己佯似不解道。
“總不能許氏被打的半死不活,侯府顧及名聲,不讓傳召大夫?毆打正室,這的確是件腌臜事,不然怎會沒聽見半點風聲,就連心切的許家夫人都不曾登門質問給許氏撐腰。”
Advertisement
說著,心含愧疚的將難題拋給葛媽媽。
“媽媽,你覺得呢?”
檀云見阮蓁分析的甚是有道理。當下點點頭,跟著看向葛媽媽。
面對兩雙無辜又清澈的眸子,特別是阮蓁那水盈盈任誰見了都忍不住心生憐。
葛媽媽:……頓力。
到底都是姑娘家,對這些男之事一知半解。也不足為奇。
好半響,含糊其辭。
“興許是吧。”
檀云著一不的呆兔子。卻是陷了死胡同。
“可若是這般,也不應該啊。”
“我今早出院子,還見王媽媽,可是一臉喜。笑的那一個花枝。”
若許氏真的有礙,王媽媽哭都來不及。
阮蓁:……這種事,刨問底的做什麼?
不過,以王媽媽的這番反應,想來是許氏得逞了。
阮蓁眸一閃,陷深思。
那藥喝了,可會影響子?許氏又能得意多久?
是不是得同心糾結許久,念叨多次的慕玖說一聲?
葛媽媽:……
當機立斷二話不說手就去擰檀云的耳朵。
“說了幾次了,正軒居那邊的事去打聽。”
“如今侯府多雙眼睛盯著姑娘,雖說現今得國公府庇護,可正因為如此,范老夫人失了好大的臉,焉能不氣?”
Advertisement
可萬不能里沒個把門,這些話讓有心之人聽了去,給姑娘一個管教不嚴的罪責,可不就是平添麻煩。
檀云當下吃痛:“不說了,不說了,媽媽輕些。”
——
到底是花了心思,接下來的幾日阮蓁趕慢趕忙著刺繡,總算在盛挽生辰宴前一宿制完。
翌日,起的極早。
阮蓁底子白,說是冰玉骨也不為過。
仙姿佚貌,靡膩理。瞧著哪哪都。著一水湖藍領褙子,下配梨花白長。黛眉杏眸,面似芙蓉。
葛媽媽手指靈活的盤著發:“這好,不會過于素雅更不會喧賓奪主。”
阮蓁目沉靜的看著銅鏡里的子。
而后垂下眸子,嗓音輕:“我這些日子不知為何,總是心慌。”
這話一落,葛媽媽手一抖,剛盤好的發髻跟著散了下來。
阮蓁安的沖淺淺一笑。
正軒居那邊不曾鬧出什麼靜。
除卻那些婆子時不時低低閑談,夸幾句范坤英勇,都是些俗言辭,便再無其他。
若不是撞見許氏捧著扁平的肚子小心翼翼走路的稽模樣,都要懷疑對方沒下藥。
“我一直留意著,原以為這件事能鬧的府上能上一,于我們也有利。”
Advertisement
可左等右等,除了察覺出范坤的眼線盯著們這個院子,再去其他。
阮蓁從首飾盒里取出耳墜。
“如今城門搜查松懈不,花朝節那天除卻將軍府大開宴席,臨安街道更會熱鬧非凡,商販,游客絡繹不絕,夜市大開,取消宵,將會有不人進京。”
“葛媽媽,馬車的事,還需你出趟門打點。”
葛媽媽正,阮蓁的意思是花朝節當日走?
也是,免得日常夢多。
“姑娘且放心,上回那馬如今養的健壯著呢。車夫我也早已妥當。”
葛媽媽辦事穩妥,阮蓁向來放心。
正要再說什麼,就見檀云開布簾,從外頭走了進來。
“姑娘,老夫人派了邊伺候的申婆子過來傳話。”
而后氣鼓鼓道:“一個傳話的婆子,說到底不過也是個奴才,難不還有三六九等?姑娘且莫被氣著。”
傳話?
范老夫人這是打算做什麼妖?
阮蓁心底一哂。面上卻不顯。
“請進來。”
很快,檀云領著穿著甚是面的婆子。
只見那婆子手腕上掛著金鐲子,發髻上別著銀簪。
申婆子是府的老人了,伺候范老夫人多年盡心盡力,就算再范承面前也說得上話。
一便打量阮蓁一眼,而后福了福子:“給姑娘請安。”
阮蓁由著打量,淡淡道。
“老夫人有什麼話我走一趟便行,還勞煩媽媽你專門跑這一趟。”
申婆子一板一眼道:“主子傳喚,哪敢推辭?這是老奴的本分。若奴才不像奴才,這侯府豈不是了套?”
本分?
阮蓁聽著這兩個明顯加重語調的字眼,心下了然。
范老夫人是專門讓來下馬威的。
“一大家子榮辱與共,若沒有侯府,哪有姑娘的今日,您今兒走出去,即便認了干娘,可說到底您還是侯府的人,必然得維護侯府的面。”
阮蓁靜靜的聽說著,一言不語。
“老夫人說了,姑娘是個聰慧的,定然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081 章
神醫仙妃
一朝穿越,被綁進花轎,迫嫁傳聞中嗜血克妻的魔鬼王爺? 挽起袖子,準備開戰! 嗯?等等!魔鬼王爺渾身能散發出冰寒之氣?豈不正好助她這天生炙熱的火型身子降溫? 廊橋相見,驚鴻一瞥,映入眼簾的竟是個美若謫仙的男子! "看到本王,還滿意麼?"好悅耳的嗓音! "不算討厭." 他脣角微揚:"那就永遠呆在本王身邊." 似玩笑,卻非戲言.從此,他寵她上天,疼她入心;海角天涯,形影不離,永世追隨.
101.5萬字8 118905 -
完結674 章
農門醫女:掌家俏娘子
郭香荷重生了,依舊是那個窮困潦倒的家,身邊還圍繞著一大家子的極品親戚。學醫賺錢還得掌家,而且還要應對極品和各種麻煩。 知府家的兒子來提親,半路卻殺出個楚晉寒。 楚晉寒:說好的生死相依,同去同歸呢。 郭香荷紅著臉:你腦子有病,我纔沒說這種話。 楚晉寒寵溺的笑著:我腦子裡隻有你!
125.4萬字6.3 81043 -
完結180 章

藏歡
太子沈鶴之面似謫仙,卻鐵血手腕,殺伐決斷,最厭無用之人、嬌軟之物。誰知有一日竟帶回來一個嬌嬌軟軟的小姑娘,養在膝前。小姑娘丁點大,不會說話又怕生,整日眼眶紅紅的跟着太子,驚呆衆人。衆人:“我賭不出三月,那姑娘必定會惹了太子厭棄,做了花肥!”誰知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那姑娘竟安安穩穩地待在太子府,一路被太子金尊玉貴地養到大,待到及笄時已初露傾國之姿。沒過多久,太子府便放出話來,要給那姑娘招婿。是夜。太子端坐書房,看着嬌嬌嫋嫋前來的小姑娘:“這般晚來何事?”小姑娘顫着手,任價值千金的雲輕紗一片片落地,白着臉道:“舅舅,收了阿妧可好?”“穿好衣服,出去!”沈鶴之神色淡漠地垂下眼眸,書桌下的手卻已緊握成拳,啞聲:“記住,我永遠只能是你舅舅。”世人很快發現,那個總愛亦步亦趨跟着太子的小尾巴不見了。再相見時,秦歡挽着身側英武的少年郎,含笑吩咐:“叫舅舅。”身旁少年忙跟着喊:“舅舅。”當夜。沈鶴之眼角泛紅,將散落的雲紗攏緊,咬牙問懷中的小姑娘:誰是他舅舅?
34.4萬字8.18 31786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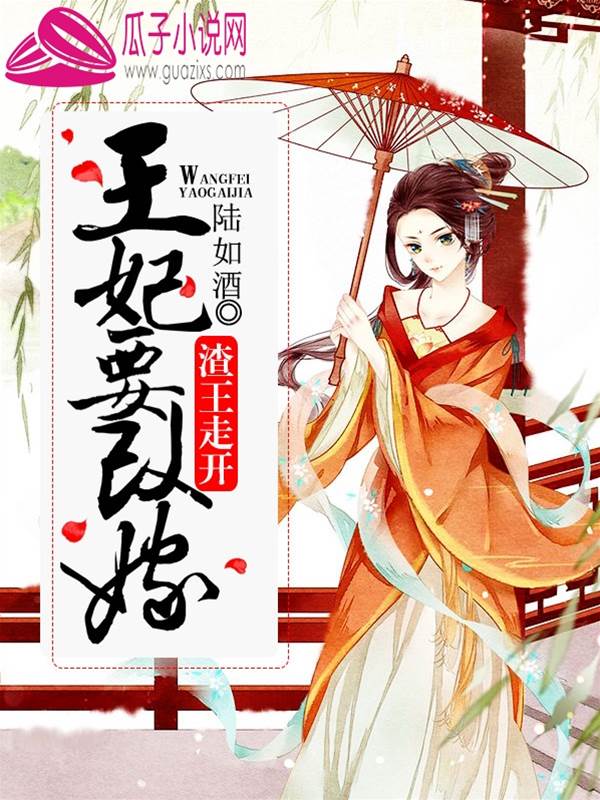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79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7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