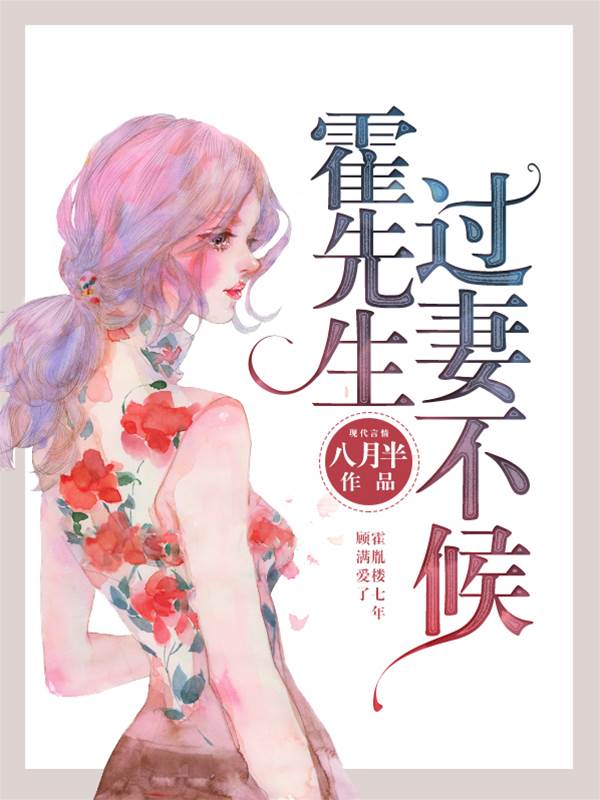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帶球跑后霸總跪求我復婚》 第50章
大約是因為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腦海里一直翻滾著一些不安分的東西,讓葉欽以為自己一直沒睡著。
那些東西繞繞的,就像是在棉花糖機里迅速融化由冷凝的砂糖, 纏繞出一些如云似霧的形狀, 與其說是完整的思緒, 不如說是被的回憶。
從冬天到夏天, 從黃昏到黎明, 葉欽想到的全是零零碎碎又毫不相關的東西。
他想起了結婚第二年的時候, 峻帶著他去櫻桃園摘櫻桃。那些果樹改良過了,并不高。葉欽卻喜歡那些生得最高的大櫻桃, 那些櫻桃接了足夠的日曬, 個個都有啤酒瓶蓋那麼大, 紅得發黑了,在日里閃爍著寶石一般的芒。
他想把那些大櫻桃摘給峻吃。
葉欽踮著腳尖, 抓住低的枝丫,借力向上跳,卻總是差一點點。
腰間一,地面就突然遠離了。他驚訝地低下頭,發現是峻把自己抱起來了。
峻仰著頭, 著虎牙的壞笑在被樹影切碎的中有一種陸離的爽朗。
“喜歡嗎?”
“喜歡嗎?”峻站在燒烤架邊,把一串烤好的羊遞給他, 帶著一點小得意,“我從西蒙背回來的。”
葉欽不喜歡牛羊,但還是開心地接過來:“嗯, 喜歡。”
四周有一些面目模糊的人, 哈哈大笑地揶揄著:“爺也有今天啊,千里背整羊, 只為博人一笑!”
“誰說不是呢,剛烤好就急不可耐地拿上去邀功呢!新婚就是不一樣啊哈哈哈哈!”
峻的冷臉上溢出一微笑:“閉啊,大雪天喊你們過來玩BBQ,再廢話請你們吃簽子。”
“葉欽過來,”峻拉著他的胳膊在燒烤架旁邊坐下,“幫我看著這串松茸,別糊了。”
Advertisement
那個時候的葉欽當然是峻說什麼就聽什麼,無比認真地盯著那串黑乎乎的東西,但其實他本就不知道烤什麼樣就算糊了,因為本來就是黑的嘛。
那群人又哄笑起來:“不行了我要不行了,疼老婆就疼老婆嘛,你不就是怕凍著人家,還說讓人家給你看著蘑菇。”
“看松茸,不好意思我污了!”
“的酸臭味,要不是看在你這有鹿,才不來這上干火。”
“爺我也冷,我也想挨著烤架坐,我也想給你看松茸哈哈哈哈……”
“滾滾滾,讓你們串串兒,就知道貧,等會兒把你們這撮兒小王八蛋全攤在烤架上煎一鍋……”峻的聲音逐漸遠了。
葉欽抱著膝蓋坐在燒烤架旁邊,看著傘篷外面鵝般的大雪紛紛揚揚地飄落,邊是一種很干燥的溫暖。
當時的他看著不遠峻高大筆的背影,心里也是快樂的吧?
沒過多久他聞到一若有若無的焦糊氣息,急匆匆地一低頭,看到那串松茸居然著火了,而且就像是澆了汽油,那麼小的一串真菌居然騰起了半米高的火舌,火星燎到了他的羊外套。
葉欽慌了,他想從回憶中掙出來,他想告訴峻自己沒有把松茸烤糊。他迫切地想要辯白:這只是一個夢。
火焰變得無比的真,連帶著夢境都變得滾燙,讓葉欽無法掙。
他拿起那串松茸,想把它扔到雪里,卻聽見峻的聲音在很近響起:“葉欽!葉欽!!”
火從睫間泄進來,刺痛了葉欽的眼睛。
峻逆著背后白的火焰,臉上沾著不黑灰,額頭鬢角全是汗。他輕輕拍著葉欽的臉:“醒過來了嗎?聽見我了嗎?”
Advertisement
葉欽打了一個激靈,這不是回憶,也不是夢,他下意識地吞咽了一下:“峻?”
房間里面有一種過度的明亮,從房頂到床前,好像一切都變得了半融化的銀白。床正對著的梳妝鏡已經被火舌碎了,在墻上留下了一個黑黢黢的影子。原本掛在翅木架上的服也早就燒盡了,只剩下焦糊的桿子孤零零地杵在原地。
一呼一吸間,空氣熾熱得可怕,好像每一次進出都要帶走所有的水分,把一串串燎泡作為足跡。
著火了。
不過幾秒鐘,卻像是過了很久。
呼吸變得愈發困難,葉欽下意識地護著肚子,心跳慢慢快了起來。他撐著子想從床上坐起來,卻一點力氣也用不上。
他本不了。
一塊疊了幾層的巾就掩住了他的口鼻,峻的聲音很低沉也很溫,卻沒有慌張焦急,就像是叮囑他看著那串松茸:“不怕,抱我。”
不知道是水還是汗,峻的服有些,但是也變一種燙手的干燥。像是種子新生的,葉欽的手指慢慢攥了。
“好巾,會有一點不舒服,我馬上帶你出去。”峻把他橫抱起來,小心地護在前,放低朝門口走。
葉欽的目越過巾,在火中本就看不見路,他大概能分辨出柜和茶幾,也都在熱流中扭曲了一個個虛影。
他的聲音不由有些抖,小聲地問:“峻,我們怎麼出去?”
峻子躬得更低了一些,呼吸也有些不平穩:“從我來的路出去。”
“我自己下來走吧。”葉欽低聲說,他其實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走不了路了,因為現在四肢都有一種很陌生的麻木,大概是因為吸了煙氣,連意識都有一點模糊。
Advertisement
但是峻的臉上也有一種不健康的紅,連汗都被蒸干了,那頭一向打理得很心的卷發被燎到了好幾,不漂亮了。
他不想連累峻,又加了一句:“我沒事兒。”
“我知道,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必須要抱著你才行。”峻用下蹭了蹭他的頭頂,口吻中帶著安,“讓我抱一會兒,乖。”
葉欽攥著峻的襯衫,愈發地分不清夢境和現實。他好像又看見了那一串咄咄人的烤松茸,有些迷迷糊糊地半閉著眼睛跟峻解釋:“那個松茸,我沒有烤糊。”
峻一愣,整理了一下蓋在他鼻子上的巾,輕輕拍了拍他的臉:“不睡啊,不可以睡。”
葉欽很乖地重新睜開眼睛,覺到峻的臉在自己臉上,在熾熱的空氣中有種異樣的清涼,他掙扎著想把巾從臉上拿開,卻聽到峻說:“忍一忍,我們到門口了。”
葉欽扭頭看著峻口中的那個門口,荒唐地聯想到了馬戲團里面的獅子跳火圈。門框已經完全被烈焰包裹了,發出“畢畢剝剝”的脆響。
火舌/出來足足半尺長,囂張地空氣中舒展,像是某種妖嬈多姿的海洋生。
人在這種時候,總得要有個抉擇。他和人間的緣分淺,但是峻不一樣。唯一憾的就是葉芽,今天才有了個名字,卻沒機會……
他對不住葉芽。可是峻和這場火沒關系,他得活著。
葉欽了,仰著頭看峻,臉上帶著一個牽強的笑:“你放下我吧,兩個人出不去。”
峻半跪在地上,把已經半干的巾展開了,依舊和地笑著:“誰說的,我給你變個魔啊。”說完就用巾把葉欽的頭臉都包好了。
巾里面很悶熱,葉欽有一些害怕,但是峻的懷抱寬厚堅實,他又沒辦法不相信他。
葉欽看不見外面,只能地抓著峻的襯衫。他能覺到烈火快速的靠近又遠離,甚至捕捉到了火舌在皮上溫熱的一,就像是小時候玩蠟燭,手指在燭火上極快的掃過,溫暖卻不傷人。
他知道峻在跑,因為在他上的有力地收又舒張。中間峻像是為了躲避什麼,劇烈地晃了一下。
“怎麼了?”葉欽的手指一,抖著出聲問。
聽不見回答,葉欽更著急了:“峻?”
過了好一會兒,像是穿過一層看不見的門,冷熱空氣打著卷地融,一陣一陣的喧囂席卷過來,都是人聲。
“出來了出來了!”
“救護車馬上就到了!”
“里面還有人嗎?”
……
峻把他臉上的巾拉了下來:“沒事兒,剛才絆了一下。”他像是有些累,抱著葉欽靠在墻邊坐下來。
有人迎過來想要幫忙:“有人傷嗎?救護車還沒到,還有一小會兒,要不你們到那邊休息一會兒?。”
峻低頭查看了一下懷里的葉欽,手指在他額頭上了,小心把他臉上的灰干凈,對來人說:“他是孕夫,麻煩你給我拿兩杯熱水好嗎?”
那個人很快拿了兩杯溫水過來,峻扶著杯子,把杯沿在葉欽邊:“來,喝點水。”
第一口溫熱的順著口腔食道,葉欽才好像活了過來,恐懼也像是滔天巨浪一樣猛地拍了下來。
空氣中彌漫著火焰肆過的焦臭味,他雙手抓著紙杯,迫切地想用水制心中的慌。
“慢點,慢點,”峻的聲音帶著一點疲憊,卻依舊耐心,輕輕拍著他的背,“我在這兒,不害怕。”
一杯水喝完,峻把另一杯遞給他,葉欽很,卻搖搖頭:“你喝。”
峻把水喂到他邊,笑著說:“我不。”
葉欽正捧著水喝,就見路尋聲氣吁吁地跑過來:“老天,我在哪兒都找不到你!”
見到認識的人,葉欽突然意識到自己一直被峻抱著有些不合適,而且喝過水呼吸過新鮮空氣,力氣也慢慢恢復了,撐著子從峻上站了起來,低聲說:“謝謝你。”
峻抬頭看著他,臉上的笑卻淡了,也不是不高興,只是像高溫中難以為繼的水,慢慢地蒸發了一些。
路尋聲扶了葉欽一把:“真的嚇死我了,他們都說你沒出來,你傷沒有?”
“沒有,不會影響拍攝的。”葉欽搖搖頭,“其他人呢?”
“劇組的人都沒事,”路尋聲舒了一口氣:“那你拍完了戲,還能去國嗎?”
葉欽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峻,聲音低了一些:“去。”
“去國?”峻的聲音很輕,卻很清楚,“你要去國做什麼呢?”
葉欽心里有一種歉意,但他不明白自己憑什麼要對峻有歉意,他咬了咬牙:“生活。”
出乎他意料的,峻沒有吃驚也沒有憤怒,居然出了一釋然的笑容,那個笑那葉欽心里莫名一疼。
“去國生活啊,”峻微微向后一靠,倚在了墻上,手腕搭住屈起的膝蓋,“也好。”
三個人在沉默里安靜了一會兒,救護車的呼嘯由遠及近。
路尋聲突然皺起眉盯著地面,蹲沾了一下從峻后緩緩漫出的深,臉瞬間變了,他抬頭問峻:“你傷了?”
峻答非所問,話里也不知道是幾層意思:“你帶葉欽走吧,讓他開心點兒。”
葉欽的心突然就跳錯了拍,他慢慢蹲下,盡可能輕地扳過峻的上半。
那一面寬厚結實的背,服已經完全燒沒了,焦黑的纖維著面目全非的皮,暗紅的從一個個皴裂的黑傷口中緩慢地滲出來。
葉欽說不出話來,只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腔中猛地撕裂了,把他呼吸的權利都奪走。
“沒關系,”峻輕輕地把葉欽推開一點,重新靠回了墻上,很累似的,眼睛眨了眨就不再睜開,只是喃喃地說了一句,“不要難過。”
猜你喜歡
-
完結1452 章

你與星辰皆動人
被送給做沖喜小妻子的夏安然,隻想裝蠢賣醜,熬死老公後跑路。可是,躺在床上的活死人老公,怎麼轉眼變成了冷酷毒辣、心狠手辣的的商業帝王?最最最關鍵的是……她之前才一不小心……夏安然抱著肚子,卑微的在線求救:現在跑路,還來得及嗎?淩墨:謝邀,人在機場,剛剛人球俱獲。
132.5萬字8 30914 -
完結487 章

蓄意熱吻
(雙潔,男二上位,國民初戀vs斯文敗類) 程微月初見趙寒沉是在父親的退休宴上。 父親酒意正酣,拍著男人的肩膀,喊自己小名:“寧寧,這是爸爸最得意的學生。” 趙寒沉聞言輕笑,狹長的眉眼不羈散漫,十八歲的少女心動低頭。 後來鬧市,天之驕子的男人於昏暗角落掐著美豔的女人,往後者口中渡了一口煙。他余光看見她,咬字輕慢帶笑:“寧寧?” 心動避無可避。 可浪子沒有回頭,分手鬧得併不好看。 分手那天,京大校花程微月在眾目睽睽下扇了趙公子兩個耳光,後者偏過臉半晌沒動。 卻無人知低調的商務車裡,眾人口中最端方守禮的周家家主,律政界的傳奇周京惟捏著少女小巧的下巴發狠親吻。 許久,他指腹擦過她眼角的淚水,斯文矜貴的面容,語氣溫和:“玩夠了嗎?” … 程微月見過周京惟最溫柔的樣子。 正月初一的大雪天,涇城靈安寺,鵝雪輕絮的天地間,人頭攢動,香火繚繞,她去求和趙寒沉的一紙姻緣。 直到周京惟逆著人流朝自己走來,將姻緣符塞在自己手中,“所願不一定有所償。” 他頓了頓,又說:“寧寧,玩夠了就回來。” 佛說回頭是岸,那一天程微月頻頻回頭,都能看見周京惟站在自己身後,於萬千人潮裡,目光堅定的看向自己。 佛真的從不誑語。
87.9萬字8 22718 -
完結484 章

閃婚後,小嬌妻馬甲捂不住了
雙雙被綠,他們一拍即合,閃婚領證。 說好三個月為限,他卻反悔了。 她逃他追,甜寵撩妻。 大家都說夏念安鄉野長大,不學無術, 連裴大少一根腳趾頭都比不上。 只有裴晉廷自己知道,他老婆有一雙神奇的手, 這雙手既能撕白蓮也能握手術刀, 既能拍綠茶也能敲代碼。 他每天都沉浸在扒老婆馬甲的樂趣里,無法自拔!
85.4萬字8 296034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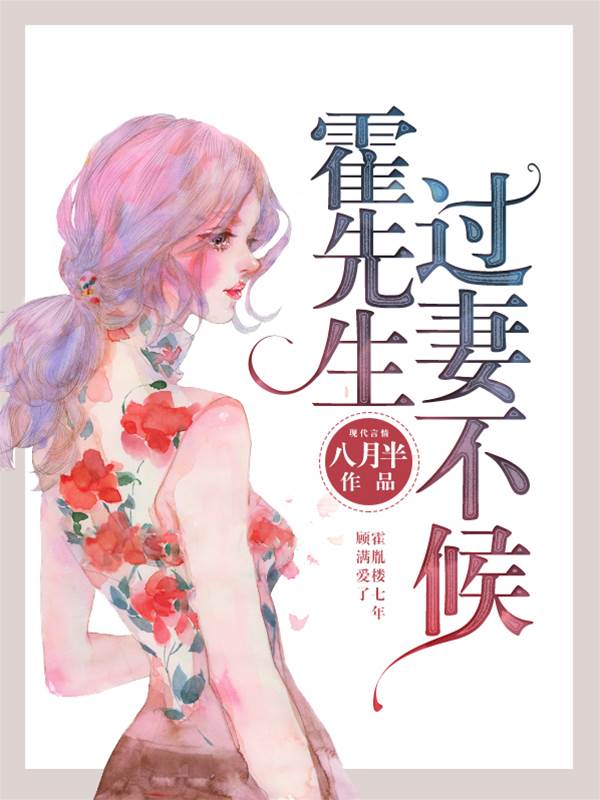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