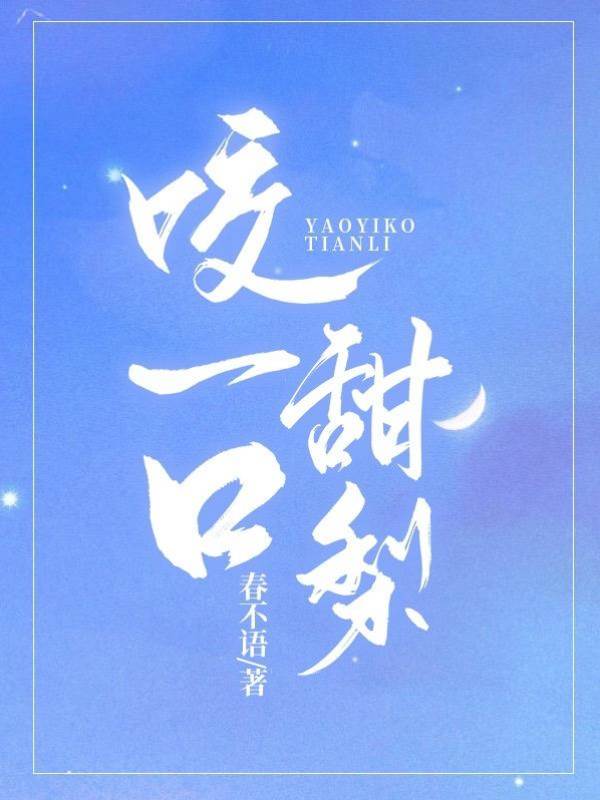《第一名媛,總裁的頭號新妻》 番深727米:或者準確的說,她是被強迫的靠在了他的懷里
<=""></> “忘了。”
把巾洗干凈晾好,率先走出浴室,同時扔下兩個字,“出來。”
忙活了半個多小時,搖著腦袋活筋骨,“床上躺著。”
一邊說一邊從上拿出手機,撥通顧南城的電話,“醫生有嗎?上來,再兩個人上來收拾下房間,弄得七八糟的。”
掛了電話不出兩分鐘,醫生跟保鏢都上來了償。
盛綰綰站在門口朝他們淡淡的吩咐,“理他的傷口,把房間收拾干凈<="l">。”
“好的,盛小姐。”攖
“顧公子跟晚安還在樓下嗎?”
“還在。”
“你們弄吧,我下去。”
說完就走了出去。
薄錦墨原本是靠在床頭,見出門菲薄的立即抿起,俊的廓冷而凜冽,眼神極其的暗淡,又似乎在克制著什麼。
顧南城跟晚安都在客廳的沙發里坐著。
晚安靠在男人的上,一個呵欠一個呵欠的打著。
顧南城低頭看著困倦的人,無奈的低聲道,“我讓人送你回去,嗯?”
晚安抱著他的手臂,咕噥著怨般的道,“你好吵,讓我睡會兒。”
顧南城,“……”
樓梯上響起腳步上,兩人一起看了過去。
盛綰綰走了過來,疲倦的倒在了沙發上,“晚安困了,你帶回去吧。”
顧南城挑眉,“你一個人搞的定?”
還沒說話,剛上去沒一會兒的醫生就小跑著下來了,盛綰綰斜眼看了過去,淡淡的問,“怎麼回事兒?”
醫生看了看顧南城,又看了看盛綰綰,苦著臉尤其無奈的道,“薄總不讓我替他上藥包扎……”
“他又怎麼了?”
Advertisement
“薄總讓我們都滾。”
盛綰綰看向顧南城。
顧公子冷冷嗤笑,“上去吧,他怕你走了。”
他已經沒什麼好脾氣了。
“行了,你們回去吧,耽誤了半個晚上了。”
晚安也問道,“綰綰,你一個人能行嗎?”
盛綰綰已經從沙發上爬了起來,睨著顧南城,“不然,繼續用鏈子把他捆起來?”
顧公子眼角上挑,似笑非笑,“你這是在怪罪我,不應該給他用手銬跟鐵鏈?”
撇撇,沒答話。
顧南城圈著晚安的腰站起來,依然是似笑非笑,“你要是真心疼的話,遷怒我我是也無所謂,只不過你也應該清楚有些事不是我能左右的,嗯?”
兩人攜手離開。
盛綰綰面無表,帶著醫生回到臥室。
保鏢也被他轟了出來,正站在門外,等“救兵”。
走進去一眼就看到冷沁著一張俊臉的男人,徑直走到床邊,眼神從他的上掃過,語氣不善,“薄錦墨,你在鬧什麼?”
男人抬頭看著,眼神晦暗到極致,也深沉復雜到極致,薄抿一條直線<="l">。
他看著,半響才低聲道,“你陪我會兒。”
那姿態,頗有些低聲下氣的味道。
盛綰綰看著,抬腳走到沙發上,兀自的坐了下來,話是對醫生跟保鏢說的,“快點吧,很晚了。”
不是很晚了,是一直都很晚。
醫生再度過去,這次男人不聲不響,沒開口讓他滾。
半個小時后,醫生跟保鏢道,“薄總,盛小姐,那我們先走了,有什麼想要再通知我們。”
“嗯。”?兩人像是松了一口氣一般,然后很快的走了。
安靜的夜里,安靜的臥室。
Advertisement
盛綰綰嗓音如昔,自然而尋常,“收拾完了,你睡吧,我走了。”
說完也不看他,徑直就往門口的方向走去。
原本聽到腳步聲時是準備停下來的,但還沒等轉過,開著的門就被一只手臂率先了過來,砰的一聲要關上。
然后整個人都被翻轉了過來,肩膀被男人按下去,抵在后的門板上。
抬起頭,看到他鷙的俊臉,面容沉如水,“盛綰綰,”他死死的盯著的臉,薄上泛出郁的嘲笑,“你是不是覺自己特別的善良?”
的背脊在門板上,仰著臉看他,歪著腦袋笑著,“善良不善良我不知道,但是難道,我得罪你了?”
男人的軀了上去,薄吻上的耳蝸,一字一頓的道,“不準走,”溫熱的氣息全都灑在的耳朵上,戰栗從皮一直延到了每一神經,他幾乎是咬著每一個字道,“盛綰綰,你說不理我就不理我,說不讓我見你,就不準我見你,憑什麼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憑什麼,嗯?”
他說著說著,仿佛越說越怒,越說越無法控制,到最后甚至輕輕地咬了一口。
舌一上的跟氣息,整個腦海中的理智就像是自失控了一般,他吻著的耳朵,然后沿著耳后一路的往下吻去,異常激烈的,熱烈的親吻著的下,脖頸,甚至繼續往下。
盛綰綰微微的懵了懵,連忙手忙腳的去推他,“薄錦墨。”
或許是他之前寧愿以這樣離譜的方式遵守諾言,或者是他剛才表現得太聽話,無害,所以沒想到會突然變得這麼,強勢。?捶打這他的肩膀,“薄錦墨,你干什麼……唔。”
Advertisement
睜大眼睛,眼睜睜的看著男人俊的臉了下來。
這一刻甚至荒唐得沒有了什麼別的覺,只覺得男人那點看上去甚至都看不太大的清渣,刺得清晰的覺得疼。
薄錦墨親吻著,腦子里已經沒有了別的任何的想法,像是完全沉浸在這樣的親吻當中了,也覺不到的掙扎跟推搡,兀自的沉迷其中<="l">。
他一開始并沒有想這麼做。
只是看要走,就不控制的跟著下來了。
然也只是想說幾句話,結果不小心上的耳朵,被氣息蠱,又親咬了下去。
于是,被蠱得更深了,直接吻了下去。
最近睡前他都習慣吃藥,南城說他藥吃的太多影響了神經,變得喜怒無常脾氣更大,變得越來越無法控制緒,他以前沒覺得,因為他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只是放一縱的尺度比從前大。
但他把按在懷里的時候,他想,大概真的是這樣。
他連對一個人的慾都無法自持。
盛綰綰被他吻得昏昏沉沉的,等再找回一點神思判斷力的時候,已經被男人扔到了床上,在下肆無忌憚的親吻。
的手被他舉到頭頂,唯一能到的就是他麻麻的吻著的腮幫的耳后,馬蚤著敏麻痹的耳后神經,一遍一遍的道,“綰綰,你不準我見我,我每天都很想你,”
那聲音大概沙啞得只有能聽到,又低又模糊,“我想你,有時候覺得你很可惡,想把你捉起來挫一頓一頓,可我還是很想你,你不來我也沒沒什麼熬不過去的,你為什麼要來?”
盛綰綰幾乎覺不到他在的服,于是就這樣被了。
他重重的親吻著,沙啞著嗓音喃喃的道,“好難,真的很難,你給我,好不好?”
在上的男人仿佛發燒了一般,溫度極高,連帶出的氣息都是異常的滾燙,要將灼傷。
盛綰綰咬著,直到這樣的作也承不住的沖擊,最后只能死死的咬在男人的肩膀上,大腦空白,渾弱。
…………
只覺得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適應這個男人對的話的哭喊視若罔聞的況了,所有的心緒里混合著委屈的,咬牙切齒的,以及另外一種酸的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緒。
過于頻繁和強烈的沖擊如水般將淹沒,到天際泛白時,甚至有種自己從頭到腳從里到外都不被自我支配的恍惚。
不像累倦到極致就沉沉的睡了過去,薄錦墨抱著的甚至是汗津津的子小睡了極短的一段時間,一照進來,他就驀然的清醒了過來。
思維很緩慢,緩慢地一時間分不清清楚是現實還是夢境。
懷里是異常溫的存在,他怔了怔,下意識的低頭。
人黑的發落在枕頭上,偶爾有幾在了臉上,瘦削的瓜子臉上還是未褪的紅,在這個早晨,得能擰出水。
是靠在了他的懷里睡的,或者準確的說,是被強迫的靠在了他的懷里。
---題外話---600+明天加更<=""><=""><="">
猜你喜歡
-
完結816 章
隱婚甜妻拐回家
爲了挽救家族利益,簡小單眼一閉就嫁給了地產大亨霍景擎.這剛一嫁人老公就出國了.只要掛個少夫人名頭,不用張腿不用受累,輕輕鬆鬆拯救了家族集團,簡小單真是睡著都能笑醒.怎料,四年婚約馬上到期,老公卻回來了!他不是對女人不感興趣嗎?這每次見到她都像餓狼撲食是什麼鬼!每次都腿軟,還要各種配合.媽的,這……
146萬字8 314307 -
完結326 章

貼身甜寵
七年後,她帶著一個腹黑可愛的寶寶,再次遇上了那個叫洛堯擢的男人,她都不知道爲何,就招惹了這個男人…
83.3萬字8.18 61248 -
完結541 章
南風若知意
跟了顧南風三年,周圍的人都說宋知意和顧南風是頂般配的一對,說的人多了,就連宋知意都當了真。 可是後來呀,宋知意才知道,人啊,貴在有自知之明,她沒有,所以她輸得一塌糊塗。
98.2萬字8 36807 -
完結1119 章

震驚,前夫帶三胞胎空降搶婚現場
兩年婚姻,一朝難產,夏寧夕躺在血泊中,卻忘了今天是他和別人的婚禮。霍南蕭說:“孩子留下,我們離婚。”他要的,只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剛出世的嬰兒竟要認別的女人做母親!夏寧夕如愿死在手術臺上,不料肚子里還有兩個未出世的寶寶!再次相遇,他如獲珍寶,可她已為人妻,還生了兩個孩子,霍南蕭發瘋闖入她的婚禮現場……“霍南蕭,我已經死過一次了,這一次我只要你的命。”夏寧夕親手毀掉他的摯愛,卻不知,那年她過世的噩耗傳出,霍南蕭一夜封了心,他紅著雙眼守了一千多個日夜,痛不欲生,只為再見她一面……
217.7萬字8.46 244024 -
完結770 章

懷孕後:那晚的事瞞不住了
公司聚餐,喝醉了的江笙陰差陽錯進了上司的房間……傳聞厲廷衍不近女色,殺伐果決,凡是招惹上他的女人都沒有好下場。一個月後,江笙看著孕檢單,腦子裏第一個念頭就是:跑!她跑他追,她插翅難飛!
84.9萬字8 69244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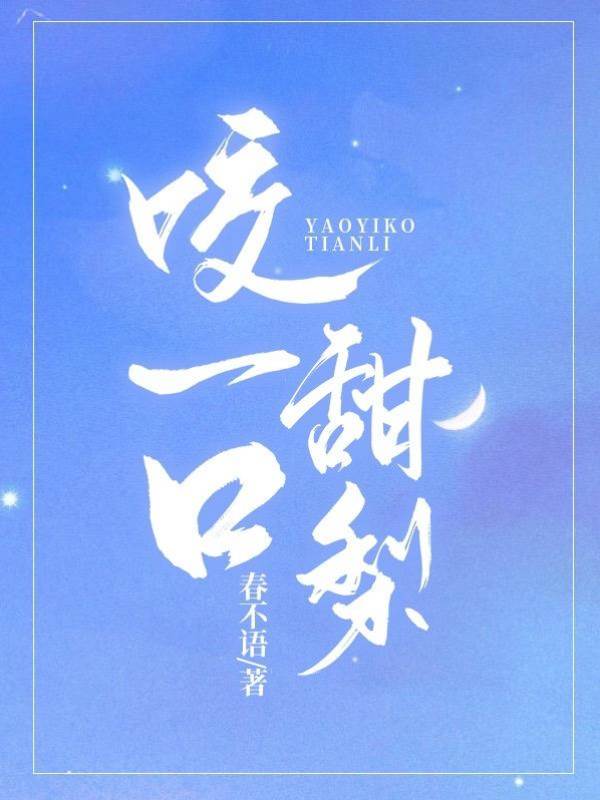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83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