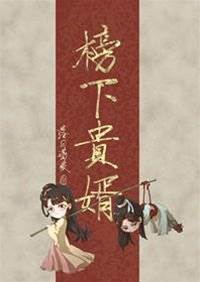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許你山河萬里》 第102章
拍賣師很熱的煽了全場的氣氛,那些富商,還有太太們,起價格來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不一會,這手鐲的價格就水漲船高起來。
徐啟凡倒是沉得住氣,直到價格高到離譜,沒人再往下哄抬時,他才最后一個舉牌,給了一個所有人都塵莫及的價格。全場的眼都簌簌下他,不可思議。
劉月也看向他“你瘋了?”本不值這個價錢。
“沒瘋,我愿意給這個價。”
有錢任,劉月忍不住白了他兩眼。怎麼會不知道,這個價格的數字,正好是的生日的日期的數字。這麼一個藏品,賣出這個價格,想必是收藏界的一大奇跡了。
拍賣師興的音量加大了好幾倍,例行公事詢問最后一遍,無人再舉牌后,他正準備敲下錘子,一錘定音,結果,忽然從門口進來一人,大聲道“這個手鐲我不賣。”
這一聲,讓所有人都朝門口看去,想看看是誰,這手鐲不是剛才那位太太的嗎?此時卻見那位太太在見到來人之后,低下了頭,朝大家道歉“我只是寧士的委托人,這個藏品是的,不是我的。”
原來是寧安容,徐啟凡皺起了眉頭,正準備起朝而去,卻被一旁的劉月拉住,示意他不要引起更大的混。
寧安容倒是很從容的直接走到拍賣桌上,拿起旁邊的話筒,對全場說“對不起各位,這件手鐲,我可以賣給任何人,但絕不會賣給。”
一手直指劉月,目含恨,帶著挑釁。
全場轟然,都看著劉月在竊竊私語。
然而劉月毫不為所,亦是目無懼的向。
寧安容看到的樣子,握著話筒的手像是要把話筒碎似的用力,因為看到劉月眼中對的憐憫。
Advertisement
竟然敢憐憫?
寧安容的怒火已沖刺著所有的思緒。從離婚之后,沒有一天是過的好,的憤怒,的不甘,幾乎要將毀了,所以今天才委托了友人幫忙帶了這手鐲來,目的就是當眾想辱劉月。
但劉月卻能如此坦看著,讓這段日子強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怒火也越燃越旺盛。
徐啟凡站了起來,一眼也沒看寧安容,而是無的對旁邊的安保人員怒斥到“誰允許無關的人員進來?馬上帶出去。”
這一句呵斥,是他對劉月的立場,也是他對寧安容的立場。
寧安容站在臺上,眼眶當即就紅了,大聲喊道“徐啟凡,我們夫妻這麼多年,你不能這麼對我。”
安保人員已上臺,想請下去,但是按著桌子不肯走。安保人員一時也沒轍,這寧安容亦是有頭有臉的人,他們實在下不去手來強的。
徐啟凡聽到的話,神更加的難看,他們的婚姻本就是建立在合作基礎之上,甚至最初結婚時,彼此也都心知肚明不一定能夠走完一輩子,如今分道揚鑣,也算是預料之中的事。并且,他未曾虧待過,離婚時,他把能給的全給了,足夠過上幾輩子食無憂的生活。
他也給足了面子,從未跟任何人講過他們曾經的婚姻是怎麼回事。但今天,這樣來鬧,過去的那點分,完全沒有一一毫了。
寧安容看著徐啟凡那冰涼的眼神,的心如被尖刀剮過。即使最初他們結合是各有目的,但夫妻這麼多年,他不,但是他啊。
既然已是這樣,索破罐子破摔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所以再次把所有矛頭指向了劉月。
Advertisement
“大家看看,就是這個人,從上大學時,就被所謂的師父包養著,教手藝,供讀書。后來因認識了徐啟凡,便把年歲已高的師父甩了跟徐啟凡在一起。那時,還是只是一個大學生,這麼多年,介我跟徐啟凡的婚姻這麼多年。”
說完,又忽然看向徐啟凡,厲聲問道“徐啟凡,你睜大你的眼睛看看這個人,當初為了你拋棄了一心栽培的師父,你敢保證,將來不會為了另外一個比你更有錢,更有權的男人拋棄你嗎?”
徐啟凡的臉已經鐵青,再看劉月的神,已沒有剛才的淡定。
只見忽然站了起來,朝臺上的寧安容走去,渾充滿了戾氣,是徐啟凡未曾見過的樣子,表亦是沉的嚇人。
直直走到寧安容的面前,在所有人沒有反應過來時,抬起一手,狠狠朝寧安容的臉煽去。
寧安容的臉,頓時五個鮮紅的手掌印,本能的出手要還手,但是劉月又早了一步,扼制住了的手腕,使得本彈不得。
只聽劉月說到“向我師父道歉。”
的聲音與的表都是狠戾的,完全不是平日的樣子。寧安容似有些被震懾住,呆滯的看著劉月。
“馬上向我師父道歉。”
在劉月的心中,周明的父親,也就是師父,是最尊重的人,甚至對他的不比自己的父親。師父是把帶出水深火熱的人,是給技藝,悉心栽培的人,是給了另外一番生活的人,怎能允許任何人去玷污他?
寧安容不知道劉月哪來這麼大的力氣,扼制著的手腕,像是鉗子,痛的額頭已滲出汗來。
“道歉。”
Advertisement
整個會場被現在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震撼的一片肅靜,所謂看熱鬧不嫌事大,沒有人上去阻止,都是靜悄悄的看著兩個人的斗爭。
大家心中都嘆,這麼看來,寧安容完全不是劉月的對手,難怪落得這樣的下場了。
場下一片安靜,場上亦是劍拔弩張。
寧安容從小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哪曾過這份委屈,被劉月拽著手腕彈不得,手痛,心更痛,卻也倔強的不肯開口說一個對不起。
直到臺下的徐啟凡走上了臺,擁過劉月,勸放手之后,劉月才放手。
徐啟凡朝寧安容到“跟道歉,還有師父。”
他的聲音亦是冰涼的,不容置疑的。寧安容看他這樣,眼淚瞬間飆了出來,不得不低頭說到“對不起。”
這一聲對不起,的一切都輸了。轉倉惶準備離開這個拍賣會現場,卻被那位自己委托來拍賣手鐲的太太給住“寧士,這手鐲如何理?”
寧安容聽到這話,原本向外走的腳步頓了下來,回頭看了看徐啟凡,看了看劉月,已冷靜下來“有錢為何不賺?賣了。”
這個人,也是冷之人,了那麼大委屈與傷害,竟能在如此短時間調整過來。若不是剛才出口辱了的師父,劉月都要佩服了。
最終是按照徐啟凡最初的價格拍賣下了那個手鐲,回家的車上時,徐啟凡便親手給劉月戴上。戴好后,執起的手,落下一吻,喃喃道“劉月,對不起。”
車氣氛很沉悶,之后兩人都不怎麼說話,更沒有毫得到這個鐲子的喜悅。
徐啟凡安心開車,劉月靜心觀察這手鐲。
忽聽耳邊有人喊“阿兮,阿兮,明日在城郊見,你要早些起來,不許睡懶覺。”
是寅肅在。
劉月拼命瞪大了眼睛,看著眼前劍眉星目的年,不是寅肅是誰?
又回到了通朝?而且回到了寅肅還是三皇子時的通朝?
“阿兮,發什麼愣呢?剛才跟你說的話,聽到了嗎?”
真的回來了?真的回來了?連問了自己兩聲,然后興的驚著撲向了年寅肅的懷里。
的作很大,整個甄府的下人都看見了,抿著的樂。而寅肅的臉已有些紅,把拼命像八爪魚似的纏著他的六兮從他上掰了下來。
輕輕著的鼻子道“知不知?”
而六兮就只是看著他傻笑,笑的簡直像是個白癡,甜甜說到“我知道了,明天一定比你早起,你現在快回宮去,免得落人口舌。”
寅肅這才騎馬離開。
第二日,是艷高照。向來睡懶覺的六兮竟然破天荒的起的比都早,一個人跑到馬廄去牽了一批馬直奔城郊。以前都是寅肅等,這次,換等他一次,只是,當剛城門,便看到了寅肅竟然比還早等在城門外。
看著的眼神十分妖孽與得意,這就是年的寅肅啊,雖然,但在面前還是的。
當兩人騎得馬并行時,他長手一,就把六兮從的馬上抱到了自己的馬上。
六兮早已習慣了這種作,但還是假裝害怕的驚,然后順勢撲進他懷里,摟著他的腰,樂此不疲。
“手出來。”
寅肅命令,六兮乖乖出手“做什麼?”
寅肅沒說話,而是直接在手上套上了一個手鐲。
“騎馬時帶上,保護你手腕。”
“哦。阿肅,我們去哪?”
“去摘野果子。”
“什麼?我沒聽錯吧?堂堂三皇子,去摘野果子?”
“宮里醫說的,用來釀酒,每天喝點,可以治你頭疼的病。”
他說的云淡風輕,六兮卻的一塌糊涂,腦袋埋在他的前蹭“阿肅,阿肅。”他名字。
“嗯?”
“我好你。”說完,赧的把腦袋埋在他的懷里,更加的不敢看他,但是表達的卻是最真實的心意。
寅肅渾一僵,放慢了騎馬的速度,霸道的抬起的頭,霸道的落下了一個深而纏綿的吻。
“劉月,到家了。”
“劉月?”
是誰,是誰在?是徐啟凡。
“睡著做夢了?”
劉月看著眼前替松安全帶的徐啟凡,時錯之中,才發現剛才那些好只是夢,可那麼的真實,就是上一世年時的記憶啊,不是夢的。
徐啟凡手在面前擺了擺,聲問道“不想回家?”
這一問,劉月終于回神,看著這輛寬敞的車,不是馬,窗外是高樓林立,不是那城郊外,徹底清醒,然后認清這個事實。
還有伴隨著的是心里撕裂的疼痛,痛的彎下了腰,整個人都蜷著。
“怎麼了,哪里不舒服嗎?”徐啟凡焦急的問。
捂著口,連都發白“徐啟凡,我好想他。我真的好想他,怎麼辦。”
“誰?”
“阿肅,我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227 章

太子妃她命中帶煞
冇人告訴謝橋,胎穿後勁這麼大,竟然成個病秧子。 好在親和力MAX,養的動物能打架,她種的藥草都成活。 進能製符看相、砍桃花;算命望氣,看風水。 退可琴棋書畫、雕刻、下廚、賺到銀子白花花。 竟還被太子拐回了家。 “聽聞太子妃自幼克親、命中帶煞,是個短命鬼,與太子成親,冇準都要性命不保,很快就要兩腿一蹬玩完啦!”京城秘聞。 N年後。 “皇太祖父、太祖母,今日又有人偷偷賭你們昇天了冇?!”
112.1萬字8 61695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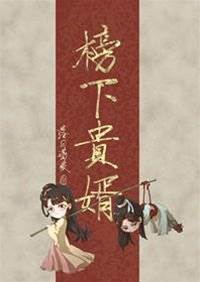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391 -
完結852 章

穿越之繼妻不好當
蘇惜竹因為地府工作人員馬虎大意帶著記憶穿越到安南侯府三小姐身上。本以為是躺贏,可惜出嫁前內有姐妹為了自身利益爭奪,外有各家貴女爭鋒,好在蘇惜竹聰明,活的很滋潤。可惜到了婚嫁的年紀卻因為各方面的算計被嫁給自己堂姐夫做繼室,從侯府嫡女到公府繼室…
229.6萬字8 265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