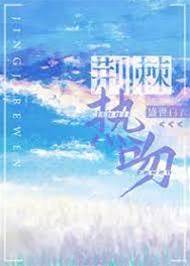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無愛承歡》 第305章 怎麼還會疼
很亮,白茫茫的線有些刺目,那是地上積雪的折。
很暗,一道又一道的黑鐵塊阻擋在我面前,眼前的一切被劃分四分五裂,連那個人完整的臉都看不到。
很痛,渾上下沒有一不在疼痛,僵的四肢,被的手掌,還有漸漸在流逝的肚子,甚至是里的五髒六腑,都扭曲一般的疼痛著。倒是心口上,並不疼,而是空了。
好累,全的力量都在流逝,連心跳也覺不到了,撐不住沉重的眼皮,沉沉的往下墜-落。
最後的視線模糊見,我約約的聽到許多雜無章的聲音,卻不知道他們是在干什麼,好像拉扯的什麼人,正一點一點的在我眼前遠去,卻一樣不知道是誰。
心空了,連腦海也跟著一起空了。
我像是一個疲累至極的旅人,只想快點閉上眼楮,好好的睡一覺。
睡一覺……等我睡醒了,一切就能恢復正常了。
“一月!不要睡!一月!睜開眼楮看看我!”一個男人的聲音打破我耳邊的嘈雜,突然的傳耳朵里。
那聲音模糊的讓人聽不出他是誰。
我想搖頭,可是脖子好重,我沒有力氣,一也不了。
我想回答,但是張了張,也沒有力氣再發出聲音。
唯有摟著肚子的手指,在這個時候輕輕的抖了下,像是在肚皮下面的孩子……
Advertisement
我累了……我要睡了……
孩子……跟著媽媽一起睡吧……
在最後失卻意識的那一刻,我覺得好暖,就像是裹著被子曬太的貓,到都是暖洋洋的。
***
砰的一聲巨響,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紅的火焰快速的將車輛席卷。
“你不要命了啊!車子炸了,快點後退!”一個男人用力的拉住另外一個了傷、還力往前撲過去的男人。
傷的男人渾繃著的發出一力量,刷開拉扯著他的手臂,哀吼著,“我的妻子和孩子還在里面,我必須去救!”
***
七天。
時間過了七天,對有些人而言,只是普通又平凡的一周;對有些人而言,卻是度日如年的折磨;對我而言,只是睡了一覺,做了一場夢。
睡醒之時,我依舊躺在一片白茫茫之中,依舊僵又疼痛,一也不了,只能從微微睜開的眼楮里,稍稍看了一眼,只覺得有人影浮,但是雙眼依舊沉重,只能無奈的落下。
消失了亮之後,我墜在黑暗中。
之前的那七天,我似乎已經習慣了那樣的黑暗,沒有任何心慌的覺,反而格外覺得平靜。
靜心之余,我發現自己雖然無力睜開眼楮,但是意識確實清楚的,還有其他的覺。
我能覺到有好幾個人在我的病床邊來來回回走,他們時不時的踫我的,好像是在確認什麼況;
Advertisement
我也能聽到周遭的聲音,有人尖,似乎很興;有人哭泣,似乎很傷心,還有一個男人,不斷的著我的名字。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睜開眼楮看看我……”
他的聲音或低沉,或放大……從激張,到疑問彷徨,到最後……變了哀怨的懇求……
在那一刻,我的腦海里漸漸地只存在一個問題。
這個男人是誰,我和他是什麼關系?
我的意識像是一團棉絮一樣,綿綿的,糟糟的,理不出思緒,想不出答案。
但是那個男人的每一次呼喚,每一次的轉變,都像是一個鉤子,輕輕地拉扯著我的心口,隨著他的聲音一下一下的痛著。
疼……
心都空了,又怎麼還會疼?
突然地,腦海中飄過這樣一句話,像是來自我心底的最深,卻將我一下子僵住了,連同意識也像是突然死機的電腦,陷在黑屏中,再一次的沉睡。
***
三天後,江城滿地的積雪已經消失無蹤,寒冷的北風也不再呼嘯,甚至還有暖從雲層總灑落下來,讓經歷了一場暴雪的人覺到冬日的溫暖。
我就在這樣的日子里第二次清醒過來,看到燦黃的線過玻璃窗灑進來,落在地板上,也落在趴睡在病床邊的陸斯年上,慢慢勾勒著男人憔悴的臉盤,胡渣布的下,浮腫的眼下,還有一睜一睜的雙眼。
Advertisement
他睡得並不安穩,好像隨時都會醒過來。
這樣的想法不過剛剛浮現,陸斯年像是被凍到了一樣突然打了一個哆嗦,然後快速抬起頭來。
跟他臉上的疲憊一樣,他的雙眼里也全是猩紅的,當眸子對上我睜開的眼楮時,陸斯年僵在了原地,一時間竟然沒有任何反應。
我靜靜地看著他,大約五六秒鐘後,他猛地向我撲過來,但是在即將踫到我的之時,突然的又停住了。
寬闊的雙臂依舊張開著,用最緩慢的作,最輕的力量,“抱”住了我,“環”在我的頸側。
“一月,你終于醒了,終于醒了……”陸斯年俯埋首在我的頸側,聲音沙啞又哽咽著。
我的沒有多力氣,別說是推開他了,連彈都彈不得,只能任由他這樣抱著。
細微間,我覺到陸斯年的胡渣踫到了我的臉頰,清楚的傳來細細麻麻的,立刻皺了皺眉。
等陸斯年終于“抱”夠了之後,他松開了手,抬著比剛才更加通紅的眼楮看著我,說道,“一月,你昏迷了十天了,我真的好怕你這樣一直睡下去,再也醒不過來。”
看著他眼神里閃耀的興,我不為所,只是平靜地對視著,目清冷如冬日的氣溫。
“一月,你的在車禍里到了重創,現在還在恢復期,暫時不能。有哪里不舒服嗎?你告訴我,我馬上讓醫生過來。”陸斯年急切的關心道。
我在這是才了眸子,張想說話,“呃……”,發出的聲音嘶啞干裂。
陸斯年皺著眉,臉上盡是心疼和不舍,解釋道,“你吸了過量的濃煙,灼傷了嗓子,暫時還不能說話。”
怪不得……我連嚨也疼的厲害。
全都快支離破碎了,嚨的這點小傷似乎不算什麼,我很快接了現狀。
沒說出口的話,只能用眼神示意。
我的目往下,從口到腰腹,最後停在……肚子上。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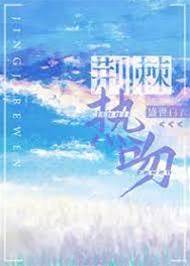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1718 章

頂級婚寵:總裁高調寵妻
同父異母的姐姐不想嫁給傳聞中又醜又不能人道的未婚夫,親生母親下跪求她:“你姐姐值得更好的,你幫幫她吧。”她心寒似鐵,代替姐姐出嫁。新婚之夜,英俊的男人皺眉看她:“太醜了。”她以為兩人從此會相敬如冰,卻不料,他直接將她壓倒:“再醜也是我的女人。”她瞠目看他:“你、你不是不能……”男人剝下她層層的偽裝,看著她本來漂亮的麵容,邪笑道:“看來我們對彼此都有誤解。”
226.3萬字8 105257 -
完結971 章

為她破戒!嗜血傅爺輕聲哄她吻她
【雙潔】【甜寵】【雙向救贖】 前世,時晚慘死。 傅霆琛為之殉情,葬身火海。 重生歸來,時晚占盡先機。 她步步為營,發誓要保護好自己的最愛。 傅霆琛偏執成性,暴戾殘戮。 卻不知道他在婚後,對一個女人嬌寵無度,溫柔繾綣。 “阿琛,打你為什麼不躲開?” 傅霆琛俯身吻著她的手指,猶如虔誠的信徒。 “手疼不疼?”
109.3萬字8.18 1072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