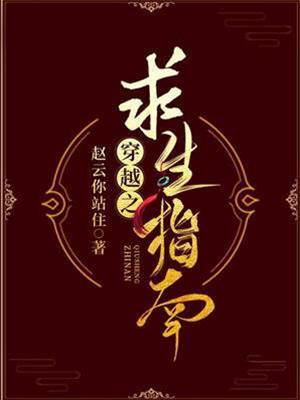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鸣蝉》 第5章 承露囊
謝大爺臉上撐起一疲憊的笑:“大郎好些了。”
謝蟬眉眼彎彎,從袖子里拽出一只圓形承囊,“大伯,我送給大哥哥的,這個可以香屋子。”
給堂兄弟姐妹都準備了見面禮,承囊是周氏和周舅母做的,里面的干桂花是親手裝的。
上輩子謝嘉瑯一生樸素,謝蟬特意挑了個樣式大方、素凈的,準備送給他。
昨天沒機會送出去,知道今天謝大爺會來老夫人這里回話,特意等在這里。
謝大爺揣著承囊回到自己的院子,心里百味雜陳。
就在剛才,他去見老夫人,告知謝嘉瑯吃了藥,已經好了。
老夫人臉上沒有喜,悠悠地嘆口氣,道:“老大,我已經吩咐下去了,你院子里那幾個伺候的姨娘,以后不用服藥了。”
謝大爺呆了片刻:“再等等罷……”
老夫人搖頭:“老大,你年紀不小了,總得有個子嗣。”
子嗣兩個字,太過沉重,把謝大爺所有反對的話堵了回去。
謝嘉瑯天生癔病,猶如廢疾,鄭氏不愿再與謝大爺同房,怕又生出一個怪胎。
謝大爺不想放棄長子,這幾年東奔西走,想治好兒子,可是勞而無功。
老夫人搭下眼皮:“老大,不是我這個做娘的偏心,你被大郎拖累,顧東不顧西,阿鄭呢,天天哭喪著臉,不理家事,家里家外,只能讓老二媳婦和老二照管……你以后是什麼打算?”
謝大爺沉默。
老夫人長嘆一聲,語重心長地道:“大郎是個廢人,不中用,阿鄭不想生,就讓那幾個姨娘生,生下來過繼到阿鄭名下,大房后繼有人,以后大郎也有親兄弟依靠扶持。”
謝大爺不說話。
老夫人板起面孔:“這幾年外面風言風語,說謝家大房養了個瘋子,吃生喝生,發狂就咬人……你以為我老了,不愿意彈,外面笑話咱們謝家的話我就聽不見?因為大郎的病,外面的人疑心二郎、三娘他們也娘胎帶病,各房都覺得委屈,怕將來說親被人挑剔,要不是我讓老二媳婦管家,他們對大郎的怨氣往哪里撒?”
Advertisement
謝大爺無言以對,滿心沉痛,“兒子明白,娘用心良苦。”
老夫人靠在枕上,捶了捶腰,放語氣:“老大,大郎有病,要是生在平頭百姓家,不知道有多艱難,說不得父母一狠心,把他扔了……他生在謝家,咱們好吃好喝養著他,讓他一輩子不愁吃穿,是他的造化。”
母親勸告的話在耳邊回,謝大爺腳步沉重。
剛進院,婢端著滿滿一簸箕碎瓷片迎面走過來。
謝大爺皺眉。
婢小聲解釋:“大爺……剛才老夫人院里的齊媽媽來了一趟,娘子把茶碗都摔了。”
謝大爺先去正房。
正房一地狼藉,婢在打掃,大夫人鄭氏坐在窗前垂淚,一看到丈夫,柳眉倒豎,委屈化作怒火:“你我以后怎麼做人!都怨你!大郎才會生下來就帶著怪病!我好好的一個大家千金,下嫁到你們家,為你們家生下長孫,結果賠上了一輩子的名聲。你就這麼對我!”
說著說著,悲從中來。
“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啊!我前世到底造了什麼孽!別人的兒子活蹦跳,只有我的兒子見不得人!”
謝大爺心中更加煩悶,“你小點聲,別讓大郎聽見……”
鄭氏氣息一弱,聲音低,接著抱怨,謝大爺不耐煩地勸。
一墻之隔的東廂房,趴在小幾前對著字帖寫大字的謝嘉瑯起眼簾,眼眸深黑,薄輕抿。
書立在門邊,聽著隔壁傳過來的斷斷續續的哭罵聲,神局促。
謝嘉瑯蒼白的臉上沒有一表,示意書幫他換一支筆。
從他記事以來,謝大爺和鄭氏一直在爭吵,尤其每次他發病后,他們吵得更兇。
幾乎每次起爭執都是因為他。
他已經習慣在夫妻倆互相抱怨指責的爭吵聲中做先生布置的功課。
Advertisement
謝嘉瑯直腰,繼續寫字。
昨天他在家宴上發癲,吃了一副藥,很快清醒,今天可以接著去上學,可鄭氏不許他踏出院子一步。
謝嘉瑯年紀不大,但是從小被謝大爺帶著出門求醫,子早。
他約明白,阿娘嫌他丟人。
謝嘉瑯寫滿兩張竹紙時,門簾一陣晃,謝大爺走進屋,朝兒子笑了笑。
“大郎,想不想去學堂?”
謝嘉瑯搖頭。
謝大爺嘆口氣,他知道兒子想去,只是怕鄭氏生氣才搖頭。
“大郎,你看,這是小九娘團團送給你的,剛才在正院見,問起你。你記得小九娘嗎?是你六叔的兒,之前一直在鄉下養著。”
謝大爺拿出承囊,獻寶似的,塞到謝嘉瑯跟前。
謝嘉瑯不說話,把承囊撥開挪到一邊,繼續寫字。
謝大爺看著兒子出倔強的側臉,心里油煎似的。
當初鄭氏和二房的二夫人郭氏幾乎同時懷孕。那時謝大爺年輕氣盛,常和鄭氏吵。一次夫妻吵架,謝大爺無意間推了鄭氏一把,鄭氏了胎氣,疼了一夜,謝嘉瑯生下來時,只有小小的一團,臉憋得青紫,一點聲息都沒有,好不容易養活了,又常發癔病,天天吃藥。
二郎謝嘉文和三娘謝麗華幾天后出生,一樣的養育,兄妹倆就很生病。
謝大爺很疚,想起老夫人的勸說,心里猶豫不決,紛如麻。
謝嘉瑯完功課,下地,練習大夫教他的一套拳戲。
他比平時多練了兩遍。
大夫教他拳戲時,囑咐他每天堅持練習,可以強健。
那時謝大爺一臉期冀地問:“能不能治好癔病?”
大夫訕笑。
謝嘉瑯明白了。
他的癔病無藥可治。
Advertisement
夜里,謝大爺和鄭氏又吵架了,鄭氏摔完茶碗摔花瓶,仆婦們抱著苦勸。
謝大爺臉上被飛濺的碎片劃出一條口子,抬腳出去,鄭氏看著他的背影,嗚嗚哭了起來。
閉的門窗擋不住人的哭泣聲。
“我造了什麼孽……”
“以后他怎麼見人吶……”
還是翻來覆去的那幾句。
謝嘉瑯躺在枕上,手指攥被角。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謝嘉瑯聞到一若有若無的幽香。
昨晚他好像夢見桂花樹了,夢里有縷縷的甜香縈繞。
他常吃藥,房里只有藥味,哪里來的香?
“房里熏香了?”
書青搖頭,謝嘉瑯不喜歡熏香,婢仆婦從不焚香塊熏屋子。
“郎君,是這個。”
青找到角落里的承囊,“九娘送給郎君的。”
謝嘉瑯想起家宴上見過的九妹妹。
皮雪白,頭發很黑,胖乎乎的,手里捧著碗,一眨不眨地盯著他看了很久。
他發作的時候,抓著木勺子,眼睛瞪得溜圓,滿臉驚恐。
大約是嚇壞了。
“我不喜歡這個味道。”謝嘉瑯走到窗前,支起窗扇,“拿下去收著。”
青應是,拿著承囊去了堆放箱籠的庫房,隨手打開一只落滿灰塵的箱塞進去。
*
六房很僻靜。
周氏不多事,謝六爺無大志,夫妻倆除了去正院晨昏定省,就關起院門過自己的日子。
夫妻倆布置房屋,忙了幾天。
謝寶珠天天過來拉謝蟬去院子玩,給看自己的箱、五爺托人送回來的新鮮玩意。
到底是小孩子,謝寶珠愿意讓謝蟬在自己房里玩那些新巧玩,但是舍不得分一些給謝蟬帶走。
謝六爺聽說,一拍大,“委屈我家團團了!”
周氏也覺得愧疚。
在鄉下時,怕謝六爺拋棄自己,心里七上八下,還得強撐著不在人前怯,以免被人嘲笑,好在有乖巧懂事的兒陪伴,才能捱過來。
來到江州后,周氏初來乍到,怕被人看不起,忙里忙外,卻忽視了乖兒。
第二天,謝六爺買了滿滿一車花布,搜羅來一大箱子奇巧玩。
周氏領著仆婦婢給謝蟬丈量,定好尺寸,馬上手裁新裳、新鞋。
謝蟬每天吃得香,睡得足,長得很快。
周氏舍不得好布料,要仆婦們往大了做,可以多穿些時日。
謝蟬的新裳趕制出來的這天,老夫人告訴周氏,孫的名字取好了,請廟里和尚定的名字。
“蟬。”老夫人笑瞇瞇地說,“和尚起了三個名字,寫在簽子上問菩薩,菩薩定的蟬字。”
老夫人信佛。
“這個字好!”二夫人立刻笑道,說了幾句吉祥話,把兒子謝嘉文拉過去,“二郎,你前幾天是不是學了首蟬的詩?”
謝嘉文誦道:“垂緌飲清,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謝麗華也背了一句:蟬發一聲時,槐花帶兩枝。
今天府里人多,分家出去的親戚隔幾天也回府問安,滿滿一屋子人,口稱贊,夸龍胎功課好,記的詩句多,老夫人膝下長大的,就是不一樣。
二夫人的笑聲一直沒停過。
謝嘉武怕二夫人也要他背詩,轉頭扎進人堆里躲了起來。
謝寶珠扯謝蟬的袖,不滿道:“什麼風頭都要搶!”
謝蟬笑笑。
蟬字好,喜歡自己的名字。
屋里眾眷說著家常,一團和氣,謝大爺在外面正廳和謝二爺、謝六爺一起招待親族,商量生意上的事……
只了大夫人和謝嘉瑯。
大夫人一直推病不出,老夫人聽之任之。
謝嘉瑯也很久沒出現在人前。
不管是謝府的人,還是來做客的親戚,所有人都默契地不提起謝嘉瑯,仿佛謝家的嫡長孫是二郎謝嘉文。
謝蟬看著人群里直腰桿,努力做出一副寵辱不驚狀、還是抑不住驕傲歡喜的謝嘉文,心里暗暗想,假如謝嘉瑯在這里,也會得到這麼多夸贊。
他可是日后榜上有名的一甲進士。
謝嘉瑯博聞強識,記憶力很好,典章制度、律法條文記于心,李恒經常要他隨侍左右,以便隨時咨詢。
那一年的進士,謝嘉瑯的仕途最坎坷。
據說他得罪權貴,家世一般,又沒錢打點疏通,被打發到偏遠地方出任知縣,縣衙窮得只有兩張湊不齊八條的破桌子。
他能從窮鄉僻壤一步步重回京師,得到李恒的倚重,靠的是真才實學。
夜里,謝蟬從謝六爺送給的寶箱里翻出一套文房四寶,捧到謝六爺跟前。
“爹爹,我喜歡。”
謝六爺謝蟬的腦袋,“爹爹再給你買一套?”
謝蟬搖頭,拈起一支筆,在紙上劃拉幾下,“爹爹,我也要學寫字,學背詩。”
謝六爺呆了呆。
“團團想上學?”
兒年紀小,才剛接回家,他沒想過給兒開蒙的事。他才學平庸,周氏不認識字,夫妻倆都覺得兒長大了只要學會看賬本就行。
“團團這是看哥哥姐姐都會寫字,想跟著一起玩,真讓學,肯定哭。”周氏兒鼻子,“學寫字不是鬧著玩,每天要早起,你起得來嗎?”
謝蟬有點苦惱。
不想早起,可是小院不如鄉下好玩,每天吃吃睡睡,難免無聊,想找些閑書解悶,必須先“學會”認字。
謝蟬點頭:“我想學。”
謝六爺抱起謝蟬,蹭的臉:“團團想學就讓學吧,要是不好玩,咱們就不學了啊。”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休夫
挺著六月的身孕盼來回家的丈夫,卻沒想到,丈夫竟然帶著野女人以及野女人肚子裡的野種一起回來了!「這是海棠,我想收她為妾,給她一個名分。」顧靖風手牽著野女人海棠,對著挺著大肚的沈輕舞淺聲開口。話音一落,吃了沈輕舞兩個巴掌,以及一頓的怒罵的顧靖風大怒,厲聲道「沈輕舞,你別太過分,當真以為我不敢休了你。」「好啊,現在就寫休書,我讓大夫開落胎葯。現在不是你要休妻,而是我沈輕舞,要休夫!」
65.8萬字8 77347 -
完結453 章

鳳回鸞
世人皆知太子長安資質愚鈍朝臣們等著他被廢;繼後口蜜腹劍,暗害無數。他原以為,這一生要單槍為營,孤單到白頭不曾想,父皇賜婚,還是裴家嬌女。那日刑場上,裴悅戎裝束發,策馬踏雪而來:“李長安,我來帶你回家!”.自此,不能忘,不願忘。
78.4萬字8 14187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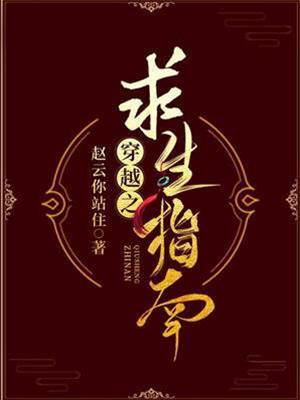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連載1300 章

家侄崇禎,打造大明日不落
魂穿大明,把崇禎皇帝誤認作侄兒,從此化身護侄狂魔!有個叫東林黨的幫派,欺辱我侄兒,侵占我侄兒的家產? 殺了領頭的,滅了這鳥幫派! 一個叫李闖的郵遞員,逼我侄兒上吊? 反了他,看叔父抽他丫的滿地找牙! 通古斯野人殺我侄兒的人,還要奪我侄兒的家業? 侄兒莫怕,叔父幫你滅他們一族! 崇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切都不存在的,朕有皇叔云逍,可只手補天! 李闖:若非妖道云逍,我早已占據大明江山......阿彌陀佛,施主賞點香油錢吧! 皇太極:妖人云逍,屠我族人,我與你不共戴天!
231.8萬字8.18 231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