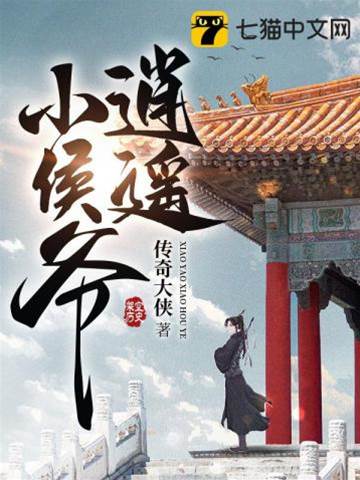《我非癡愚實乃純良》 第49章 臭石頭
羅德元一句話問出來,王笑心中一。
羅德元將他的表盡收眼底,又道:“呵,果然是你。依鄰里所言,一個極俊俏的年,十五六歲,白束發,襟上繡著云雷紋,衽上紋著鶴鹿同春圖。”
王笑這件外只昨天穿了一天,今天便還是穿著,此時被人穿,卻也難以否認。
他只當這案子已經過去,卻沒想到會被人翻起來細查。
羅德元又道:“那鄰里見你推門進了唐氏的院子,他心中好奇,爬到自家屋頂上看,你卻是登堂室,大半天沒有出來。所為何事?”
王珍再次與王珠對一眼,兩人神皆有些不好。
良久。
王笑不知如何回答。
還是裴民反應快,喝道:“羅大人,你要查案就查案,不要問一些無關要的東西!你聽了些長舌婦人的片面之詞,捕風捉影,嚼寡婦門前的是非,還有一個朝庭命的樣子嗎?!”
羅德元道:“這是本案最重要的兩個人證,怎麼會是無關要?王笑,你昨日去找唐氏,孤男寡呆在屋中,到底所為何事?!”
終于,王笑開口道:“我隨的玉佩丟了,過去找,卻沒找到。”
“丟了?還是送出去了?”羅德元目在他腰前一掃,梆梆地道:“現在本認為你二人皆有殺人嫌疑。”
裴民“呵呵”笑了一聲,譏道:“史言雖是靠論事,但查案子卻不同,查案是要講證據的!此案的兇手是木子,這不是誰瞎編出來的,是人證證確鑿,因此巡捕營才定了案。而你懷疑來懷疑去,卻是一點證據也沒有!”
“證據?好!”羅德元道:“我今早在唐氏院中見到一把梯子,極是嶄新,顯然是這幾天新買的。這一把梯子若是架在王家的外墻上,正好可以供王家中的某個人與唐氏幽會……”
Advertisement
全場靜默。
這句話其實很容易反駁。
可王珍、王珠想到自家門房所言的“三爺一瘸一拐地半夜回來”,兄弟倆自然心中明白。
居然讓這個豎儒說對了。
王珠便搖了搖頭。
裴民喝道:“誅心之論!羅大人,注意你的言辭!”
王八蛋,你他娘的是怕事不夠大?這要是讓你坐實了,就是新選的附馬人品有問題,還得牽連到嘉寧伯府、監……
而且還是從老子手上壞了事!
京城中哪一天沒有死上數百人?你這瘋狗非要揪著個連苦主都沒的案子不放,我去你娘的!
思及此及,裴民又看了羅德元一眼,暗道,這瘋狗莫不是就是沖著這個來的?
卻聽羅德元道:“關于此案,本現有第二種推斷。王笑與唐氏存有私,被唐氏的騙子同伙發現,兩人打死了這個同伙,在地上留書,將嫌疑推給連環殺手。唐氏院子的梯子便是佐證,見到二人來往的鄰居便是人證。”
裴民道:“你堂堂史,如何能說這等不負責任的議論。那唐氏難道不能買梯子嗎?便不能是人家為了修屋頂?”
羅德元道:“所以本所說的是‘佐證’而非‘證據’,但若是搜一搜唐氏屋中,或許便能找到王笑所謂‘丟’失的玉佩了……”
王笑眼皮一跳,背后泛起涼意。
王珍與王珠再次對了一眼。
王珍:私或許有,殺人不會。
王珠:那我來吧。
“早聽說史有風聞奏事的特權,今日一見,實在厲害。”王珠便冷笑起來,道:“但,此案羅大人還是先不要太過手的好。”
“本秉公據實,敢論曲直而已。”羅德元又再次抱拳向天拱了拱手,道:“你又是何意?”
Advertisement
“今科進士三百人,京中士子千上萬,死者為何偏偏要盜用羅大人你的名字?”王珠表淡淡的,里卻有些譏諷:“剛才說布店小二見到一個慌張逃走的青年文士,那人有可能是兇手,也或者……羅大人你的模樣便正是‘青年文士’嘛。”
“你休要口噴人!”
“我也只是推測,敢論曲直而已。”王珠淡淡道:“對了,說到機。或許是因為羅大人你被盜用了姓名,心生氣憤,便去找死者報復。”
羅德元道:“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說了這只是推測。此案還是要由裴大人探查才是。”王珠道:“我只是不明白,為何羅大人你要如此急切?一幅咄咄人地想把事栽在別人上的樣子。”
羅德元道:“誅心之論,若是如你所言,我不如就讓太平司以兇手是木子結案……”
王珠打斷他,擺手道:“我只是提供一種可能罷了。案子定下來之前,羅大人與舍弟都只是證人,甚至說有嫌疑。我建議雙方都不要開口,等候裴大人查明真相。”
“裴大人?哼,他若是真有心思要查清楚,本何苦要在這親自……”
“羅大人,水落石出之前,你還是說話為好,以免徒惹嫌疑。”王珠再次打斷他。
羅德元明明說話鏗鏘有力,偏偏王珠語氣如刀,就是能一句話打斷他。
王珠又轉向裴百戶道:“鄙人有些小建議。一是先查明死者分,二是查清楚死者與羅大人之間的關系。比如他為何偏偏要冒充羅大人?對了,還要查清楚……”
王珠說著,頓一了頓,接著微微一笑,道:“……還要查清楚哪個才是真正的——今科進士羅德元。”
Advertisement
一句話耳,羅德元怒發沖冠。
裴民卻是“呲”一聲,譏笑出來。
王珍亦是沉道:“此案確實還有這一種可能,也許死掉的真的是新科登榜的羅德元,有人殺了他,冒名頂替,充作朝庭史……哎呀,是我失語了。”
“荒唐!誅心之論!”羅德元氣得一張臉如豬肝一樣通紅,怒道:“本寒窗苦讀二十七載,憑腹中才學考中的進士,如何來的假?!”
裴民道:“那你怎麼知死者腹中沒有才學?許是你自認有才,卻屢試第,故憤而殺人。”
“荒謬!”羅德元道:“本是不是真的羅德元,一問便知。”
裴民道:“好!我這便派人去羅大人家鄉問一問。”
羅德元一滯,氣得手指直哆嗦。罵道:“這案子一團迷霧,你不將那唐氏捉起來拷問,卻要派人千里迢迢到我家鄉去查,不是拖延敷衍是什麼?”
裴民背過雙手,淡淡道:“等到羅大人份弄清楚之前,我不想回答你。”
“本要彈劾你!”
裴民道:“我不過一個百戶,依規據辦案。怎麼?偏偏查到你頭上時,你便要彈劾我?莫非是心中有鬼?”
羅德元氣急,大罵道:“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們這些商賈、騙賊、番子、勛貴、太監沆瀣一氣,以銀錢為橋梁,以權勢為貨,蒙蔽天家。就是你們這些人,如蛆附骨,將這世道越弄越壞!好,我們走著瞧!”
說著,他起就想走。
‘勛貴、太監’、‘蒙蔽天家’八字耳,裴民與王珠對一眼,心中暗道,果然如此。
這羅德元的狐貍尾算是出來了。
王珍便笑道:“羅大人留步,大家不過是討論案罷了,不要激,不要激。”
王珠亦是道:“兩位大人難得臨,我大哥還備了兩份薄禮相贈。來人,拿上來。”
羅德元本已要拂袖而去,聞言卻是停下腳步。
裴民心中冷笑:“裝作一幅正義凜然的樣子,一聽有禮就挪不腳。呵呵,這些文……”
卻見兩個家仆端著托盤上來,托盤上還蓋著紅布。
沒想到羅德元冷笑道:“好大的膽子,敢當著朝庭史的面,公然行賄。裴大人,你這蟒爪服怕是要下來了。”
王珠似乎有些不耐煩,里“嘖”了一聲。
王珍卻還是帶著溫文爾雅的笑。
羅德元一掀紅布,愣了一下。
卻見兩個托盤上卻都是書。
兩本《東坡詞集》,封面,紙質上乖。
還帶著墨香。
王珍笑道:“此書如今在京城中可有些難覓,這是我自留的兩本。今日兩位大人來,難得言語投機,就送于二位吧。”
贈書雅事,何謂行賄?
“哈。”裴民再次輕笑一聲,斜睨向羅德元,臉上譏諷之意更濃。
“不可能。”羅德元喃喃了一句,拿起案托盤上的書就翻。
“別以為本不知你這里面夾了銀票……”
一本書翻完。
并沒有銀票。
“對,你們只打算行賄這裴民一人。”
他又翻另一本。
依然沒有銀票……
裴民哈哈一笑,譏道:“羅大人莫不是想銀票想瘋了?”
羅德元氣急:“你們在耍我!”
這就很丟臉了。
就像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王珠淡淡道:“今日羅大人來,我教良多,卻有一句話也想與羅大人共勉——世間之事,未必會全如自己心中所揣度,人心有惡,卻未必人人皆惡。我輩行事,先自省,再省世人,此所謂‘君子慎獨’。”
羅德元一張臉紅到脖子。
王珠說完,卻是低頭把玩著茶杯蓋,顯然在送客了。
羅德元也不說話,憤憤而去。
裴民與王珠對一眼,點點頭,亦是離去。
猜你喜歡
-
完結802 章
大明官
大明成化十三年,這是一個宅男漫不經心做著皇帝的年代,這是一個沒有權威的年代,這也是忠奸、正邪、黑白分明的年代.這是國無大患、垂拱而治的年代,這也是法紀鬆弛、官風懶散的年代,當一個現代歷史系碩士高才生來到這個時代附體在一個小帥哥身上,一個個搞笑、傳奇、史詩般的劇情自然就精彩上演了.
179.2萬字8 21927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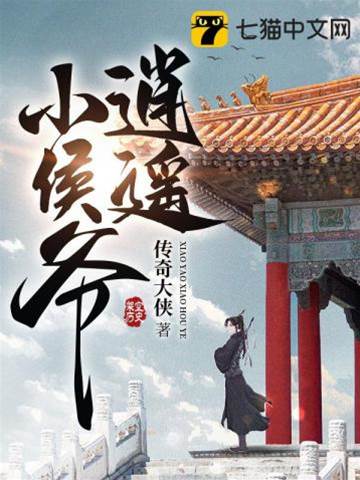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0414 -
完結1082 章
寒門巨子
穿越成家境中落的杯具書生,外有欠債大筆,內有年幼小妹,前世為會計師的李凌想了想:種田是不可能種田的,這輩子都沒加這個天賦點,做上門女婿、給富婆當二爺模樣長得又不上檔次,只就有做生意、考科舉這種事情,才能維持得了生活的樣子。 於是,在這個魚龍混...
259萬字8 307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