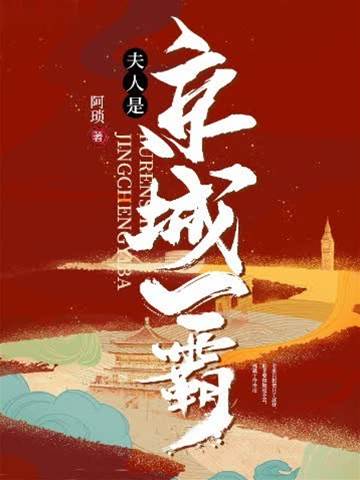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閨寧》 第413章 憤怒
有小潤子在宮中裡應外合,舒硯宮,並不難。
加上肅方帝才下了令要為惠和公主大辦壽辰,宮裡頭也正是忙碌的時候,人來人往,較之尋常更為熱鬧,裝扮廷里的人,尋常不會人注意。舒硯換上了服飾,跟著小潤子一早安置好的人,沿著長巷,目不斜視,緩步往紀桐櫻那去。
近些日子,肅方帝又掛心起了修建那座他夢中高塔十二樓的事來,倒對公主這邊鬆懈了些。
頃,舒硯一行到了永安宮門外,但見廊下整整齊齊的立著一排形高大的侍,個個面無表,令人不由心頭一。難怪若沒有小潤子相助,就連重掌了印的皇貴妃,也沒有法子輕易同紀桐櫻傳遞信息,更不必說親見一面。
然而他們一路行來,宮裡頭的戒備卻並不森嚴。
唯有永安宮外,方才得見這般場景。由此可見,肅方帝即將要宣告天下的那樁婚事,只怕好不了。
他防備著皇貴妃,也防備著居於永安宮的惠和公主。
小潤子先得了印公的信,知舒硯是個要的人,故不敢掉以輕心,此次便特地尋了借口前來親迎,順道從肅方帝那領了來永安宮傳話的活用以遮掩。
至廊下,他不偏不倚地同舒硯打個照眼,微微一頷首,旋即一甩拂塵,道:「都給咱家把腳步放輕些,別驚擾了公主殿下。」
言畢,他使人推開了沉重的宮門,抬起腳領著後端著東西的幾人,漸次。
這是紀桐櫻生辰前的第七天。各家各戶已得了令,待到那日,眾人便需宮赴宴為惠和公主賀壽。於是,這生辰賀禮,自是不得要心打算一番。哪家準備送什麼,都得譴了人去悄悄打探一番,這萬一撞在了一塊,到時未免難堪。
Advertisement
世上稀罕到底是,要不然怎能稀,所以消息一出,滿京都都是各家派出來搜羅賀禮的人。
東城是往來商旅最多之,酒樓茶肆,鱗次櫛比。自外遠道而來的商隊貨,從來也都是直接在東城卸下的。新鮮的東西,轉瞬便都進了東城各的鋪子里,被擺上高高的櫃檯,了招攬客人的最好噱頭。
肅方帝要為惠和公主大辦壽辰的事一出,東城這潭本就不平靜的水,更是被攪得一片混。
來來往往,肩接踵的人們,瞪著眼在周圍尋找合適的東西,氣氛熱鬧異常,堪比上元燈會。
謝姝寧站在二樓的書房裡,倚窗而,遠的長街之上,行人如蟻,在一塊了黑黑的一團。
皺了皺眉,半合了窗扇,轉回來看向坐在書案后的燕淮,輕聲說:「你覺得惠和公主會被指給哪家?」
雖有人手在外走,幫著搜羅信息,但到底不曾親自在朝堂上走過,所知的都只是些零碎皮,當不得真。燕淮卻不同,他是實打實在錦衛里扎過的,何況而今秦南仍在錦衛所里。
所以,心中暫時沒有人選,可保不齊燕淮已猜到了。
問著話,腳下已朝他走了過去,走至近旁,便往書案邊上的椅子上坐下,睜著雙明眸看他。
燕淮仔細思量一番,搖了搖頭:「京都適齡的世家子弟,不過這些,但看此番皇上的做法,一時半會還是人猜不。」
「好在溫慶山已娶妻了。」謝姝寧聽著,愁眉不展,但想到溫慶山做不駙馬了,勉強舒心了些,一不留神低語出口。
燕淮正好聽見,一怔,疑地問:「怎麼突然說起他來?」
謝姝寧這才驚覺自己方才說了,不由微訕,胡道:「若他沒親,豈不是也正是合適的人選?」說完,補了一句,「先前,惠和公主臺選婿,我曾在旁陪同,親眼見過一回他,生得玉樹臨風,是個風.流人,也配得上公主殿下。」
Advertisement
若非當時從中搗,只怕那事已是了。
只可惜,此消彼長,好事多磨,避開了溫慶山,紀桐櫻這一回要嫁的人,似乎也不是個好的。
咬了咬淡紅的瓣,將嘆息聲憋回了肚裡。
燕淮並不知心中所想,只聽得說溫慶山是個風.流人,忍不住眼神微。
夫妻倆這幾日都膩在一塊,謝姝寧對他的小作跟神漸漸瞭若指掌,見狀不由追問:「可是有何不對?」
畢竟燕家跟溫家,也曾訂下過親事,溫慶山對而言,自不比燕淮悉才對。
然而燕淮同溫家長子,也並不稔,只是他恰恰曾當著溫夫人的面揭破過那張畫皮,知道真相而已。
他垂眸,清清嗓子,說:「你昔日在臺所見之人,並非是他。」
謝姝寧大驚,口道:「假的?」
「假的。」燕淮嘩嘩翻著手裡的書,口中解釋著,「真正的溫家大公子,量不過四尺余,何來的玉樹臨風?」
謝姝寧霍然起,小撞在了邦邦的雕花椅上,登時疼得皺了眉頭,手去捂。
「啪嗒」一聲,燕淮手裡的書被他重重丟在了書桌上,隨即他形一躍,翻過了書案到跟前,子一矮,手已按在了的小上,一把將下輕紗管捋上一截,出裡頭玉骨冰。
謝姝寧這一下撞得不輕,雪白的皮子上登時便紅了一塊。
燕淮一面輕輕地上去,一面忍不住斥:「這麼大個人了,也不仔細著些。」
「我是被嚇著了……」謝姝寧不敢呼痛,憋著氣往椅上坐了回去。
一條還擱在燕淮手裡頭,他輕按了兩下,問:「疼不疼?」
謝姝寧覷著他的臉,點一點頭,連忙又道:「倒也不是很疼……」
連劍傷都過,這點疼,緩過氣來,便也就忍得了。
Advertisement
誰知燕淮聞言愈發沒好氣,沉了臉說:「這是沒傷筋骨,要不然可有得疼。」言畢,他抬頭看一看,見面微白,眉宇間含后怕之意,又不由得於心不忍起來,低頭往小上一親,起道:「你坐著別,我下去拿葯。」
謝姝寧連連點頭,一疊聲道好,目送他出門,而後彎腰往紅腫看了兩眼,瞧這樣子,只怕要青上好幾日,不無奈嘆口氣。
片刻后,燕淮捧著只紅木小匣子進來,擱在書案上打開來,取出只青花小瓷瓶。
他蹲在前,細細給傷塗上藥膏,一邊心疼道:「你這上本就容易留下痕跡,這麼大一片,也不知何時才能消。」
謝姝寧聽見這話,不住面上一熱。
前幾日,他在上留下的痕跡,到這會也都還明顯得很。
咳嗽兩聲,輕聲道:「左右沒傷著筋骨,沒大事。」
燕淮在上作輕地著,耳畔聽著近乎呢喃的細語,不由有些心猿意馬起來,忙斂了斂心神。
上清涼,謝姝寧舒了一口氣,遂想起方才未完的談話來,便問:「你方才所言,可是真的?溫慶山量當真才四尺余?」
「嗯,而且他神志並不清明,只怕是生來如此。」燕淮應道。
不但矮,還傻……
謝姝寧憶起前世,紀桐櫻竟真嫁了溫慶山,頓時氣紅了眼睛,「溫家好大的膽子,公主臺選婿,竟也敢弄了個假的去!」
這可是欺君之罪!
說著,想起溫慶山如今可也是娶妻了的,不覺咬牙。
英國公府辦的好一樁齷齪事,這一世雖則已變了,他們最終卻還是為溫慶山娶了妻。
一旦進了狼窩,又有幾個姑娘能願意撕破臉皮昭告天下?
而且溫慶山而且結的這門親,方門第遠差於溫家,自然更是為難。
氣得握拳,世人對子素來刻薄,這事即便最後天下人知道了,眾人不恥溫家之餘,卻也只會看那姑娘的笑話。
同樣為子,又知前世被誆騙的那個是紀桐櫻,心頭便有一難消的怒氣來回盤旋累加。
再想不出,肅方帝為紀桐櫻擇定的那門親事,再差又怎能比溫家的還差。心裡也不知是慶幸還是苦,百般滋味,令人難。
燕淮為上完了葯,直起來,正要將手中瓷瓶放回匣中,卻被忽然一把攔腰抱住。
他一愣,耳邊聽得因為埋首在自己懷中而顯得悶悶的聲音:「你差點也進狼窩了……」
若娶了溫雪蘿,他就了溫家的婿。
燕淮失笑,「英國公倒是個好的,只可惜其夫人……不大樣子……」
連帶著兒子跟兒,也都教得不大好。兒子本是嫌棄的,倒也不在乎,但兒卻是看重的。然而溫雪蘿同,卻是日漸離了心。
*****
時飛逝,惠和公主的壽辰,很快就到了日子。
七天前的清晨,舒硯悄悄了皇城。
同一天午後,燕淮跟紀鋆,在東城一角見了面。
連著幾日,京都的天都不曾徹底晴過,斷斷續續下了好幾天的雷雨。
雨水泛濫,北城石井衚衕的那口子石頭水井,淙淙往外冒著水,差點淹了街。
直到今日,惠和公主的壽誕,這連著了好久的天,才算是真的放了晴,萬里無雲,湛藍似海。
眾人備好了禮,頂著明晃晃的日頭,魚貫往皇城去。
猜你喜歡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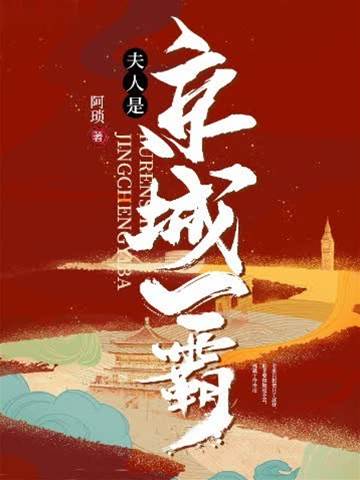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63 章

三生有幸擁你入懷
姐姐,你就在地獄裏看著妹妹我如何飛黃騰達吧哈哈 ”庶妹把她的雙腿扔給了狗,猙獰地大笑著。付出一切,隻為助丈夫登上皇位。誰承想,他竟然聯合她的庶出妹妹殘害她一家!兒女慘死,親妹妹被奸殺,父母被陷害至死。這一切都是拜他們所賜!她不甘心!再次睜眼,她竟然重生!這一世,她定不會放過這對狗男女!虐渣男,鬥庶妹,讓他們嚐嚐什麼叫錐心之痛!隻不過這一世,卻又多了個與她糾纏不休的霸氣王爺!傳言攝政王霸氣腹黑,冷酷殘忍,更是野心勃勃!卻對她包容萬分,護他周全,甚至為了她放棄一切!看女強男強如何強強聯合贏天下!
44.9萬字8 22897 -
完結264 章

嫁皇叔
顧清儀糟心的高光時刻說來就來。未婚夫高調退婚踩著她的臉高抬心上人才女之名不說,還給她倒扣一頂草包美人的帽子在頭上,簡直無恥至極。請了權高位重的皇叔見證兩家退婚事宜,冇想到退婚完畢轉頭皇叔就上門求娶。顧清儀:“啊!!!”定親後,顧清儀“養病”回鶻州老家,皇叔一路護送,惠康閨秀無不羨慕。就顧清儀那草包,如何能得皇叔這般對待!後來,大家發現皇叔的小未婚妻改良糧種大豐收,收留流民增加人口戰力瞬間增強,還會燒瓷器,釀美酒,造兵器,改善攻城器械,錢糧收到手抽筋,助皇叔南征北戰立下大功。人美聰明就不說,張口我家皇叔威武,閉口我家皇叔霸氣,活脫脫甜心小夾餅一個,簡直是閨秀界的新標桿。這特麼是草包?惠康閨秀驚呆了。各路豪強,封地諸侯忍不住羨慕壞了。宋封禹也差點這麼認為。直到某天看見顧清儀指著牆上一排美男畫像:信陵公子溫潤如玉,鐘家七郎英俊瀟灑,郗小郎高大威猛,元朔真的寬肩窄腰黃金比例啊!宋封禹:這他媽全是我死對頭的名字!
67.2萬字8.08 67373 -
完結482 章
魅上龍皇:棄妃,請自重!
一個腹黑冷情的現代女漢子,穿越成爹不疼後娘害的軟妹紙! 遇上霸道冷酷武宣王,隻手遮天、權傾朝野,傳聞說,他睡過的女人比吃過的飯都多,可是一夜貪歡之後,他竟對她癡纏不止,他說,女人,你姿勢多、技術好,本王很滿意,賜你王妃之位以資勉勵。 【第一次見面】 傅子軒:聽侍衛說,你傾慕於本王。 秦落煙:不,準確的來說,是我想睡了你。 喜歡和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第二次見面】 秦落煙:脫褲子。 傅子軒:該死,我要殺了你! 秦落煙:殺我之前,先脫褲子。 傅子軒:禽獸!
83.9萬字8 612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