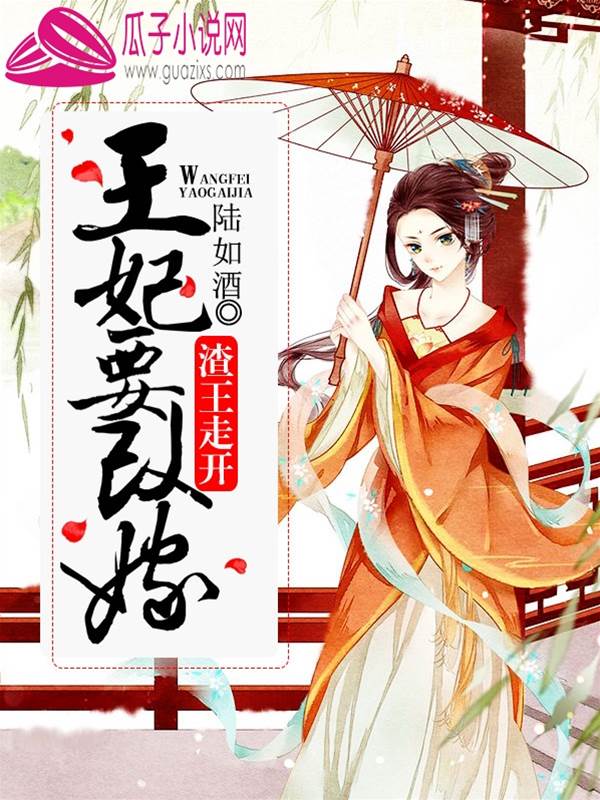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生於望族》 第72章 人算天算
盧老夫人聽了於老夫人的話。還算滿意,但卻沒忘記,自己的要求不僅僅如此。增添幾個夜間巡邏的人手,或是給平府衙打聲招呼,都不過是警戒手段罷了,在無堅固外牆圍繞的顧莊,一但有大批民攻擊,只怕連一刻鐘都支撐不住,就算有人事先發現了,又或是事後平府衙的兵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趕到,也於事無補。畢竟,顧莊的居民大多是手無寸鐵的普通民衆,就算是顧氏族人,也不是家家都能住上大宅院,有高聳的院牆與厚實的門板可以稍加抵外來侵略的,更何況莊上還有大量的佃農、商人、工匠與僕役?
然而,看著於老夫人以及柳顧氏的臉,又再看了看一旁神各異的段氏等人,還是將這些話吞了回去。要的是將各種以備萬一的安排落到實,而不是一再提出建議後,因爲某個心狹窄的小輩爲了爭一口氣而犯糊塗。導致這件大事落到了空。
盧老夫人只說了幾句閒話,便十分利落地告辭了。文怡從開口說第十個字開始,便起往外頭走去,經過柳東行邊時,瞥了他一眼,卻礙於旁人,只能停也不停地往外走。
柳東行眼神一黯,卻很快就恢復了神,他可以聽到,顧家那兩位別房的太太也在辭行。這些大戶人家的太太們,十個裡有八個是好事的,儘管們自認賢良淑德貞靜自守,在人前總是端著端莊貴婦的架子,但閒著沒事時最的還是關注親戚朋友家的流言蜚語。們的離去,意味著關於他世的另一波傳言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傳遍顧莊。雖然婚事沒定,讓他有些沮喪,但一想到二嬸那張臉上會出現什麼表,這點沮喪就立刻一掃而空了!
Advertisement
長房的人沒有留客,盧老夫人與文怡祖孫倆很快就回到了自己家中。文怡看著祖母的臉,有些猶豫地了一聲:“祖母,方纔……”臉一紅,便咬住了脣,低下頭去,不敢把話說完。
盧老夫人擡頭看了一眼,不聲,只是吩咐石楠:“去跟你爹說,去二房請四老爺過來。我有要事要與他商量。要快!”石楠領命而去,另一個大丫頭水葒送了茶上來,悄悄看了兩位主人一眼,便輕手輕腳地退了下去。
盧老夫人平靜地喝著茶,文怡拽著手中的帕子,心越跳越快。很想知道祖母對那件親事是怎麼看的,但又不敢直接開口問,偏偏祖母一點反應都沒有,想猜也猜不。
盧老夫人放下茶碗,迅速地掃了孫一眼,心下暗歎。這件親事,說不上滿意,也始終抱有戒心,在宣樂堂時,不過是當著衆人的面,礙著老妯娌的面子,才說了那些話罷了,只是權宜之計。孫兒才過了十四歲生日不久,離真正出嫁還有兩三年功夫呢,要細細看過,才能確定那個柳東行是不是孫兒的良配。
想到這裡。便開口道:“回頭等你四伯父來了,我跟他商量好事,怕是要開始準備警戒的安排了。咱們家是嫡脈六堂之一,自然是要出力的,你回去查看家裡的僕役,凡是年青力壯的男子,手上差事不要的,都調出來以備萬一,另外再安排有力氣的僕婦在各院班守夜。晚上要用的燈油火蠟、飯食、棒等都要採買齊全了,若有什麼不知道的,再來問我,也可去問仲大。”
文怡說不上心裡是失還是什麼,卻也知道警戒事大,低頭應了,退出房間,便在廊下輕輕嘆了口氣,然後打起神去忙活了。
Advertisement
四老爺顧宜正很快就來了,他在族中形象很不錯,雖然也有人暗地裡說他沽名釣譽,或是裝模作樣,但不可否認,他在長輩面前一向很守禮數,讓人挑不出刺來。
他與盧老夫人談了足足一個時辰,文怡不知道他們都談了些什麼,只知道在安排好一切之後,前去向祖母覆命時,四伯父便面帶微笑地對道:“你們家裡男丁,只兩個青壯參與到夜間巡邏便是了,各門戶都要看嚴了。讓底下人夜裡警醒著些。雖說你們宅子小,沒別人的醒目,但虧在是後來修的院牆,跟早年祖宅的厚牆不能比。”
文怡聽得胡里胡塗的,直到第二天,整個顧莊都熱鬧起來時,才明白了四伯父的意思。
顧家先祖在建立家園時,並不僅僅是考慮到子孫後代的居所而已,除了祭祠、學堂、倉庫等附屬建築以外,也想到了對外防的問題。不過,因爲這是一個村莊,而不是城鎮,加上又地太平地帶,所以,防設施並沒有放在明面上。當然,那是僅僅針對最初建好的那些建築而設置的。
文怡遠遠地看著十多個莊丁從小門中合力擡出一條三丈長、一尺見方的厚重黑木條,搬到九個主宅外圍的路口間,與二十多條同樣大小長度的木條壘在一起,一條一條疊起來,再用厚實的木板與鐵打造而的大鐵釘加以組合,形了一堵一尺厚的重木牆。考慮到人員還要從這裡通過,因此木牆並未合攏,留下了一個半丈寬的缺口。每晚一過初更時分(晚上19點),便用厚木板擋上,有專人看守。
文怡回頭問祖母:“這能行麼?雖說厚的,但終歸是木牆,若是匪人放火,或是用利砍……”
Advertisement
盧老夫人淡淡地道:“那不是尋常木料,已上過幾層特製的黑漆,不懼水火,刀砍不斷,想要對付它,除非是用最鋒利堅固的大木鋸鋸上一個時辰。才能將它攔腰鋸斷。這麼疊了牆,想鋸斷也是不容易的,要拿木樑大力撞開,就象大軍攻城時對付城門那樣,遇到烏合之衆,這已經足夠抵擋一會兒了。”頓了頓,又在惋惜:“事隔百年,老祖宗本想得周到,後輩們卻辜負了祖上的好意。長房的木居然有十來拿去做了新屋子的房樑,二房的木板和鐵釘也都被糟蹋得不能用了!五房索都鋸開做了燒火柴!幸好三房當年搬走時,把他們的木頭都留了下來,不過是堆在角落裡沒人知道罷了!不然只怕不夠這麼多個路口的。而我們家的……”嘆了口氣,“幸好他們將房舍佔去時,我人把木頭都搬回來了,不然也會被糟蹋了。如今只夠做單牆的,跟老祖宗吩咐的兩尺厚的牆差了一半……”
文怡沉默著,從來不知道自家後院裡堆的這些“雜”原來這麼有來頭。可惜了,顧莊承平百年,老祖宗留下來的這些防設施,早就被忘了,怪不得祖母只肯去找伯祖母於老夫人說呢,如今在顧莊,除了這些經年的老人,小輩們怕是連這種東西的存在都不知道吧?
看了祖母一眼:“四伯父說的……我們家的牆……不要麼?”宣和堂的宅子已經被分割過了,只有正面的院牆還是當年初建時的厚牆,其他的都是後來加建的青磚牆,用來分隔院落罷了,論堅固卻遠遠不如老牆。
盧老夫人淡淡笑了笑:“咱們周圍都是房子,哪有這麼容易?再去尋些堅固的木板來,加厚幾個門,日夜派人守著,也就是了。這是命,我們把能做的事都做了,剩下的就看天意了。”
雖然盧老夫人說這要看天意,但文怡深深覺得,人力也十分關鍵。
顧莊上下,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贊同盧老夫人的看法。願意提起十二分警惕心,防備可能來襲的匪徒的。木牆能保護的就只有那九個主宅,那些後建的房舍以及前莊的商鋪、民居就不在保護範圍了,因此莊民只是看著那些黑牆,有些好奇地議論著,反倒是於保護中的顧氏族人認爲這種措施大驚小怪,阻礙了他們的正常生活。有人抱怨木牆缺口太窄,馬車出不便;有人嫌木牆的小門夜裡關得太早了,連累他們在外頭應酬玩樂完,回家時卻被關在牆外;還有人覺得大熱天的樹起厚牆,擋住了風,害得他們在家裡不得不忍炎熱天氣;甚至還有人認爲這木牆是黑的,黑地擋在路間,委實太不吉利。
在這樣的抱怨聲中,六房上下承著不小的力,別人當面雖然不會說什麼,但背地裡卻沒議論六老太太年紀大了折騰,幾個小賊在莊口打個轉,就鬧得全莊人都不得安寧。剛開始時,這種非議只有幾個人提起,過了幾天,便連三姑太太柳顧氏回孃家省親時帶著的那個“族侄”到底是“庶長子”還是老一輩事實上的“嫡長孫”這種大八卦,都無法滿足人們的閒心了。他們紛紛在私下議論,六老太太忽然鬧這麼一出,到底是爲了什麼?而四老爺居然會順了的意,又是打的什麼主意?!有傳聞說大老爺在京城遇上點麻煩,甚至還寫過信回來,暗示要將族長之位傳給二房,四老爺這麼做,長房又不吭聲,是不是意味著什麼?
文怡在紛擾中保持著沉默,什麼話也沒說,每天只是象往常那樣,料理家務、服侍祖母,連閨學那邊也沒再去了,對長房的邀約也找了藉口拒絕,只是在閒暇時,會向丫頭婆子們打探一下口風,看外頭都有些什麼傳聞,當然,除了對祖母和四伯父行爲的議論,還有柳東行世之謎的傳言。
顧莊上已有不人開始懷疑,三姑太太柳顧氏以及柳姑父多年來反覆強調的“嫡長”份,其實只是他們給自己臉上金,真正的嫡長子、嫡長媳另有其人,只是已經去世了,柳東行正是他們的孤,而柳姑父的生母,也並不是其父元配正室,也就是說,三姑太太當年是嫁了個庶子,真不知道是長房被騙了婚,還是爲了攀龍附,明知對方是庶出也顧不上了……
文怡聽了這些傳聞,心裡爲柳東行高興。他終於擺了那種尷尬的境。但接下來,又開始擔心,因爲傳聞中也提到,六太太又帶著八小姐上長房請安去了。
時間轉眼就來到了端節的前一日。因世子還席那天,顧家各房爲了夜間巡邏與組織防等事忙,人們都無心赴宴,導致席面上有些冷清。世子雖沒說什麼,但柳顧氏深覺丟了面子,便好說歹說,勸他多住兩日,等端節下顧家進城去打醮時,再正正式式擺一日戲酒,給他踐行。世子拗不過舅母的熱,加上也有意與舅母和表弟多親近,便從善如流了。
這時,平城裡傳來消息,府城以南八十里外的平南鎮,在四月底遭到了流民的侵襲。那流民的首領自稱是“皇天普照大王”,帶著近千人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聲稱要殺盡爲富不仁者,劫富濟貧,還說今年的旱是上天示警,老天爺派他下來懲治貪惡霸的。他們佔了平南鎮兩日,燒殺擄掠無所不爲,沒想到一時不察,兵殺了個回馬槍,折了大半人馬,一路向南逃竄去了。兵一路追殺過去,據說那個匪首邊只剩下不到一百人,用不了多久,就會落網了。
顧莊上下聽了這個消息,奇怪地沒有到張,反而放鬆了許多。看來民是有的,匪徒也是有的,但那是發生在平南,離顧莊有近百里呢,兵又追得,那些民怎能逃到顧莊來?可見顧莊一切太平!
平府的衙差調了大半前往平南增援,知府大人再次派了使前來,暗示東平王世子朱景誠以及王府親衛,爲了安全計,當儘早離開。朱景誠給了肯定的回覆,而顧家長房上下,已經將打醮要用的品準備齊全,預備送進城去了。爲了確保道路暢通,那厚厚的木牆被搬了開來,只等忙完端節事宜,就要拆開,迴歸到角落裡去了。
文怡見狀,心中暗暗著急,立時回稟了祖母,而盧老夫人也馬上請了四老爺顧宜正過來說話。無奈族中反對者衆,顧宜正雖然代理族中庶務,卻終究不是族長,而族長所在的長房那頭又明裡暗裡催個不停,他只能讓步了。而且平南那邊的消息也變相證實了,匪不會禍及顧莊,他反倒還勸盧老夫人,不必太過擔心。
文怡祖孫倆看著他離去的影,默默對視一眼,都有些無奈。文怡勉強笑道:“應該不會有事的,不是說……平南出了子麼?上回大概只是過來探路,見事不可爲,他們就另外找上了平南……”
盧老夫人沒說話。
就在這一晚,當人人都在睡時,顧莊忽然起火了。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完結1081 章
神醫仙妃
一朝穿越,被綁進花轎,迫嫁傳聞中嗜血克妻的魔鬼王爺? 挽起袖子,準備開戰! 嗯?等等!魔鬼王爺渾身能散發出冰寒之氣?豈不正好助她這天生炙熱的火型身子降溫? 廊橋相見,驚鴻一瞥,映入眼簾的竟是個美若謫仙的男子! "看到本王,還滿意麼?"好悅耳的嗓音! "不算討厭." 他脣角微揚:"那就永遠呆在本王身邊." 似玩笑,卻非戲言.從此,他寵她上天,疼她入心;海角天涯,形影不離,永世追隨.
101.5萬字8 119356 -
完結674 章
農門醫女:掌家俏娘子
郭香荷重生了,依舊是那個窮困潦倒的家,身邊還圍繞著一大家子的極品親戚。學醫賺錢還得掌家,而且還要應對極品和各種麻煩。 知府家的兒子來提親,半路卻殺出個楚晉寒。 楚晉寒:說好的生死相依,同去同歸呢。 郭香荷紅著臉:你腦子有病,我纔沒說這種話。 楚晉寒寵溺的笑著:我腦子裡隻有你!
125.4萬字6.3 81054 -
完結180 章

藏歡
太子沈鶴之面似謫仙,卻鐵血手腕,殺伐決斷,最厭無用之人、嬌軟之物。誰知有一日竟帶回來一個嬌嬌軟軟的小姑娘,養在膝前。小姑娘丁點大,不會說話又怕生,整日眼眶紅紅的跟着太子,驚呆衆人。衆人:“我賭不出三月,那姑娘必定會惹了太子厭棄,做了花肥!”誰知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那姑娘竟安安穩穩地待在太子府,一路被太子金尊玉貴地養到大,待到及笄時已初露傾國之姿。沒過多久,太子府便放出話來,要給那姑娘招婿。是夜。太子端坐書房,看着嬌嬌嫋嫋前來的小姑娘:“這般晚來何事?”小姑娘顫着手,任價值千金的雲輕紗一片片落地,白着臉道:“舅舅,收了阿妧可好?”“穿好衣服,出去!”沈鶴之神色淡漠地垂下眼眸,書桌下的手卻已緊握成拳,啞聲:“記住,我永遠只能是你舅舅。”世人很快發現,那個總愛亦步亦趨跟着太子的小尾巴不見了。再相見時,秦歡挽着身側英武的少年郎,含笑吩咐:“叫舅舅。”身旁少年忙跟着喊:“舅舅。”當夜。沈鶴之眼角泛紅,將散落的雲紗攏緊,咬牙問懷中的小姑娘:誰是他舅舅?
34.4萬字8.18 32062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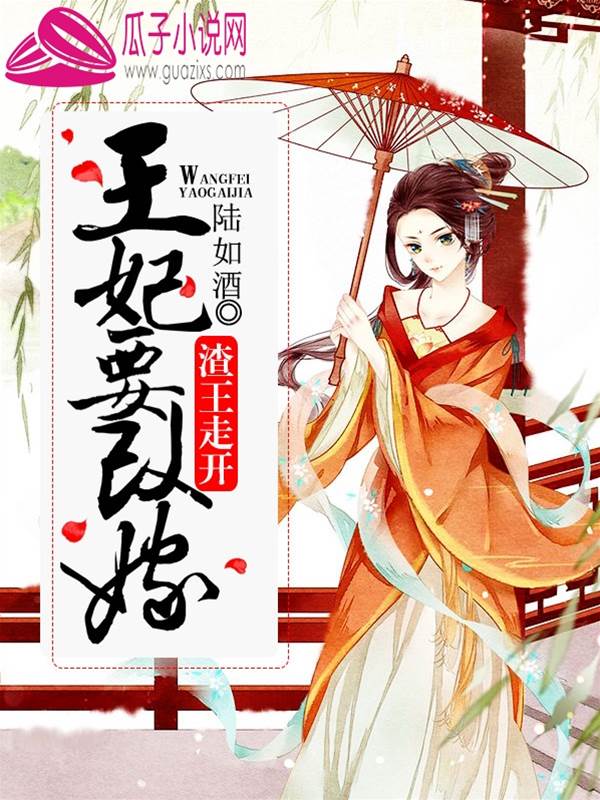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9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