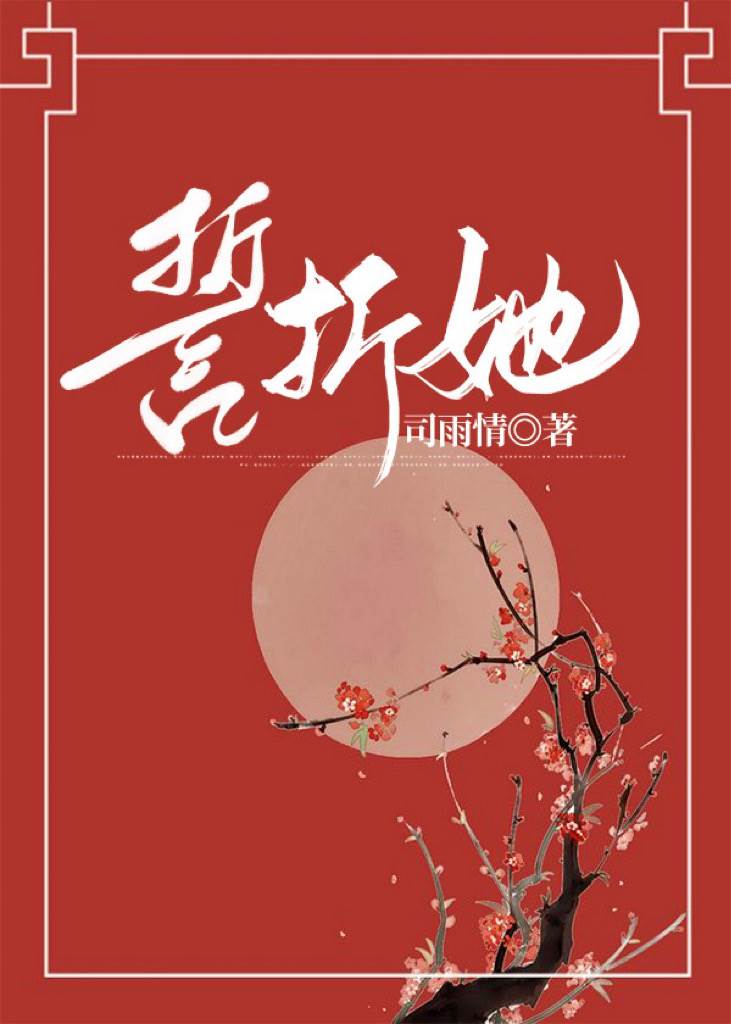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枷鎖》 第125章 前世
一句圣上,一聲萬安,生生將他推拒到千里之外。
剛一剎那乍見時滿腔的歡喜,瞬息被的生疏碎了渣滓,之后淬了冰,冷的他凝固,寒的他心口發涼。
他依舊半蹲在那,雙手還保持著之前出去的姿勢,只是雙眸的驚喜與歡愉漸漸褪去,沉寂一片不見天日的沼澤。
僵的側過臉,他一瞬不瞬的盯著那匍匐跪地的人,似不死心的要從上看出些旁的緒。然而沒有,他目的只有的卑躬屈膝,只見的卑微叩首。
他眸猛地栗。這一瞬息,靈魂深好似傳來撕扯的劇痛,痛的他幾發癲,疼的他險些發狂!
阿苑,阿苑。
九年之后再見,他與之間,可就只剩一句問安?
沈文初此刻仿佛置于怪陸離的大夢中。
他雙目失了焦距的向對面的九五之尊,恍恍惚惚的又看向那伏地叩首的妻子,只覺得面前的場景如做夢般不真實。
眼前似隔了重重大霧,再也無法將人看得真切。
意識好似飄到了半空,周圍的一切也似都離他遠去。
他很想將這一切都當做一場荒誕的夢,可他卻知,這并非是夢。
“圣上……萬安。”
他還是來到了的側,雖步伐蹣跚卻異常堅定,俯首問安的時候,緒已趨于平靜。
罷了,真也好,假也罷,都不重要了。
是他明正娶的妻,是他深之人。
無論接下來迎來的會是什麼,他都會與一道面對。
沈文初清朗的聲音打破了室令人窒息的沉悶。
林苑的淚就一下子涌上了眼眶。
事到如今,他也不肯怪,竟還愿與生死與共。
可卻如何愿見他步死地?
是的錯,是不該將他拉扯進的旋渦中。
Advertisement
強烈的后悔啃噬著的心。
這一刻,恨不得能匍匐到那個男人腳下,給他下跪,給他磕頭,只要肯放過他,放過他們,可以任由其打罵殺伐,可以任由其發泄怒火,如何作踐都。
晉滁黑如寒墨的雙眸,落在了并列而跪的兩人上。
此刻在他前匍匐跪地的二人,像極了恩兩不疑的苦命鴛鴦。
這個認知讓他右手有些許發抖,差點控制不住的拔劍,將跪在旁的那個男人劈碎末!
可他終是忍住了。
縱是他恨的發狂,此刻他亦要忍住,因為他做錯了事。
想起林家,他雙手驀得一抖,這一刻悔恨與懼怕化作了濃烈的不安,如濤浪將他悉數湮沒。
萬一知道,知道他……
他猛咬了牙將這些念頭強行拋擲出去,拒絕做這般的假設。
還尚不知道,日后也將不會知道。
這件事,他永遠也不會讓知曉。
他慢慢握了拳,強迫自己將目從沈文初上移開。他與還有的救,不能因為一個沈文初,就讓與他離了心。
“阿苑,你我之間何來這般生疏?縱是相隔九年,可我待你之心,一如既往。”
林苑本以為接下來迎接的將會是疾風驟雨,如何也沒想到,他竟未問未斥責也未雷霆大怒,反而態度略顯溫和。
錯愕間尚未回神,肩上就多了雙強勁有力的手掌。那厚實的掌心上肩的那剎,的記憶讓反的做出拒絕作,待猛地回過神時,見到的就是他那僵在半空的手掌。
可他依舊并未怒,在僵過瞬息后,又小心翼翼的朝手,這次見并未抗拒,就稍用力將扶了起來。
“阿苑,你尚在病中,我扶你先到榻上歇著。”他單臂環過肩背,仿佛未察覺輕微的栗,輕的攬抱著往榻上的方向而去,同時令門外候著的太醫。
Advertisement
林苑沒有說話,也不敢回頭去看沈文初的神,任由晉滁扶著到了竹榻上。
“即便你要與我賭氣,也不該拿自己的子開玩笑。你子素弱,這僻遠鄉下簡陋又鄙,哪里適合你調養子?”
他袍坐在旁側,手輕握住右手,掌心帶些貪的輕微挲稍許后,朝外遞給來診脈的太醫。
“阿苑,這些年來你苦了,是我不好,應該早些找到你才是。”
屋異常的靜,除了那深款款的帝王在說著話,其他人皆保持著緘默。連呼吸聲都似得極輕。
診脈的太醫幾乎全然屏住了呼吸。面前這放著嗓音溫似水的人,跟那皇城里晴不定的帝王簡直判若兩人,讓人不知是暴風雨前的寧靜還是旁的,只讓人約不安。
林苑不知該如何回話,亦不知該以何種態度來對待他。
不知是不是九年未見印象變得模糊的緣故,總覺得面前的人太過陌生了,陌生的讓到有些違和。此刻他小心翼翼的待,連與說話都好似怕嚇著般了嗓音,頗有幾分待如珠如寶的意味,這般珍視,便是九年前,好似也不曾見他姿態放得這般低過。
他如今這番態度,可是想將這里翻篇,能放文初,以及他們所有人一馬?
雖然這般做法明顯與他不符,可心還是忍不住奢,或許做了多年帝王,他人也變得寬容溫和了呢?
“如何了?”太醫診脈過后,晉滁問道。
太醫回道:“娘娘是憂思過甚,傷及了肺腑,需要心調養,方能將子慢慢養回來。”
他朝消瘦的面上看過,忍不住將的手合攏在掌心里:“若即日啟程回京,子可經得住顛簸?”
Advertisement
太醫想了想,道:“若能再待上兩日,將再養一養,是最好不過的。”
“那就在此地再多待兩日。”
屏退了太醫,屋又重歸了沉寂。
晉滁略抬了眼皮,終于掃向屋的一干人。
稍遠呆站的春杏,床榻前癱坐的木逢春,還有那跪地朝他們這怔怔著的沈文初。
他沉了眸,竭力維持平靜的表象。
“逢春,近前來。”
旁邊人突然的一句話,讓林苑陡然回了神。
驀的抬眸,雖極力掩飾驚恐,卻難掩驚疑不定之。
木逢春茫然的抬頭,恰撞進帝王深沉的黑眸中,讓他忍不住僵住了。
“木逢春,枯木逢春猶再發,當真是好名字。怪不得殿試那會,便覺你親切,原來緣分在這。”他看向旁人,笑問:“如何不早與我說?難道我就是那般容不得人的?”
林苑腦中難免想到他強迫燒草編小馬的景。
“是我想差了。”竭力讓出口的聲音顯得不那般張與生,同時也盡量松緩些繃的脊背。
終于又對他說話了,不再是那冷冰冰的問安。
他看的目忍不住變得灼熱,恨不得放縱自己積年抑的所有,悉數沖傾瀉而去。
可他現在還不能,還不適應,他需慢慢來。
在他看的眸就要轉為迫人的貪婪盯視時,他強迫自己轉了目,看向對面的木逢春:“日后在朝中好好干,為國效力,為朕的左膀右臂。”
說完,也不等木逢春回應,轉而看向春杏的方向:“春杏,扶你小主子下去歇著罷。”
春杏一個激靈,手腳抖著過來扶木逢春。
木逢春這會突然回過神來,向他娘的方向。
“娘……”
誰知見他開口,晉滁卻驟然變了臉,突然冷厲盯著他大喝:“出去!”
木逢春被喝住的那剎,被春杏連拖帶拽的用力拉了出去。
剛一踏出了屋門,兩人就分別被人捂住了,拖向了一旁。
此時屋僅剩三人,晉滁與林苑,對著沈文初。
屋的氣氛沉悶的有些令人窒息,林苑已經來不及去想剛他為何突然厲聲喝斥逢春,現在要擔心的是他能不能放過沈文初。
逢春他輕易放過了,那文初呢?他可還會放過?
晉滁攏著的手,緒不辨的向沈文初,而沈文初卻始終都在看著林苑。
林苑知道,沈文初是在等的一個解釋,還有一個答復,可是,此時此刻,沒法給他想要解釋或答復。甚至,連看他一眼,都不能。
沒人說話,屋的氣氛繼續沉寂,林苑知道,不能再繼續這般下去了,得打破這沉默的氣氛。
“圣上,這位是……”
“我知道。”晉滁攏著的掌心微微用力,不許分毫,連指向沈文初的方向都不允許。對上的視線,他面如常的笑道:“我知他是逢春的夫子,你不必多余解釋。”
沈文初聞言卻撐著子站起來,俊秀的面容略帶蒼白,沖著前方男人的方向施禮:“在下是……”
“文初!”林苑猛地一聲制止他,到晉滁與沈文初的目同時朝而來,霍的驚覺,聲音生了三分:“沈夫子,謝謝你這幾年用心教導逢春。”
文初與的關系,他只要稍打聽便知,如今他既這般說,那就表明不肯多予追究。如此就好,留的條命就好,其他的,不重要了。
沈文初的搖晃幾瞬。
幾個瞬息后,他兩手作揖,重新對著對面的兩人施禮,聲音微帶著:“在下確是木逢春的夫子,姓沈,名文初,字,清平。拜見圣上,娘娘。”
林苑別過眼,狠狠咬了下舌尖。
晉滁著對面那氣質溫潤的男子,面上浮著淡薄的笑。
若說此生他最想殺之而后快之人,那沈文初絕對算上一個。不殺此僚,他簡直要寢食難安。
他真是恨吶,比對那符居敬都恨。
那符居敬也不過是權衡利弊下的選擇,可這沈文初卻是鐘心悅后的選擇。
這種認知不僅讓他恨,也讓他痛,如把尖銳的利刃,刺向了他心窩最的地方。
可他依舊未表現分毫,饒他心中已是恨痛滔天。
“你也下去罷。”
沈文初慢慢轉離去,離開的背影蕭索,頹然。
屋門被人從外面帶上了,屋僅剩了他們二人。
晉滁不著痕跡的打量了一下這不大的茅屋,簡陋仄了些,卻干凈整潔,臨窗的桌上擺了瓷瓶裝了些野花,旁邊擺了兩個自己編纂的藤椅,墻壁上掛滿了落款為清平的字畫,臨門還懸了個風鈴隨風而,雖是陋室卻充滿了溫馨,看得出房屋主人的用心。
他的目從這些布置上寸寸移過之后,最后落在了這方竹榻上。竹榻矮小也不算太寬大,但睡兩人已經足夠。他忍不住手去上面的被褥,雖陳舊,但已蓋了數個春秋,其上已沾染了的氣息。
他的眸幾經變換,他很難不去想,在這張榻上,在這沾染了香的被褥上,他們做過了什麼。他幾乎魔怔的不停的去想,親沒親他的,沒他的,還親過哪,過哪……明明不去想,可偏偏這些念頭瘋狂的往腦中竄,迫的他頭部炸裂。
林苑見他的目持久的盯視在那榻上,忍不住出口喚了聲:“圣上。”
他卻驟然掀眸:“你喚他文初,卻喚我圣上?”
心跳猛地一滯,而后喚他道:“伯岐。”
他面稍霽。
“你子不好,早些歇著吧,歇兩日待你轉好些,我就帶你回京。”
他扶躺下,而后在外側的方向也合躺下,為蓋好了被子。
“日后,你我就好好過日子,過去的,就讓它過去罷。”
他強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些容易讓他魔怔的事。
如今,還活著,這就已經足夠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68 章
全京城都盼著她被休
上一世的蘇皖,未婚失貞,狼狽至極,最終含恨而死,重生歸來後,她抱著兒子去了景王府。 景王楚晏,一雙桃花眼勾魂攝魄,卻偏偏冷淡禁欲,被譽為京城最寡情之人,多少貴女削尖了腦袋想成為他的侍妾,他眼皮都不帶掀一下。誰料,他卻突然要成親了,娶的還是那個聲名狼藉的女子!整個京城都炸開了鍋,茶餘飯後,每個人都等著看好戲——單憑一個孩子就想拴住景王?當真是癡心妄想! 然而一年又過一年,景王依然被栓得牢牢的,吃醋狂魔始終在線,連她多看兒子一眼都不行!蘇皖不僅沒被休,還寵冠京城!俊美妖孽男主vs貌美黑心女主ps:甜寵,慢熱,不喜勿入,暫定晚上十點左右更新,麼麼噠比心。推薦一下自己的接檔文,求收藏~古言:《嬌妻難哄》by黑子哲侯府倒臺後,彎彎就被二叔送給了三皇子。她自此成了他的籠中雀,任其欺辱把玩,死時才不過十八歲。重生歸來,彎彎戰戰兢兢撲到了豫王懷裏。美人眸中含淚,秀眉纖長,美得令人怦然心動,然而在場眾人卻倒抽一口涼氣,誰不知豫王冷血冷情,最厭惡女子的碰觸?誰料她不僅沒事,還被豫王當成個小掛件,帶回了王府。
60.3萬字8 32587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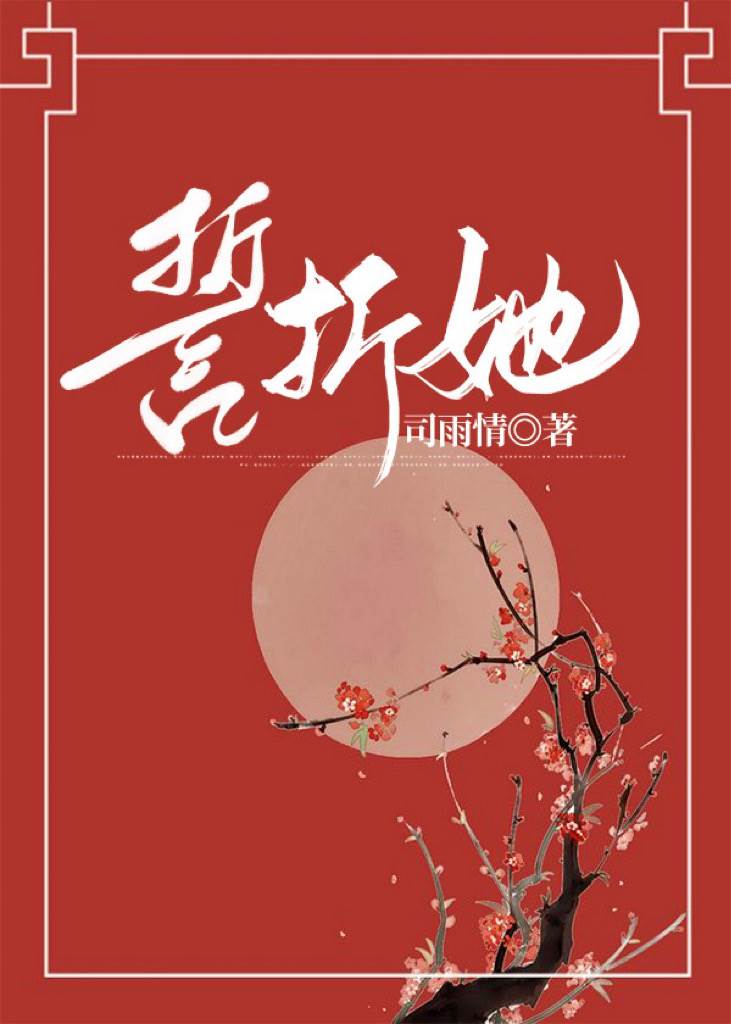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8952 -
完結646 章
醫妃傾城:皇上有禮了
《醫妃傾城:皇上有禮了》尼瑪,顧非煙做夢都想不到,她竟然穿越了! 不僅穿越,還收到了一份熱氣騰騰的宮斗「大禮包。 自虐嫁禍陷害栽贓?她就不會將計就計?不就是狗血宮斗戲麼?還難得到她這個來自21世紀的醫學博士?不過……這個皇帝怎麼有點煩人?「愛妃,利用完了就想跑?」 「那不然讓我以身相許嗎?」 「準了」
116萬字8 102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