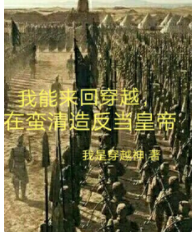《回到明朝當王爺》 第449章 重新洗牌
與此同時,兵部陸完也突然擂鼓聚將,把京中諸將全部召集來宣讀聖諭,然後選出二十餘名散職功勳將領立即隨張永去與十二團營各高級將佐移兵權。武定侯郭勳直接掌管的神機營進駐京城,五千營、三千營移防京師左右。
已經回京的司禮監首領杜甫在大將軍許泰的武力配合下,把十二團營的監槍使太監全部撤換掉,司禮監、尚寶監等重要司衙門皆由許泰的人馬把守,同時外四家軍做爲唯一一支沒有固定防務的機力量,也移駐北京城下,刀出鞘、弓上弦,殺氣凜然。
隨著各個衙門一道道將令的下達,只見宮裡宮外、城裡城外,一路路兵馬川流不息,人喊馬嘶,燈籠火把串如長龍,滿城百姓都驚惶失措,不知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調發生了什麼事。
廠吳傑、西廠苗逵派出大批的檔頭、千戶,率領番子們臨司禮監、東廠、錦衛,逮捕了一批管事太監、錦衛同知、僉事和東廠的檔頭、千戶,刑等人,同時六部九卿等重要員地門口都出現了番衛特務的影,既是監視、也是保護,總之,不得進出。
第二日凌晨,東方第一線照耀在紫城上時,又有一批以江西道巡察使爲首的朝中員分別被勒令閒住、批捕。
忐忑不安的文武員被召集到皇宮前邊,三大學士出面向驚惶不知所謂的大臣們宣讀了一道奇怪的聖旨。當文武員們看到站在最前的三大學士時,便知道楊廷和也了牽連。恐怕是前途堪憂了。
閣三大學士以焦芳資歷最老,但是目前實際上的第一首輔已經變了楊廷和,由於年紀太大,焦芳也已漸漸退居幕後。上一次皇帝施行新制改革,朝中由楊廷和主持,而焦芳做爲資歷最老的閣老卻藉故安地方離開京師,就是樹起楊廷和的風向。
Advertisement
然而現在卻是由老焦芳來宣讀這樣重要的旨意,大學士樑儲位列其後,而楊廷和居於末位。儘管這僅僅是一個公開場合的站位,但是在場上卻是一種很微妙的兆示,足以向這些場中打滾多年的老油條提示許多人事變的訊息了。
更令他們驚駭的卻是旨意的容令人匪夷所思,儘管早知道這位皇上平素的想法就是天馬行空,也難以想象他會下達這樣一道聖旨。焦芳一句一頓唸的清清楚楚:“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令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錦衛,六科,十三道。每衙門止留佐貳一員在京,其餘並閣,皇親,公侯,駙馬,伯爵,俱赴行在!”
這道旨意一下。北京城各個衙門口兒就只留一個二把手理日常事務,其他幾乎所有員,外加皇親國戚、功臣勳卿、特務頭子等等,都要傾巢出,赴通州朝覲天子。天下的政治中樞一下子從北京變通州了。
旨意宣罷,輿論大譁,員們驚疑不定,議論紛紛,焦芳等三大學士面沉似水,立於上方一言不發。只聽午門前文武百議論聲越來越高,終於有人憤然高呼:“這是謀!皇上怎麼會下這樣的命令?一定是謀!”
“不錯!這一定是有人脅持了天子,要將滿朝文武和皇親國戚全部往通州一網打盡,焦閣老,不可上當啊!”
有些穩重一點的,措辭倒還溫和:“三位大學士,皇上不回京城,卻要滿朝文武盡赴通州,實是曠古未有之奇聞。昔年永樂大帝、英宗皇帝駕親征塞北,也不曾帶出這麼多員,是否封還旨意,上疏皇上?”
四下著普通侍衛服的人,其實早就換了西廠番子,這些人冷眼旁觀,哪些人惶恐驚懼、哪些人出言煽,滿朝文武各自表現盡皆記在心裡。
Advertisement
等到他們鬧騰得差不多了,四下突然冒出幾支整整齊齊的隊伍,纓槍如林、刀鋒似雪,甲冑鮮明,明黃的戰袍、帽上著一支突突的天鵝羽。
外四家軍!這是皇上的親軍,林軍裡的林軍,皇上親任三軍統帥威武大將軍的外四家軍。午門前頓時靜了下來,隨著整齊的隊伍一步步近,那鏗鏘的步伐都發出鋼鐵一般渾厚沉重的聲音,文武百們有種抑的不過氣來的覺。
前百步,“鏗”地一聲,隊伍停止了前進。可是那種窒息的抑卻毫沒有消失,士兵們一個個神冷肅,就象一道鋼鐵鑄就的森林。
秀才遇見兵時,應該怎麼辦?
‘秀才’們騎馬的騎馬、坐轎的坐轎,羣結隊地離開北京城,在許泰大軍的護送下,‘爽爽快快’趕向通州城朝見天子去了。京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一部分高層或耳聞、或揣測,多明白了一些,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平素不問朝政的皇親國戚們,卻是糊里糊塗,不知所謂。
南京大獄,一個甲鮮明的將軍端然坐在椅上,筆結實的軍服、軍靴下踏著一個**的**,那上痕累累,被反綁雙手倒在溼朊髒的地面上,猶如一頭待宰的豬玀。
鞭梢毫不在意地撥弄著他的下,那個披頭散髮、赤**的人卻毫無知覺,江彬惻惻地笑起來:“錢大人,滋味兒如何?”
“嘖嘖嘖,都沒反應,啊!我忘了,錢大人就是對付人才象個爺們,是不是得找個人來你才行呀?可惜了,這軍中大獄,不準人進來,你說怎麼辦呢?”
“唔……唔唔……”,錢寧掙扎了一下,他的裡塞著一團破布,本說不出話來。
Advertisement
他地下也不知怎麼弄的,張的如同一桿槍戟,部卻被牛筋兒系得的,也不知充多久了始終不得消褪,因充過久而油亮發紫,江彬手中尖利的鞭梢在上邊,就沁出紫黑髮臭的珠來。看來淤脹的早已經在裡邊變質甚至凝固了,否則只消破道口子就得噴濺出來。
江彬嬉皮笑臉的道:“錢兄,兄弟手下的服侍的還算周到吧?呵呵,侍候人可不只是錦衛的人才懂,軍裡邊人才多著呢”。
wWW ⊙тт kan ⊙C 〇
錢寧的目已經快要噴出火來,落到這步田地。他還有什麼好怕的?現在他和太監沒有什麼區別,甚至連太監都不如。儘管幾日滴水未沾了,可是難免還是會有尿,但是現在本排不出去,他的小腹鼓如鐵,那種痛楚是無法言喻的。”
“你們這羣混帳王八蛋!”江彬扭頭朝手下罵:“我說過多次了,錢大人與我可是不打不相識的。讓你們把錢大人得侍候舒坦了麼,看大人的樣子好象還不夠舒服。一點都不讓老子省心!”
“是是是!”
江彬又扭過頭來,滿面春風地道:“錢兄,我說你聽啊!”
錢寧:“嗚嗚嗚……”
江彬:“你我兄弟一場,深厚,你就放心去吧,你的那些妻妾,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們的,絕不讓們食有缺,春閨寂寞。兄弟想你的時候,就睡睡你的老婆,這一來也就懷念起你了,你看兄弟的法子好不好?”
錢寧:“嗚嗚嗚……”
江彬擺手道:“你不用謝我,誰讓兄弟是實在人呢,人點滴之恩,我江彬一定是涌泉相報啊。錢兄,等你上路了,兄弟我還會在府裡給你設個靈堂,讓你的夫人們按時祭奠呢!”
錢寧:“嗚嗚嗚……”
江彬:“唉,錢兄啊,我知道你捨不得我,兄弟也捨不得你啊!你不是喜歡在人上作畫嗎?你看這樣行不,兄弟打明兒起就拜南京城最好的畫匠爲師!我一定學好水墨丹青,在你老婆上勤加練習,每年到了你的祭日,我一定花樣翻新的鼓搗出來!讓你的夫人們祭拜你時在你靈前展示一番,以你在天之靈!”
錢寧說不出話,但是子卻劇烈地搐了一番,中一陣咳嗽,隨即,鼻腔中涌出鮮。他被氣得吐,卻被堵住,兩道殷紅的鮮自鼻腔裡流了出來。
“哈哈哈哈……”,江彬仰天大笑,笑聲在獄室迴盪不已,過了半晌,他擡起腳用靴尖給錢寧蹭了蹭鼻,然後站起道:“大家好兄弟嘛,你瞧瞧你,個什麼勁兒?”
,又從錢寧的鼻子裡流了出來,江彬慢慢俯下,對上錢寧那雙死魚一般的眼睛,從懷裡掏出一頂綠油油的小帽兒,讓錢寧看了個清楚,然後‘啪’地一下扣在了他的頭上,錢寧力地扭著,想要掙扎掉它。
江彬似笑非笑地道:“老錢啊,兄弟我特地命人制了幾百頂這樣的小帽,你放心,我會隔三差五給你燒一頂過去,讓你的頭頂如青山不老,鬱鬱蔥蔥。
對了,你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那未年的小兒子吧?我會好好栽培他的,讓他長大*人之後做南京青樓之中的頭號大公,這才配得起你這頂四季長青的綠帽子呀……”。
“呃!呃!……。”錢寧的子就象打擺子似的,鮮如注般從鼻孔中噴涌出來,他的子掙扎的越厲害,鮮噴的越多,整個口鼻全被糊住了,子的抖由急而緩,漸漸沒了靜。
江彬臉上的笑漸漸消去,眼中出鍼芒一般鋒利地目。一個親兵過去踢了錢寧兩腳,然後擡頭道:“大人……”。
江彬一擺手,轉向外走去。走出大獄,到了之下,一個從宣府追隨他來到金陵的心腹親兵悄悄跟了上來,低聲道:“大人,錢寧氣斃了”。
江彬仰天吁了口氣,放鬆了臉上獰厲的線條。
那親兵又低笑道:“大人,錢寧的幾房小妾確實如花似玉,心,要不要給您……?”
江彬嘿嘿一笑,拍拍他肩頭道:“小蚊子,剛剛我就是爲了氣他才這麼說,你當我還真的要學他不?此一時,彼一時也。老子現在可不是流氓把總,而是將軍,懂嗎?
將來,咱也能站朝堂的,人妻解恨是解恨,可是貽人把柄就犯不著了。犯家眷,還是由法司衙門置的好,你們別沾手,大丈夫功名就,還愁沒人麼?”
“是!”,小蚊子陪笑道:“大人高見”。
江彬抻抻嶄新的副總兵雄獅補服袍,笑瞇瞇地道:“那當然,做嘛……做久了自然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通州城頭,黃羅傘蓋。
正德皇帝與楊凌、張天師兄妹立於城頭之上,旁侍衛扈從。遠遠的,已約可見大隊人馬正逶迤而來。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楊卿,你來對一對如何?”
沒料到正德還有這興致,楊凌想也不想便道:“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
“唉,這是聯,不可用,你再想一對”。
“這個……”,楊凌心道:“除了東西當鋪當東西,我可就記得男學生生男了,還有什麼吶?”
可憐楊秀才實在不擅長對對子,一時便僵在那兒,張天師聽了也蹙眉細思,一時想不出合適的對法,正德本就是等著百到達在這兒閒逗悶子,所以也不著急。
張符寶那眼角兒一直脧溜著楊凌看呢,見他爲難模樣,不知怎地,心中也替他著起急來,看著,心中忽地想到一個對子,忙悄然退了一步,待楊凌過來出一食指,左邊一指、右邊一指,然後另一隻手也出食指,兩食指在一起合了合,又左右一分。
楊凌一怔:“這是啥?鬥鬥飛?”
張符寶見他不懂,又急又氣地站在皇帝后邊衝他眉弄眼的,楊凌心中急轉,忽地想了出來,喜道:“左侍衛,右侍衛,左右侍衛侍左右!”
張符寶聽了臉上頓時綻開一個甜甜的笑臉,正德訝道:“不錯不錯,真的不錯,還能應眼前這景兒,嗯,最佳的當然是對東西,但這片刻之間能想得出左右,也十分難得了”。
楊凌心虛地看了眼符寶,乾笑道:“不知皇上心中,除了東西當鋪的對子,想得是什麼妥當下聯?想來當比臣這一條要高明得多了。”
正德哈哈笑道:“朕負責出上聯,不負責想下朕。”
楊凌窒了一窒,拱手道:“皇上英明!”
正德嘿嘿一笑,閃目看看城下越來越近的京中百,說道:“整個朝廷都被朕搬到這通州城了。現在,立即下達各府道軍政要員調防的聖旨,在朕率領百回京之前,一切部署必須完!”
“是!”楊凌也不再說笑,肅然籤應了一聲。
正德皇帝坐鎮通州,遙探肅清京中反叛、將文武百調出京城,全部約束於帳下,隨即從通州發佈調令,各地重要吏的調防換開始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權力重新洗牌在他手中開始迅速完。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傾城俏醫妃
(章節錯亂,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她,是醫藥世家,廢物顧七,平凡的面容下掩藏著一張傾城國色。 她,是鬼醫聖手,異世靈魂,淡漠的面容下有著隨心百變的性格。 當她穿越而來,代替她成了“她”時,身中極品媚藥,是再死一次?還是找個男人當解藥?他,玉樹蘭芝,清逸絕塵,看似無害,實則卻是吃人不吐骨的腹黑狼,一朝錯上,為免被他剝皮抽筋,她只能用上連環計,一避再避,量他有再大的能耐,也絕不會想到,當日強上他的人就是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寵她入骨,愛她至深,哪怕她是世人眼中的廢物,無才無色,他卻視若手心之寶,把她放在心尖之上,許諾,哪怕負盡天下,也絕不負卿!她本是慵懶淡泊之人,冷血而冷情,稟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既然有他護著她,寵著她,愛著她,她就斂起鋒芒,掩去風華,當一個世人眼中的廢物,偷得浮生半日閑。是誰觸了她的逆鱗?激起她心中嗜血?無法修煉的廢才?無一是處的廢物?毫無戰鬥力的顧七?誰知,她風華的綻放,強勢的崛起,只為那守護她而倒下的男子!一朝風雲湧動,揭去廢物之名,揚吾強者之威!長劍在手,且問天下誰與爭鋒!
194萬字8.4 974186 -
完結183 章

一紙休夫,代嫁王妃要出牆
蘇洛雅是丞相府最不受待見的三小姐,父親和皇帝的關係讓蘇洛雅成了皇帝護女被逼代嫁的最佳人選。花轎冇坐熱,一支利箭,魂穿而來的蕭蕭代替了蘇洛雅,展開了不平凡的古代之旅。遇到的第一個男人,溫柔絕美,儼然一小受!混入皇宮要找武卿王,囧,居然找錯了人,攪亂了溫柔如水四皇子的心……夜探王府,被抓現形,傳說中的宗卿王爺風流成性也就算了,居然還是個斷袖!好吧,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嬸不可忍,本姑娘從來不是一個省油的燈,既然你不喜歡我,我也就不必再委曲求全了!某日,蘇洛雅一紙休書拋下,盛怒而去……
42萬字8 12754 -
完結705 章

侯門棄女:妖孽丞相賴上門
一覺醒來,穿越到一個歷史上沒有的朝代,喬薇無語望天,她是有多倒霉?睡個覺也能趕上穿越大軍?還連跳兩級,成了兩個小包子的娘親。 看著小包子嗷嗷待哺的小眼神,喬薇講不出一個拒絕的字來。 罷了罷了,既來之則安之吧,不就是當個娘嗎?她還能當不好了? 養包子,發家致富。 不為惡,不圣母,人敬我,我敬人,人犯我,雖遠必誅。 杏林春暖,侯門棄女也能走出個錦繡人生。 小劇場之尋親: “囡囡吶,嬸娘可算找到你了!你當年怎麼一聲不吭地就走了呢?嬸娘找你都快找瘋了!你還活著真是太好了,跟嬸娘回家吧!一個女人賺了那麼多銀子,在外頭多不安全吶!”某花枝招展的婦人,拿著帕子,“傷心欲絕”地說。 “你不關心我孩子,倒是先關心我銀子,真是好疼我呢!可是我們認識嗎,大嬸?”喬薇一臉冷漠。 小劇場之尋妻: 小包子領回一個容顏冷峻的男人:“娘親,叔叔說他是我爹。” 喬薇莞爾一笑:“乖兒子,告訴你爹,要證明自己的身份,應該怎麼做?” 小包子翻開金冊子,一板一眼地說道:“《喬氏家規》第一百零一條,欺辱未成年少女,賜宮刑。叔叔,如果你真是我爹的話……” 不等小包子說完,男人冰涼的指尖掐住了喬薇的下巴,露出一抹冰冷而危險的笑:“如果爺記得沒錯,那晚,好像是你強上了爺!”
289.9萬字8.25 248977 -
完結4104 章

清穿之嬌養皇妃
擁有傾國傾城之貌的沐瑾回府了,四爺後院眾人無不虎視眈眈:來了,實力爭寵的來了! 沐瑾很苦逼,爭寵幹什麼?多耽誤種田!她並不想回來啊,福晉心思深沉,李側福晉咄咄逼人,宋格格是個笑麵虎,耿格格是個假天真,她空有美貌其實地位低、沒靠山、兩眼一抹黑!好想哭,想回莊子種田! 眾人氣憤:信你才怪!你個心機女,才回來多久啊,自己算算跟爺‘偶遇’多少
363.1萬字8 139286 -
連載3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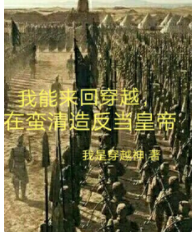
我能來回穿越,在蠻清造反當皇帝
殺伐果斷+冷血+爭霸文+造反+不圣母本書主角每隔一段時間會搞大清洗行動,每次屠殺幾百名上千名不聽話有叛心的手下將領們。對外進行斬首行動。主角建立帝國后,會大清洗
65.6萬字8.33 8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