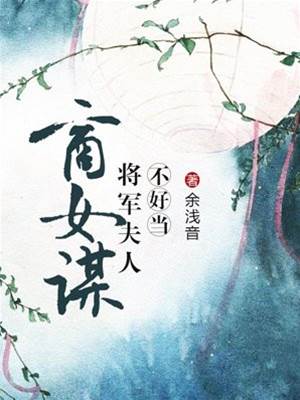《和病嬌綁定之后》 第95章 至此纏綿
他彎下腰。
一片昏暗里,夏蒹看不清他的容,他垂著頭,臉被墨發擋住,一點點彎下腰,將臉上去,上的腳面。
夏蒹皺起眉,“裴……裴觀燭?”
“嗯,”他的聲音顯得極為安靜,像是不知何時,他從某得來了巨大的安全,今夜持續已久的緒不穩從他上爬走了,他臉被墨發遮擋,夏蒹卻莫名覺得,他如今一定是笑著的,而且笑的不同于往常,“我在,夏蒹。”
他說著話,夏蒹覺腳面有屬于他的發掃過,夏蒹忍不住蜷起腳趾。
“夏蒹,”抱著腳跟的人忽然垂著頭發停住作,他一不,只低垂著滿頭長發,“夏蒹也會覺得,你和我是上天注定的嗎?”
會。
夏蒹張了下。
卻本沒資格說這個會。
哪怕,大抵比裴觀燭更認為們二人是上天注定的。
但是這樣沉重的話語,如果是從的里說出來,裴觀燭一定會無法理解。
正當躊躇不前,細細的親吻覆上腳面,年的聲音從垂下來的墨發里,悶悶的浮出來。
“夏蒹肯定不會這樣覺得,”他一邊說著,一邊彎著子,一下又一下親吻的腳面,腳踝,和那條細細的黑腳踝繩子,“只有我一人會覺得,終于解了,”他抬起頭,墨發凌,隔著暗淡的宮燈,夏蒹看到他眼眶泛紅的一雙眼,著難以言喻的笑臉,“只有我一人覺得解,那就足夠了。”
“你……”夏蒹看著他的樣子,微微愣住,正要說你怎麼了,便聽他問。
“夏蒹,你恨我嗎?”
“我怎麼會恨你?”
“是嗎,”裴觀燭顯得有些泛紅的眸子看著,“不恨我,那是我嗎?”
Advertisement
“我……”夏蒹微微皺起眉,“我不討厭你,裴觀燭,這個詞太沉重了,我不想騙你,我也騙不過你,我只能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他漆黑的眼珠一不的盯著,蒼白纖瘦的指骨,著腳踝上的黑繩結。
“夏蒹我嗎?”
“我都說了,我很喜歡你,這個詞太沉重了。”
“為何?為何于夏蒹而言便是沉重?”他手往前,在的上,像一條蛇纏著的上來,在跟前。
氣息織,夏蒹微微起眼,對上他的視線,這大抵是夏蒹第一次看到裴觀燭這樣狼狽,比起上次在籠子里找到他時還要狼狽,他頭發全都散落下來,紅發帶松松掉到發尾,臉上像是黏著淚,發一一在他蒼白的臉頰上,他像個鬼一樣,面無表的用漆黑的眼珠看著。
“……本就是很沉重。”夏蒹看著他過分濃黑的眼珠,心上蔓出一陣莫名,正要轉過頭回避,忽然覺有輕輕地重量上。
年一只手扶著,坐的很直,他微微瞇起眼,泛紅的勾起一個笑,“夏蒹不我,是不是因為晚明相貌丑陋?”
“哈——唔!”
聲音被年吞腹中。
近乎啃食般的糾纏,不管是聲音,舌頭,唾,思緒,全都被他吃了下去,夏蒹大腦開始缺氧,手錘他又推他,但都被他著,直到眼睛被他的手掌住,視線一片漆黑,又一亮,夏蒹還沒來得及看清綁住眼睛的是什麼東西,便覺年在腦后用布條系好了結,全世界都黑了。
“好可。”
視線漆黑,夏蒹頭轉了一下,覺年的聲音清晰傳耳,冰涼的指頭著的下,年抱住,“夏蒹好可。”
Advertisement
“你這是做什麼!”
夏蒹皺起眉,正要抬起手去把綁著眼睛的布條放下來,便覺手被裴觀燭的抓住,用力之大,夏蒹竟然都覺到了一陣尖銳的痛。
“嘶!”
“不準,”他的聲音很溫,事實上,裴觀燭不管何時聲音都是這樣的,所以蒙上視線之后,夏蒹本就分不清他當下緒,“夏蒹若是,我會很難,不知會做出什麼。”
夏蒹微頓,漸漸停下力氣。
手腕被他扶著,挲而過,“好可憐,很痛吧?對不起,小暑。”
“你這樣好可,”他的手放到的臉上,“好想讓夏蒹一生都這樣,如果夏蒹眼盲,或者是沒有,那該有多好?那樣的話,我也不用總是怕夏蒹會跑出去了。”
他聲音越來越低,像是帶著哽咽,“我好難過……”
有淚水打上的手背。
他一下一下,用臉蹭著的手背,“我好難過,因為夏蒹不是這樣,但我又好開心,因為如今,夏蒹與眼盲或是沒有,其實都并無太大差別了,但是……但是,我又好害怕,夏蒹,我好怕,我怕你恨我,一生都不會我了,我好怕,真的,因為其實,我真的很想讓夏蒹我,夏蒹能知道嗎……”
夏蒹子有些僵,一不,總覺如今若是打斷了他,就發掘不出更多東西了,但是裴觀燭給覺就像是忽然犯起病來,說的都是莫名其妙的話。
什麼,與眼盲或者沒有,都沒有太大差別了?
是因為,裴觀燭將的眼睛給蒙上了嗎?
年的聲音,斷斷續續傳耳道里。
“好想要夏蒹我,好想要,”他一下一下,蹭著的手,“為何會這樣想要呢?我真的想不明白,明明能確定夏蒹會一生在我邊就足夠了,但是,我其實不想犯和父親一樣的錯誤,我一定要夏蒹在死之前,不,我要夏蒹我才行,永遠都我才行。”
Advertisement
“父親我阿母,很,很,因為我父親覺得,阿母很干凈,是這世上最干凈的人,父親本以為我也會是像我阿母那樣干凈的人,因為我是我阿母的孩子,但我不是,我和父親是一樣的,所以父親才會不我,阿母也會不我,”年的睫蹭著手背的皮,“但其實,我覺得們也十分污穢,因為夏蒹才是最干凈的,他們,父親,還有阿母,他們那兩個無知又自大上不得臺面的蠢貨,是因為沒有見過夏蒹,才會以為癡傻才是最干凈的,但明明,干凈的理所應當是夏蒹才對。”
“呵呵呵……”他低低笑起來,“父親他好蠢,又好笨,真應該把他的頭砍下來,留著那樣不比豬驢聰明分毫的頭顱本就毫無用。”
“夏蒹好可。”呼吸打到的邊,他十分溫的,用舌去描繪,夏蒹呼吸發,忽然一陣尖銳的刺痛襲來,夏蒹唔一聲,腥味冒出來,淚水染了布帶,夏蒹抬起手想去捂住被咬破流的角,便覺手掌被他的膝蓋住,后知后覺的恐懼一層一層爬上的后背,“你……你要做什麼啊?”
“我?”他親昵的蹭著的角,說著話,慢慢坐直了,“我要報答夏蒹。”
“什麼意思?”
沒人說話。
但夏蒹能覺到他正看著。
一直被住的右手手背驀的一松,手被他抓著,指腹上一片溫。
年的息上指尖,的覺爬上來,夏蒹頭皮發麻,視線一片漆黑,無限放大,第一次覺到了未知的恐懼,驚怕的嗓音都發起,“裴!裴觀燭!”
“唔……債。”他含糊不清的回話,夏蒹手腕被他抓著,拼命往一旁躲,一片漆黑里,夏蒹到他的臉,灼熱般的滾燙。
“……小暑,我的,唔,小暑。”
息聲散在耳邊,頸側發,夏蒹子發起,涼氣蔓上肩頭,外裳層層疊疊堆到手邊,夏蒹輕呼出聲,又被他用手捂住了。
“雖然很想和夏蒹相親,”黑暗里,夏蒹覺他臉靠上脖頸,檀香味近乎鋪天蓋地般散過來,“但若是一時放縱,夏蒹之后肯定會討厭我,所以今夜,晚明只做能給夏蒹帶來舒服的事。”
還沒從與他的親回神。
夏蒹腦勺上枕靠,年溫熱的呼吸聲埋下來,他冰涼若蛛般的發一縷縷落下來,是想象,夏蒹都能覺出他如今定是極為麗。
但埋在心口的呼吸卻往下,空氣的涼散下來,夏蒹“呀!”的尖一聲,沒想他竟然這麼大的膽子,被解放的一只手正要往下去推他,扯過一邊散落的襦,便被他抓住了手腕。
“不怕,夏蒹,”他聲音帶著,“我也,我也不會穿的,夏蒹不穿,那晚明……也不會穿,不要……害。”
料聲,夏蒹到了他的皮,心中的恐懼也沒那麼大了。
“夏蒹,”他輕輕念著的名字,“夏蒹……夏蒹……”
夏蒹微頓,手心到他發燙的臉,連著脖頸,就連耳垂上應該冰涼的耳珰,也染上了溫熱。
猜你喜歡
-
完結827 章
鬼王嗜寵:逆天小毒妃
南宮離,二十一世紀藥師世家之女,采藥喪命,魂穿異界大陸,附身同名同姓少女身上。 什麼,此女廢柴,懦弱無能?沒關係,左手《丹毒典》,右手通天塔,毒丹在手,巨塔在側,誰若囂張,讓誰遭殃。 尼瑪,太子悔婚,轉賜廢物王爺?姐要逆天,虐死你們這群渣。 廢柴變天才,懦女變毒女,鬼王守護,遍走天下!
213.7萬字8 28501 -
完結474 章

姑娘今生不行善
盛京人人都說沛國公府的薑莞被三殿下退婚之後變了個人,從前冠絕京華的閨秀典範突然成了人人談之變色的小惡女,偏在二殿下面前扭捏作態,嬌羞緊張。 盛京百姓:懂了,故意氣三殿下的。
94.2萬字8 12271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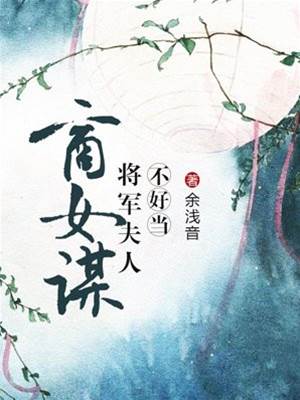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5772 -
完結322 章

霓裳帳暖
西涼戰敗,施霓成了西涼王精心挑選要獻給大梁皇族的美人貢禮。 她美得絕色,至極妖媚,初來上京便引得衆皇子的爭相競逐,偏偏,皇帝把她賞給了遠在北防邊境,戍守疆域的鎮國大將軍,霍厭。 衆人皆知霍厭嗜武成癡,不近美色,一時間,人們紛紛唏噓哀嘆美人時運不濟,竟被送給了那不解風情的粗人。 一開始,霍厭確是對她視而不見。 他在書房練字,施霓殷勤伺候在旁,他睨了眼她身上透豔的異服,語氣沉冷,“穿好衣服,露成這樣像什麼樣子。” 施霓滿目委屈,那就是她尋常的衣飾。 後來,同樣是那間書房,霍厭不再練字改爲作畫,他將施霓放躺到檀木面案,於冰肌雪膚之上,點硯落墨。 原來,他要她以身作他的畫紙。
51.6萬字8 138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