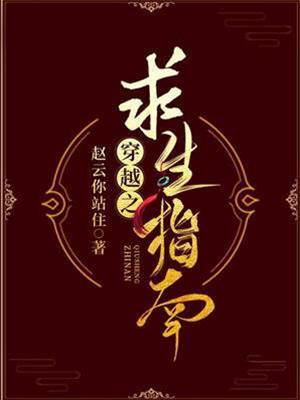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三十六陂春水》 第24章 瑯玡(十二)、長安(一)
齊凌笑了笑,重新執起筆,轉過頭不看,隨口問:“那你準備怎麼謝我?”
朱晏亭沒有料到他真的會要求謝禮,著實為難,然而話已說了,只得搜腸刮肚,邊想邊說:“我……有一隨侯珠,徑寸大小,前后可照一丈遠。”
齊凌黑了黑臉:“如若沒有記錯,這顆珠子是西垂殿的吧?你就準備拿朕的東西送回來送朕?”
朱晏亭真難住了,要放在以前,荊楚之珍,奇異之玩,云夢之寶,無論如何也尋得出幾樣可以送給皇帝的禮品。
然而焚燒丹鸞臺,孤而來,上所攜真正屬于的,除了皇帝的納采之禮外,便只有一張長公主以前狩獵用的鴟紋雕弓。
雕弓……
圍獵,天馬。
忽然想到了什麼。
目中浮現出火跳躍一樣的喜悅,笑道:“臣就攜我母留下的鴟紋雕弓,為陛下獵一腋狐裘,獻給陛下如何?”
的提議讓齊凌也詫異了一下:“你還會弓馬?”
“只會皮,然我心拳拳,愿竭力一試,以悅陛下。”朱晏亭說得很謙虛。
齊凌本就極好狩獵,這個提議正中了他的下懷,當即定下,等祭祀五方天帝的祭奠過后,起駕回長安之前,帶朱晏亭去扶桑苑圍獵一次。
算算日子,就在三日之后。
……
元初三年的五帝祭祀是齊凌登基之后首次祭祀五帝,毗鄰東海,聲勢浩大。
占卜、出行、祭祀、宣召、垂訓。
皇帝需要足足忙碌兩日,腳不沾地,不在蒼梧臺。
借此機會,朱晏亭在早上給太后問安之際,邀請同來問安的臨淄王后到西垂殿小坐。
西垂殿有庭,木華葳蕤,奇鳥引頸,嘀啾直鳴,庭中高屋建瓴,可從西側瞰整個蒼梧臺,萬千屋脊,紛紜過客,收眼底。
Advertisement
朱晏亭與臨淄王后去履坐葦席上,迎一蓬清風。
“之前王后所有求于我,是什麼事?”
臨淄王后朝側招了招手,道:“若阿,過來。”
一綠黃裳的貌子從跟隨臨淄王后的行獵中走來,對朱晏亭行禮。
如雪,舉止溫文,一雙晶瑩剔的杏目,邊一笑就是一對兒梨渦。
臨淄王后道:“這是我的侄,吳若阿,上次你見過的。”
朱晏亭著夸贊了兩句,然后目含笑意,靜靜盯著臨淄王后瞧。
臨淄王后也不瞞,附耳過去,在耳邊悄聲說:“我為此子,謀一夫人之位。可現在還不是時候,往后還需要你多照應。”
朱晏亭頓時了然,下頜輕點——先前到蘄年殿,還奇怪為何諸王都有獻,這次東巡的東道國臨淄王卻毫無靜。
想來臨淄王已敏銳察覺到這次世家獻,諸王手,惹得皇帝不大開心。
為了不讓吳若阿還未見皇帝就留下不好的觀,因此延后了送宮的計劃。
“王后曾助我于水火之中,照應阿妹,我義不容辭。”朱晏亭輕輕說,的聲音和風聲纏著,顯得有些縹緲“然我是一孤,外無家族所傍,無兄弟可倚,危若風中之燭,水中之冰。封了皇后,也是看著好看,聽著好聽。阿妹若來,前路千難萬險,可要想好。”
臨淄王后揮手令若阿退下,等只剩二人,手覆住冰涼的手:“傻孩子,往后臨淄就是你的娘家,也是你的后盾,你怕什麼?”
朱晏亭笑笑的不說話。
王后說完,自己也覺失言,訕訕把手放了回去。
沒有緣和姻親聯系的“娘家”,注定只能停留在口頭上,起不到半點作用。
Advertisement
王后復一深思,乍然心驚,朱晏亭世如此,竟然真的是孤一個人,連一個可以和自家結親的兄弟都沒有。
以如此煢煢之,登上至高座,恐怕是禍非福,斷不能久。
朱晏亭見眉目含愁,是真的為自己擔憂,心下一暖,安道:“舅母放心,這是我自己所求,雖死無悔。”
臨淄王后環視富麗堂皇的蒼梧臺,再顧遠熙熙攘攘瑯玡城:“我也舍不得若阿,可我不得不送去。就算是為了臨淄不像章華那樣……”
今時今日的臨淄,和當年的章華,何其相像。
諸王當前所慮,又何嘗不是唯恐哪一日,自己變下一個章華國。
臨淄王后恐朱晏亭傷,匆忙轉移了話題。
朱晏亭倒不以為意:“現下還有一件棘手的事,想求舅母幫忙。”
臨淄王后托之與,此時對自然是所求必應,連忙答應。
朱晏亭附耳過去,小聲說了幾句話,王后眼眸驟然睜大,驚詫得久久說不說話,半晌,方十分勉強的點了點頭。
……
皇帝畢竟是東巡途中,所攜守衛、宮人有限,加上祭祀盛大,調了許多侍,蒼梧臺留下的,大多是臨淄王的人。
因此臨淄王后比較好安排,這日趁太后在午歇之際,悄悄將換了裝的朱晏亭接了出來。
一駕深覆重帷的車,穿衢過巷,來到瑯玡大獄。
早有人囑咐過,不問也查,任車上的人直獄中,停在其中一間前。
隔柱而觀,斗室里坐著一個背脊直的青年人,著囚服,正是李弈。
朱晏亭試了一個眼,立刻有人打開了獄門上的鎖鏈。
“喀嚓”金屬相之聲,將靠壁上假寐的李弈驚醒過來,一抬頭,看見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在此看到的人,結一滾,沙啞聲音喚道:“小殿下?”
Advertisement
朱晏亭上下打量他一眼,見他沒有刑的跡象,神尚佳,稍稍松了一口氣。
無聲而,在他前三兩步,蹲下了:“李將軍,你可還好?”
李弈見著宮人,雙眉蹙:“你怎麼會來瑯玡,這是……”
朱晏亭一指比在際,輕輕“噓”了一聲,低聲道:“多的你先不要問,我有幾句話要囑咐你。”
李弈縱然滿腹擔憂,不知究竟做了什麼,然而在安靜的目下,問不出話,只靜靜聽著說。
“我現在一切都好,不會嫁給吳儷,我會嫁給陛下。”
說出這話的瞬間,李弈眼中陡然掠過驚瀾,這個結果,出人意表,卻又在預料之中。
“我會想辦法救你出去,不過,你恐怕回不去章華了。”
李弈輕輕道:“好”
朱晏亭從懷里取出了一個青的香囊,香囊上蕭蕭繡著一支綠竹,里頭鼓囊囊裝著什麼事。
“這里面,裝著一點香草,還有瑯玡百里巷的門牌,劉壁等在那里,你若得釋,去找他們。”
李弈將香囊在手里,不說話。
朱晏亭切切叮囑:“將它妥善安放,不要離,也不要被人發現。”
李弈點了點頭:“好。”
朱晏亭時間不多,囑咐完就站起,告辭離去,才到門邊,聽李弈喚:“小殿下?”
疑轉回頭。
牢籠里窗孔很窄小,細細的一道,分割李弈沾了污穢的英面容,朗眉軒之下,雙目定定:“弈愿追隨小殿下,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
三日之后,天朗氣清,經一場攜狂風驟雨的春雷之后,瑯玡被蒼蒼天所照,草濃郁,萬逐漸茂。
皇帝攜朱晏亭,于扶桑苑圍獵。
這一次由于的加,沒有邀請諸王,也沒有調臨淄王的兵馬,調羽林郎護衛,遠近漸次以帷幕遮擋。
朱晏亭著輕便胡服,執一把樣式古樸的鴟紋雕弓,從車上下來。
期門郎立即給牽來一匹看起來溫順聽話的獅子驄。
抬目一看,不遠齊凌也換了便裝,引馬而來。
他的馬乃一通黝黑的玄駒,勁馬金羈,目如琥珀,足踏寒鐵。
齊凌翻而上,一手執弓,一手牽轡,笑目著:“狐最狡,機敏萬分,擅流竄山林,你可莫要撞到樹上去。”
朱晏亭的騎是跟著李弈學的,六藝中唯好此道,勤于練習,平素也引以自矜。聽皇帝懷疑會撞到樹上,當下作利索翻上馬,猛一夾馬背,策馬走在了前方。
一連串的作英姿颯爽,練漂亮,兼之胡服收,不若平常寬袍大袖,直接勾勒出腰之間的起伏弧線,越發顯得姿態姽婳嫻靜。
齊凌在馬后不遠,看見高聳發髻之畔,出直如玉琢的耳朵和側頸,目停頓了一瞬,不妨正巧被回眸顧來,撞到一。
目中有些疑,似乎對他的觀察到怪異:“陛下,可否與臣一試騎?”
齊凌收轉目,直視向前,擎韁笑道:“朕這匹馬與你賽,未免太欺負你。你可去馬場再挑選一匹。”
朱晏亭沉思片刻,道:“我甚慕烏孫國上貢的天馬,陛下肯割麼?”
“一匹馬而已,你若喜歡,便贈給你。”齊凌吩咐期門郎去牽。
然而那期門郎聞此言卻嚇得面發白,猶疑四顧,撲通一下跪倒在地。
皇帝輕輕一手韁,將他的坐騎止住:“怎麼了?”
朱晏亭也一臉迷的駐馬看來。
那期門郎戰戰兢兢道:“回陛下的話,烏孫國的貢馬養在苑中,我等數人照料,不敢有片刻輕忽。然而不知是否天馬跋山涉水,遠道而來,水土不慣之故,數日不吃不喝,神懨懨,恐怕不宜給貴人乘騎。”
齊凌面有些不虞,令他將馬牽來。
那匹形若蛟龍、震懾來客、名長安的天馬,再度牽至齊凌面前時,已不能辨其威武雄壯之態,馬目委頓,一原本像烈烈火燒的凌張刺著,顯得疲憊不堪。
齊凌向來馬,更何況這是烏孫國進貢的馬,有西邦臣服的寓意,故而十分重視,當下傳喚負責養馬的員來問。
那人也答不出個所以然,只說傳了醫,換著法子,甚至遠從百里之外的冀南運來草料,然而無論怎樣嘗試,這馬都不肯吃東西。
皇帝當即有些慍怒,傳喚太仆謝誼,令他親自來解釋。
期門郎眼見龍生怒,戰戰兢兢,聲道:“臣,聽過一個說法,天馬頗認降服它的第一個人,臣斗膽求陛下傳喚降馬猛士,令他一試?或……或有奇效。”
齊凌聽見這話,方想起來,李弈還被關在牢籠里,沒有決,也沒有開釋。
他沉片刻,下意識將目轉向了朱晏亭。
后者也正靜靜看著他,表如常,看不出什麼緒。
他角微微一揚,吩咐執金吾:“傳李弈來。”
約莫過了一盞茶的時間,幾名衛士押解李弈赴馬場。他著赭,因為要面見皇帝,凈了面,頭發也收冠中,不復狼狽之態。
李弈神還算好,下拜叩首,聲音朗朗:“罪臣叩見陛下。”
齊凌目視天馬,對他道:“去看看,若你能令馬吃草,就算將功抵過,朕就放了你。”
李弈應聲稱是,走上前去。
怪異的是,李弈一靠近,病懨懨的天馬忽然打了一個響鼻,而后,將馬首湊到了他的上。
李弈與此馬結緣頗深,降服它時也極喜它威武烈,手拍馬頸,輕馬鬃。熱乎乎的氣息,噴在他脖頸旁。
李弈牽著馬走了幾步,本懶洋洋不彈的天馬勉強曲蹄跟著他走,將鼻湊到他赭廣袖之間,頂著他的手,十分親昵。
李弈再攜草喂它,馬果一張口,吃了下去。
期門郎目瞪口呆看著這一幕,不由稱奇。
齊凌頗信讖緯之,視此馬為西域邦服的征兆。
最初,李弈降服了它,雖然他的份不很令自己滿意,但勇猛和忠義還是令他生出才之心,故而此人犯下大錯,也未能直接斬殺。
現在,天馬不吃不喝,偏認這個主,肯湊在他邊,親昵溫順。
皇帝又想起,李延照曾經對他說,自己和李弈曾經兩人中一匹馬,一邊金箭,一邊飛劍,剛好對應一。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休夫
挺著六月的身孕盼來回家的丈夫,卻沒想到,丈夫竟然帶著野女人以及野女人肚子裡的野種一起回來了!「這是海棠,我想收她為妾,給她一個名分。」顧靖風手牽著野女人海棠,對著挺著大肚的沈輕舞淺聲開口。話音一落,吃了沈輕舞兩個巴掌,以及一頓的怒罵的顧靖風大怒,厲聲道「沈輕舞,你別太過分,當真以為我不敢休了你。」「好啊,現在就寫休書,我讓大夫開落胎葯。現在不是你要休妻,而是我沈輕舞,要休夫!」
65.8萬字8 77347 -
完結453 章

鳳回鸞
世人皆知太子長安資質愚鈍朝臣們等著他被廢;繼後口蜜腹劍,暗害無數。他原以為,這一生要單槍為營,孤單到白頭不曾想,父皇賜婚,還是裴家嬌女。那日刑場上,裴悅戎裝束發,策馬踏雪而來:“李長安,我來帶你回家!”.自此,不能忘,不願忘。
78.4萬字8 14187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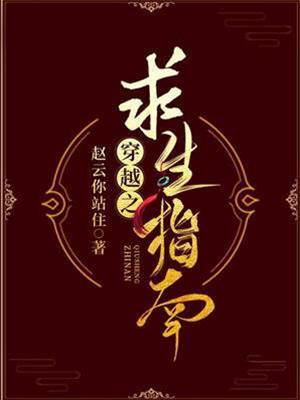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連載1307 章

家侄崇禎,打造大明日不落
魂穿大明,把崇禎皇帝誤認作侄兒,從此化身護侄狂魔!有個叫東林黨的幫派,欺辱我侄兒,侵占我侄兒的家產? 殺了領頭的,滅了這鳥幫派! 一個叫李闖的郵遞員,逼我侄兒上吊? 反了他,看叔父抽他丫的滿地找牙! 通古斯野人殺我侄兒的人,還要奪我侄兒的家業? 侄兒莫怕,叔父幫你滅他們一族! 崇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切都不存在的,朕有皇叔云逍,可只手補天! 李闖:若非妖道云逍,我早已占據大明江山......阿彌陀佛,施主賞點香油錢吧! 皇太極:妖人云逍,屠我族人,我與你不共戴天!
233.1萬字8.18 231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