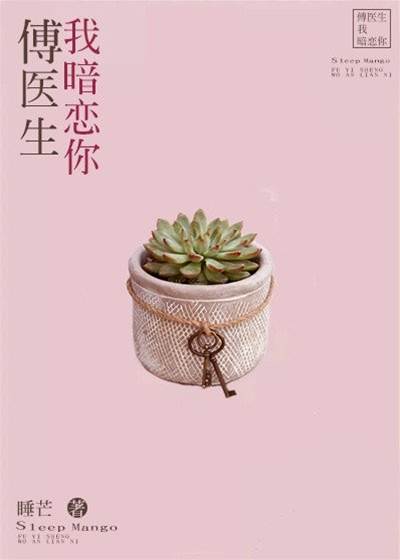《伏鷹》 第48章 坦白
蘇渺喜歡他頭發,宛如貓咪般、蹭了蹭他的手:“因為我小學的時候,班級里有個生念懿,很漂亮,每天都會穿不一樣的可小子,的名字筆畫很復雜,班上絕大多數同學都不認識這個字,但我覺得這個名字很特別。有這樣的名字的生,爸爸媽媽一定特別。不像我的名字,普通又一般…”
遲鷹記得蘇渺第一次對他自我介紹:“蘇渺,渺小的渺。”
“我媽媽給我取這個名字,大概也是因為希我不要好高騖遠,認清自己的份。”
他修長漂亮的指尖勾起了的下頜,“不是渺小的渺,是渺渺兮余懷,人兮天一方。”
蘇渺聽到這句話,憋了幾秒,還是忍不住笑了起來,連忙手捂住了緋紅的臉。
渺渺兮余懷,人兮天一方。
十七歲的,生平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贊譽。
Advertisement
遲鷹在這方面總有本事,能讓罷不能、心向往之,喜歡得不能自己。
蘇渺捂著臉,過指去看他。
他倒也被小姑娘的反應惹笑了,眼角沾染了愉悅,忍不住湊近,挲的下頜:“你怎麼這麼喜歡害。”
“哎呀!”
“不過我喜歡看你害的樣子。”
蘇渺平復了心,正襟危坐,評價道:“遲鷹,你太會花言巧語了,你對生都這樣嗎?”
遲鷹一本正經道:“你見我對哪個生這樣過。”
“沒有安全。”
“我邊一個孩都沒有,不像某人,邊又是什麼秦什麼路的…”
蘇渺故意道:“啊,說起來,路興北也在京城,要不要約他見見呢。”
他用機械手臂敲了敲的腦袋:“你敢。”
……
窗外雪紛紛,房間里溫暖又舒適,蘇渺上搭著薄薄的小毯,在他的電腦桌前看了一會兒《蠟筆小新》。
Advertisement
冒藥的藥勁兒上來,蘇渺昏昏睡,沒多久便睡死了過去。
這是來京城睡得最好的一個覺,在屬于他的那種悉又安心的氣息里,居然也沒有認床。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次日的清晨,溫煦的過窗梢灑在了的臉上。
眼睫微微了,蘇渺懶洋洋地坐了起來,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深藍的大床上,手機擱在床柜邊充著電,旁邊還有一杯水,尚有余溫。
了凌的腦袋,環顧四周。
房間陌生,整潔而規矩,空氣中又著悉的氣息。
下意識地想到,這里只能是遲鷹的臥房。
蘇渺看著自己上這件小,子也沒有,就這樣湊合著睡了一整夜。
局促地坐起,匆匆走出了房間,四下里尋找著年的影——
“遲鷹?”
“遲鷹。”
院子里的積雪尚未融化,年穿著單薄的黑,蹲在溪邊看魚,后背脊骨的廓顯著,有種野蠻生長的勁兒。
Advertisement
“醒了。”
“唔,我昨晚…睡得太死了。”蘇渺走到他邊,揪住了他的袖子。
“知道,跟豬一樣,推都推不醒。”
“我睡了你的床,那你呢?”
“當然是你邊。”
“啊!”
看著驀然脹紅的臉頰,遲鷹忍不住了,笑了,“逗你的,我睡沙發。”
蘇渺低聲說:“不好意思哦。”
遲鷹領著來到了溪畔的小木桌邊:“吃早飯了。”
發現小桌上擺放著一碗新鮮的冰,在下閃著水潤明的澤,上面撒著花生米、葡萄干、還有芝麻…
驚訝地回頭:“遲鷹,你做的?”
“不然,難不是秦斯?”
“你又提什麼秦斯啊,關他什麼事。”
“也是。”遲鷹將紅糖水緩緩灑在冰碗里,抬起下頜,得意地著,“什麼秦的,他就不會做冰。”
猜你喜歡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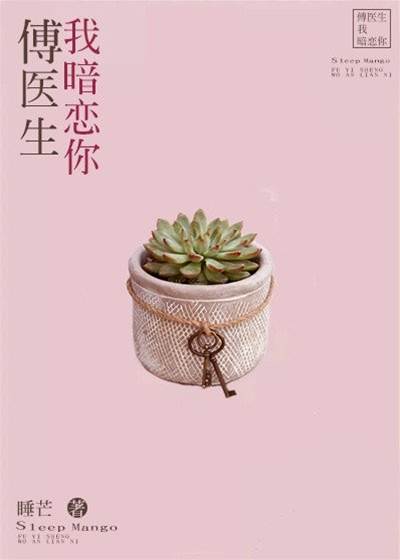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91 -
完結2391 章

南風過境,你我皆過客
沈姝自詡擁有一手好牌,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會把這手好牌打得稀爛。墮胎,容貌被毀,事業一塌糊塗,聲名狼藉。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這樣,大概是因為傅慎言的出現吧!畢竟,愛情真的能毀掉一個女人的一生。
217.2萬字8 16205 -
完結142 章

見色起意,嬌嬌小美人被霸總纏上
【蓄謀已久 見色起意 先婚後愛 雙潔】【嬌軟美人vs腹黑霸總】溫絮和江衍第一次見麵,是在“迷度”一家高級會所,氣氛曖昧。—溫家一夜破產,她紅著眼眶,懇求,“江先生,請你幫幫我。”俊美的男人直接將溫絮逼到角落,手指似有若無擦過她那嬌嫩的紅唇,循循善誘,“400億可不是小數目,我是個商人,溫小姐該明白虧本的生意我不會做。”溫絮楚楚可憐,“那要怎麼才能幫忙?”江衍眸光漆黑,眼裏占有欲及其強烈,他把女人直接摟進懷裏,嗓音低沉,“留在我身邊,做我的夫人。”—江衍這人,天性高冷,與誰都不屑一顧。在沒碰到白月光之前,宛如高山白雪,讓人不敢染指。“你之前明明很高冷的,現在怎麼這樣了?”男人在溫絮的鼻尖啜了一口,目光溫柔繾綣,“乖,在自家老婆麵前,不需要端著。”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蓄謀已久
26.9萬字8 22135 -
完結835 章

人性禁島
春節沒買到票,我坐黑車回家,沒有想到車上的女人一直盯著我看,我想報警……【深扒】春節搭錯車後失聯恐怖真相,黑車不要亂坐,因為黑的不僅僅是錢,還有你的命!【2o15年末懸疑靈異之作】黑車微博求關注:eibo.com/u/5484588718(海棠花未眠本尊)客戶端如果現斷更的,可能是客戶端延時,可以站內搜索人性禁島,或者海棠,到封麵後,把已追取消,變成追書,再次點追書,章節也會出現。上架之後,保底三更。(不定時爆)兩個玉佩加一更,皇冠加六更個人QQ:3o62985856(海棠花未眠)作者勿擾,一般不閑聊啊!求金鑽,追書,求推薦票,求注冊,求一切。
198.6萬字8 25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