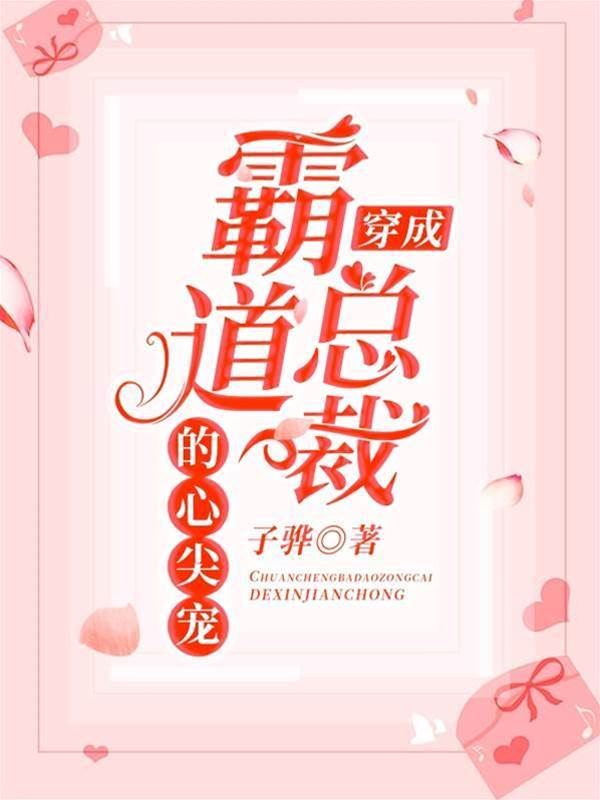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我家賢妻太薄情》 第42章 第 42 章
玉溪頗有些失落, 一腔事非長短沒說,恨不得半夜去找子清嘮一兩句。
但薛宜寧要睡,還得守夜, 只好先回床上去躺著。
要是明天將軍說不納夏柳兒為妾就好了,玉溪在床上想。
等到第二天, 才是清晨,薛宜寧剛梳洗, 何媽媽就從外面探聽到了消息, 等不及來稟報。
夏柳兒連夜就被送走了,長生送的,邊還跟了個婆子,后來才知, 夏柳兒要去郊外一小院子里住了, 長生和那婆子在跟前侍候,再不會回府上了,自然也沒有進門這回事。
玉溪早就等了一夜的消息, 此時聽到,不由就振道:“真是這樣?連長生也一起走了?”
何媽肯定道:“千真萬確, 和正堂里出來的消息。說是昨夜夏姑娘落水后,將軍先見了長生, 然后又見了夏姑娘,說的什麼不知道, 反正后面就把他們送走了,絕不會再回來了。今日前院的阿貴就去和正堂侍候了,替的是長生的位置。”
“怎麼這麼突然呢?難不是因為落水這事?”玉溪問得疑, 臉上卻是眉開眼笑。
何媽媽也是帶著笑, 然后回:“這就不知道了, 興許是?”
子清倒比倆沉得住氣一些,說道:“這事旁人要議論,就讓他們議論去,我們聽著就好了,別跟著去說閑話。”
何媽媽連連點頭:“我知道的,我都是聽,絕不說話。”
待何媽媽走后,子清才奇怪道:“倒沒想到將軍會這般置,夏姑娘此時想必是后悔夜間出來了。”
“長生怕是也后悔去救吧,也沒辦法,了夜,除了長生和將軍,還有誰能去救人?怪運氣不好,撞見的是長生,不是將軍。”玉溪說。
Advertisement
薛宜寧看玉溪一眼,若有所思。
覺得,以駱晉云對夏柳兒的分,不至于如此冷刻薄。
真的是因為夏柳兒被長生救,失了清白嗎?
駱晉云并不像這麼認真古板的人。
一定是有其他什麼事,到了他的逆鱗,讓他不能容忍。
種種細枝末節,若是認真去推敲,大約也能琢磨出真相來,只是懶得去費這個神。
走了便走了吧,那夏柳兒看著弱可憐,卻并不安分,總弄出些這樣那樣的事來。
但愿日后駱晉云再納小,能尋個老實本分一些的,讓后院清靜兩日。
駱家后院一整天就在議論夏柳兒和長生的事,閑話的同時,所有人都警醒了一些,都道夫人仁善,輕易不會趕人出去,這將軍卻是個不留面的,連最寵的人和最重的心腹小廝都能說趕走就趕走,更別提其他人。
二房黃翠玉正坐月子,一邊喝著銀耳羹,一邊聽邊媽媽說著外面的事。
那媽媽將這事說得繪聲繪,黃翠玉開始還覺得有意思,可惜自己沒看著這熱鬧,回頭又想想,不由就難起來。
同是駱家的媳婦,薛宜寧那邊都比這里好,連住的院子,那邊都金福,而這里則什麼銀福。
唯一比薛宜寧強的,就是生了兩個兒子了,薛宜寧進門兩年,還一個屁都沒有。
第二樁更得意的,就是駱晉風那傻子不敢納個小的到邊,而大哥則帶了個滴滴的良家回來。
那人還不安分,攪得金福院那邊了許多氣,都知道。
就因為這兩樁,這幾個月在薛宜寧面前腰桿都直了不。
還等著之后那姓夏的進門,薛宜寧天天獨守空房,眼看著姓夏的生了兒子生兒,自己還得強歡笑,那時才算真正氣順了。
Advertisement
沒想到這下弄的,夏柳兒竟然悄不作聲的,就被趕走了。
還是大哥趕走的。
他不是喜歡那夏柳兒的麼?怎麼就送走了?
還聽說他最近竟開始在金福院那邊過夜了。
這樣下去,回頭薛宜再懷上了,不是又死死住了?
黃翠玉越想越煩躁,朝那媽媽道:“行了,別說了,多大點事,早就知道了!”
媽媽連忙住口,見心不好,便說道:“那……那我先下去忙了。”
說著便出了屋。
黃翠玉攪了幾下碗里面的銀耳,問丫鬟阿香:“之前不是和燕窩一起燉的麼?怎麼今天只有銀耳了?”
阿香連忙回說:“那燕窩是之前大夫人那邊送過來的,說給夫人補子,本來也沒多,到昨日就燉完了,只有銀耳了。”
黃翠玉心中不喜,抱怨:“我坐月子還是坐月子,要喝點燕窩還是得送!”
阿香低聲道:“那燕窩好像是大夫人娘家送來的,老夫人節儉慣了,府上除了待客,一般不會備這個。”
黃翠玉一把扔了調羹:“你這什麼意思?是說我要喝就讓我娘家送?說我娘家不如薛家?”
阿香連忙認錯:“我沒有,夫人,我沒那個意思,我就是說……就是說……沒有燕窩了,這銀耳也好的……”
“好好好,好個屁,你給我滾,又丑又笨,我看見就煩!”
阿香紅了眼睛,垂著淚立刻就退了出去。
黃翠玉心想,金福院那玉溪子清的,肯定不會這麼沒眼力見,說話惹心煩。
一直煩著,栓兒下午又一直吵鬧,惹得人不得安寧,便越發沒有好臉。
等到傍晚,聽見駱晉風進了院,卻半天都沒進房來,便問阿香,“二爺在做什麼?”
Advertisement
因坐月子,駱晉風按習俗不能在房里過夜,搬去了廂房住,但白日來看看卻是可以的,此時他回府,這麼久都沒說來看看,黃翠玉已有些不高興。
阿香知道帶著氣,小心回答:“二爺回來時好像從哪家酒樓帶了只烤蹄髈回來,大概是怕薰著夫人,正在房里喝酒。”
黃翠玉冷笑:“你去把他給我過來。”
阿香不敢耽誤,連忙就出去人。
沒一會兒駱晉風過來,才啃過蹄髈,里還帶著油,似乎記掛廂房里沒吃完的蹄髈,就站在門口探進來道:“怎麼了,我干什麼?”
黃翠玉沉臉朝他呵斥:“你給我進來!”
駱晉風這才不愿地進來:“又是怎麼了?栓兒哭了?橫豎又不是你哄,怎麼這麼大氣?”
黃翠玉拉著他坐下,怒聲道:“我子虛,要喝燕窩。”
駱晉風忍不住笑了起來:“當了貴夫人就是不一樣了,銀耳都瞧不上,要喝燕窩了。那不天天在喝著麼?要喝找阿香給你燉,找我有什麼用?”
黃翠玉耐著子咬牙道:“已經沒了,但我這月子還沒完呢,你想辦法給我去弄來。”
駱晉風沒買過燕窩,但也知道那東西貴,算了算自己手上的私房錢,回道:“你有錢?有我就給你去買。”
黃翠玉氣道:“你是腦子壞了還是心壞了?我是你駱家的媳婦,才給你們生了個帶把的孫子,要喝燕窩補個子,還得自己拿錢去買?我說的當然是讓公中出錢,廚房買來燉!”
駱晉風反問:“你覺得可能嗎?母親和大哥,都不喜歡什麼燕窩魚翅的東西。”
“怎麼不可能,他們不喜歡是他們,我現在是坐月子!”
“那你怎麼不去和母親說?”駱晉風回。
黃翠玉氣不打一來,急赤白臉道:“我是媳婦,你才是兒子,那栓兒也是你的種,你不說誰說?”
駱晉風不吭聲。
黃翠玉悲聲道:“同樣是駱家的媳婦,人家大房的天天燕窩蟲草阿膠,我生了兩個兒子,喝一口燕窩還是人家施舍的,說出去都沒人信……”
駱晉風回道:“那是人家嫁妝多,想買什麼買什麼,娘家又總送這送那,母親總不能讓人家娘家不送。”
黃翠玉又被氣到,深吸一口氣才忍著沒發作,繼續哭道:“也就你這麼老實,覺得那是人家自己出錢買的、是娘家送的。你也不想想,這兩年,管著家里的賬,多錢打手里過?隨便做個假,就是幾十上百兩銀子,要不然怎麼過得和我們不一樣呢?”
“的賬,也是要給母親看的。”駱晉風回。
黃翠玉不屑地一笑:“就母親那能耐,你覺得做個假賬,能看懂?”
駱晉風無言。
黃翠玉說道:“你也不用去和母親說,你就和大嫂說,說我子虛,要補,讓吩咐廚房,去買些燕窩回來就行了,我一個人,又吃了多,只是勾個賬的事。”
駱晉風一聽就不太愿意:“從你懷孕到坐月子,本來就是專門給你做的菜,我看著頓頓都是好幾個,好的,你就別再費這個神了。”
一不留神,黃翠玉哭了起來,委屈道:“只是想在月子里喝個燕窩而已,竟像要金山銀山似的……我知道你就是怕你大哥,也怕你大嫂,這也不敢說,那也不敢說……
“只怪我傻,一心想為你多生幾個孩子,也讓你們家后繼有人,哪想到孩子生了,自己就沒人管了……
“反正熬壞了我,你也不怕,回頭等我死了,再娶一房年輕的進門。如今你份不同了,想娶誰也不是事,哪像當初我嫁你,什麼都沒有,別說家世、聘禮,人活不活得都兩說……”
“行了行了,我去說行了吧。”駱晉風實在被哭得頭疼,應下這事。
黃翠玉又泣了幾聲,回道:“你就去和大嫂說,若是不應,你就讓把自己不喝的勻一點我也,你不知道,不喝的可都是直接倒的。”
駱晉風嘆了口氣,他不知道那玩意兒有什麼好喝的,明明家里別的吃食多的是。
他還欠著大嫂的人沒還呢,怎麼去開這個口?
猜你喜歡
-
完結54 章

東宮鎖嬌(重生)
人人都道太子裴瑧厭惡媚色女子,裴瑧自己一度也這麼覺得。但當他得知有人要設計陷害他與蘇妧時,卻鬼使神差的將計就計入了這圈套,和蘇妧成了荒唐事。醉心于權勢的冷血儲君,一朝食髓知味,只想把美人嬌藏進東宮。可當他醒來時,得到的消息卻是美人自裁了。裴瑧怒發沖冠,不知做了多少瘋狂事。得幸重新來過,裴瑧只有一個念頭,這輩子,他再不會讓她從他身邊逃走。 PS:架空,雙潔,HE。
15.6萬字8.18 24188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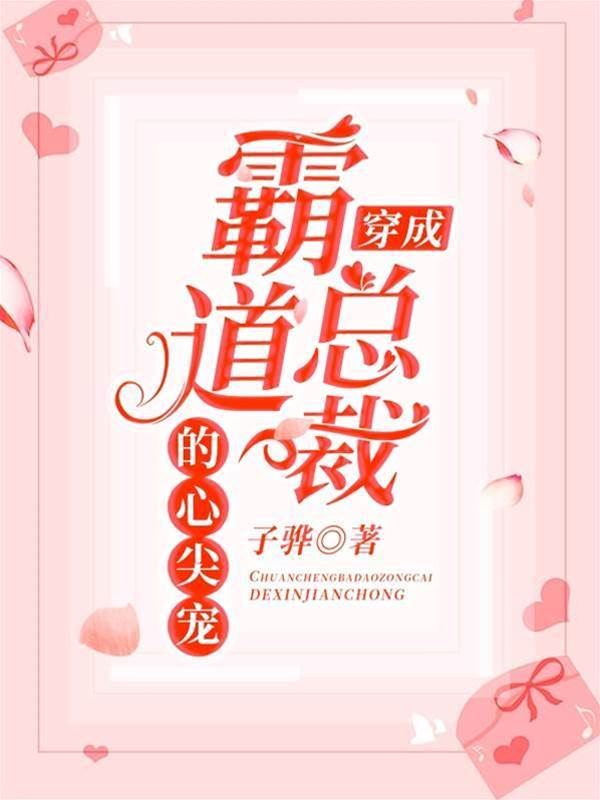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730 -
完結309 章

侯爺獨寵:夫人要出逃
她本是21世紀的法醫,一朝穿越,成了寄人籬下的孤女。為了父仇家恨,被奪走的一切,她不惜嫁給一個藥罐子。豈料藥罐子,卻是那將她玩弄于股掌的人。奪回被奪走的一切,還不清的桃花債,無處可逃的背叛。被忘記的十五年之約,最后才恍悟,他的冷酷無情,不過…
84.9萬字8 39777 -
完結852 章

我見探花多嬌媚
靖寶有三個愿望:一:守住大房的家產;二:進國子監,中探花,光宗耀祖;三:將女扮男裝進行到底。顧大人也有三個愿望:一:幫某人守住家產;二:幫某人中探花;三:幫某人將女扮男裝進行到底!…
146.8萬字8 32622 -
完結476 章

世婚
世代為婚,不問情愛,只合二姓之好。 春花般凋謝,又得重生。 一樣的際遇,迥異的人生,她知道過程,卻猜不到結局。 重生,並不只是為了報復。 重生,並不只是給了她一人機會。 重生,原是為了避免悲劇,讓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幸福。 ——*——*—— 男主: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 女主:嗯,這話好聽。 不過夫君,金銀田產都交給我管理吧? ps:坑品有保證,但是跳坑需謹慎,男主簡介里說得很清楚,不喜莫入!
132.5萬字8 81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