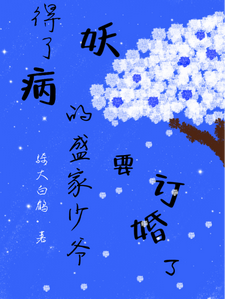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你快點心動》 第19章 心動了嗎
季清洄的敵意太過明顯,毫無遮掩,也無遮掩之意。
年只是站在那里,便如一棵白楊,巍峨拔,可風沙。
程聽蘿生出了點兒“原來也有人在護著”的覺,鼻尖有些酸,拉了拉季清洄的袖子,“我們回去吧。”
這是拒絕意。
拒絕和溫常賦他們走。
徐亦婉臉上是擋不住的落寞。
不遠,溫蘊和溫辛站在那里,靜看著他們這邊,沒有走過來。
程聽蘿一回眸就看見了他們。
和溫蘊遙遙相,溫蘊一及的眸,就如被燙到般地低下眸。
也收回了視線,轉和季清洄離開。
公車上,程聽蘿第一次和季清洄并排坐。
把書包抱在懷里,同他講今天發生的事。
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
陳述完事以后,季清洄聽見說:
“我好像,可以飛出深淵了。”
“只不過,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從天而降了兩個,可以把我拉出去的人。”
他側目看。
“既然沒有比現在更糟的環境,那不妨過去試試。”
程聽蘿看著窗外,抿了。
是啊。
既然沒有比現在更糟的環境,那為什麼不走呢?
早就想離開了,不是嗎?
另一個環境,再怎麼糟糕,大抵也糟糕不過現在。
程聽蘿覺得有道理。拿出手機找出溫辛的Q.Q,發了一句話過去:【有什麼事,下午可以讓你爸媽找我爸媽說,我不手,也沒有意見。】
當時加Q時以為只是加了個同學,沒想到有朝一日還會有這樣的用途。
見心事重重,季清洄拖著腔懶懶地說:“小小年紀哪來那麼多煩惱。”
程聽蘿心想,怎麼沒有?那可真是太多了。
Advertisement
坐了八站,下車后,好奇地問:“我還不知道你家在哪呢。”
“好奇啊?”季清洄跟分道走,勾著笑,隨意地揮了下手,“不告訴你。”
程聽蘿:“......”
這個人,真的是,非常的拽。
往自己家走。
只剩自己一個人了。
忍不住回頭了下,心想,如果這事兒是真的,如果走了,那以后就不會再和他坐同一路公回家,也不會再在學校外的區域偶遇到他了。
記得剛來的時候,還因為要和他坐同一輛公而張抗拒,沒想到這才沒多久,竟然會因為再也不能和他坐同一輛公而到不舍。
程聽蘿笑了笑,是在笑自己的善變。
可是來到這座全然陌生的城市后,季清洄是第一個敞開心扉的人。
很多很多話,自己都沒想到,但有時候氛圍驅使、亦或者是他上偶爾的覺驅使,不自的就是同他吐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明明這人看上去又冷又拽,并不像是一個男知己,但他們好像真的了朋友。
程聽蘿說不出是什麼覺,但覺得。
這是一件還不錯的事。
并不喜歡和陌生人相,但是和他相并不會有不適的覺。
回到家時,先去倒了杯涼水喝,解解暑熱。
肖來娣在喂程小哲吃飯,程小哲全神貫注地在刷手機的短視頻。
程小哲年齡雖小,卻早就喜歡上玩手機了,要是不給他玩,他會又哭又鬧。肖來娣哪里舍得寶貝兒子哭,于是對他總是無下限的縱容,要手機就給玩一會,反正等程洪昌回來他就黏爸爸去了。
程聽蘿有很多的話想問肖來娣,卻又不知從何問起。心下轉了不知幾百轉后,佯裝無意地問:“媽,為什麼你這麼疼他?你從來沒這樣對過我……”
Advertisement
時和程小哲如今天差地別,可以稱得上是個沒有年的人。
肖來娣的作都不帶停頓的,隨口回答著:“廢話,他是男孩子,你跟他比什麼比?要是家里沒有個男孩,那不就是斷子絕孫了?人家是要在背后指指點點地笑話你的。生了兒子以后,我腰桿都直了,我不疼他疼誰啊?等以后老了走了,都得靠他哩,誰去世了沒個兒子抬棺坐轎啊?沒有的話,死了都丟人!閨有什麼用啊,以后養大了都是別人家的,疼了也是白疼。”
程聽蘿想說不是的。
孩也是子孫后代,兒也會給你養老送終,笑話的那些人思想封建,他們才是錯誤的。我們應該糾正他們,而不是為了迎合他們而使自己做出和他們一樣錯誤的事、使自己的思想和他們齊驅。
但是很快清醒過來。面對的是肖來娣,肖來娣從一出生接的就是這樣的思想,從的名字就可以見得,在想什麼?怎麼可能改變得了肖來娣?
肖來娣又何嘗不是那群人中的一個?早就被腐朽了思想,同化了靈魂,說再多都是多余,平添爭執罷了。
今天問這些,不過是想看看肖來娣的反應,試圖找出什麼和世有關的破綻。想得到的結果是:肖來娣的偏心會不會有一部分是因為不是親生的?
可是就目前而言,看不出一痕跡,肖來娣這樣待,似乎就真的只是因為重男輕。
程聽蘿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但是言至此,也只能先按下自己的諸多猜測與懷疑。
下午去上學,肖來娣帶著程小哲在睡午覺。臨走前,看了一眼他們房間的方向,眸深深。
有一種,即使自己再也不回來,也不會覺得留的覺。
Advertisement
-
這世界上好像有一種定律。
——明明以前不怎麼遇到過的人,一旦在意起來,就會常常遇見。
在校門口,程聽蘿遇見了溫常賦送來上學的溫辛和溫蘊。
他們從那輛坐過的車上下來,和車里的人揮手道別。
程聽蘿只是看了一眼,便悶頭往學校里走。
是被季清洄提起來的。他帶著點哼笑的聲音一道響起:“老低著頭做什麼,本來就矮,再低下去,人影都看不見了。”
程聽蘿:“……”
像是被招惹了的虎,張開爪牙想咬他:“你才矮!我哪里矮!”
有一米六七,在南方與矮這個字本沾不上邊。更是頭一回被說快看不見人了。
可是——
忽然沉默。
因為發現說矮的人確實很高,好像確實……有資格說矮。
他怎麼長的,怎麼能長這麼高?
程聽蘿驚訝地一算,唔,比高了一個頭不止。
——行吧。
人家確實有資本。
心里服了,上沒服:“長那麼高干什麼,擋路。”
季清洄氣笑了,“比不過怎麼還人攻擊?”
程聽蘿反駁得很快,拒絕承認:“我沒有。”
小姑娘終于恢復正常了。季清洄覺得自己真的是很善良。他很滿意地抬了抬眉,角勾著弧度。
符戈和岑可從校外跑進來,追上這兩人,“你們來得好早!”
到班級后,溫辛總想和程聽蘿說話,可是又不知道說什麼。他頻頻往那邊張。
程聽蘿看過去時,他又連忙收回目,佯裝無事發生。
程聽蘿想了想,還是沒說什麼。主要是,也不知道和他說什麼。
不管是溫辛還是溫蘊,現在都不想面對。
現在這個點,也不知道溫常賦他們找上門了沒有。
之所以讓他們下午去,就是想讓他們大人自己理這件事,不想摻和其中,也不想參與他們的談話。
是真是假,該怎麼做,他們自己說去,只想等一個結果。
上學時間,程聽蘿的手機都是靜音的,放學的時候發現有兩個未接電話,都是程洪昌打的。
看來他們應該已經見了,這件事也已經朝程洪昌和肖來娣挑開了。
現在回去,面對的就是他們一群人了。
程聽蘿深深地嘆著氣,到了一巨大的力。
更沒想到的是,在校門口,看見了程洪昌。
這個從小到大都沒接送過的人,史上第一次出現在了的學校門口。
程聽蘿頓住腳步,不知他為何出現,也不知他緒如何,有些不敢上前。
是程洪昌先開的口。
“干什麼呢?過來,回去了。”
程聽蘿默默地跟過去,跟在他后走。
程洪昌是有出行工的,來到這里的第一天他就買了輛電瓶車,不然去哪里都不方便。他帶著程聽蘿找到停在路邊的車,載著回家。
程洪昌四十幾歲的人,白了半個頭,但他經常去染頭發,所以現在看著是黑的。
這一路上,程聽蘿覺得到他尤其沉默。
坐在程洪昌的后座,被他載著,是一種完全陌生的驗。上一次……都忘記是多久之前了。
程聽蘿和肖來娣還好,怎麼說也是朝夕相,就算有仇那也是在對方心里滿滿的存在。但是從程小哲出生后,程聽蘿和程洪昌父倆的流得可憐。
程聽蘿其實很父和母。即使從未得到過,也見過別人家的幸福,羨慕不已,可得不到。
在縣的好友錢橙就是獨生,的媽媽很,滿心滿眼都是,是程聽蘿最羨慕的人。“獨生”的份也是程聽蘿的一個執念,設想過很多次——要是沒有程小哲就好了,要是是獨生就好了。總覺得,如果是獨生,也可以擁有爸媽的寵。
對程洪昌和肖來娣,是有幻想的,也是有的。是在的基礎上,才會生怨與恨。
突然的,程洪昌終于開口了:“今天下午,我被回了家……我知道,他們已經去找過你了。”
程聽蘿輕輕地“嗯”了一聲,等待著他的下文。
“我就想問問你是個什麼想法?”
程聽蘿:“……我不知道。”
“你愿意去的吧?我猜得到,畢竟那是個有錢人家。”
程聽蘿沒有說話,父倆再次陷沉默。
的,程聽蘿似乎聽得見一聲嘆氣。
程洪昌接著說:“你要諒一下我們,我們就是普普通通的農民,掙點錢不容易,把你養大已經很不容易了,你得知道恩。我們想生個兒子也沒有錯,整個村里誰家沒兒子是要被笑的。百年來都這樣,不止咱一家,別人家的孩乖得很,沒一個像你戾氣這麼重,想的那麼多,你太自私了,你都沒有為我們考慮過。”
程聽蘿的心落了寒意。
到頭來還是這樣,他們總是要指責自私,總是要將那些形百年的封建糟粕灌輸進的腦子。
可是,流傳已久的東西難道就是對的嗎?
不甘心在重男輕的世界里被輕視,就是的不對嗎?
一個鍋接一個鍋地往頭上扣,毫不曾顧慮過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這些話會不會傷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會不會給造影——到底誰才是自私的一方?!
事到如今,他們還在試圖扭轉的思想,指責的怨氣,卻從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半分過錯。
程聽蘿只覺得可笑至極。
笑他們的可悲,笑自己的可憐。
“所以呢?你想說什麼?”
孩的聲音很平靜,無波無瀾,不再對他接下來的話抱有任何的期待。
“……沒想說什麼,就是覺得我們父倆蠻久沒說話了,想和你聊一聊。”這個已經有滄桑之態的中年男人嘆了口氣,“我本來覺得,你懂事的,就不想多說你,但是現在想想,還是得講一講。孩子家,你脾氣要好一點,別那麼,整天頂撞這個頂撞那個,傳出去都能把人嚇跑。平時也要多和你媽學做菜,做的那麼難吃,以后怎麼嫁人?”
“我不是為了嫁人而生的,我是一個獨立的人,你不要總是想把我□□一個‘適合嫁人’的人。”程聽蘿冷聲道。
猜你喜歡
-
完結727 章
同桌求愛
一次見義勇為,讓沒有交集的兩人成了怨念很深的同桌。從此冤家互懟,語不驚人死不休。大家都覺得兩人會水火不容度過高三時,薑非彧卻開始驚天地泣鬼神的表白模式。一天一月一年,鮮花蛋糕玫瑰。 “薑非彧,求你放過我吧。” “不行,你都好意思叫權詩潔了怎麼能拿走我的全世界呢?” “what?” “和你在一起才是全世界(權詩潔)。” 媽的,她能拒絕這個智障嗎?
62.2萬字8.18 48034 -
完結111 章

穿成大佬的嬌軟美人
作品簡介: 按照古代賢妻良母、三從四德傳統美德培養出來的小白花蘇綿綿穿越變成了一個女高中生,偶遇大佬同桌。 暴躁大佬在線教學 大佬:「你到底會什麼!」 蘇綿綿:「QAQ略,略通琴棋書畫……」 大佬:「你上的是理科班。」 —————— 剛剛穿越過來沒多久的蘇綿綿面對現代化的魔鬼教學陷入了沉思。 大佬同桌慷慨大方,「要抄不?」 從小就循規蹈矩的蘇綿綿臉紅紅的點頭,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出格表演。然後全校倒數第一抄了倒數第二的試卷。 後來,羞愧於自己成績的蘇綿綿拿著那個零蛋試卷找大佬假冒簽名。 大佬:「我有什麼好處?」 蘇綿綿拿出了自己覺得唯一擅長的東西,「我給你跳支舞吧。」 ———————— 以前,別人說起陸橫,那可真是人如其名,又狠又橫。現在,大家對其嗤之以鼻孔。 呸,不要臉的玩意。
34.1萬字8 9661 -
完結245 章

玫瑰惹清風
聶錦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妹妹突然生病,需要換腎,她成了腎源的不二選擇。從來沒有管過她的媽媽上門求她,妹妹的繼哥程問也來求她。知道妹妹喜歡程問,聶錦對程問說,“想要我救她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一個要求!”程問,“什麼要求?”聶錦,“冬天快到了,我想要個暖床的,不如你來幫我暖床?!”程問,“不可能。”聶錦,“那你就別求我救她!”程問,“……多長時間?”聶歡,“半年吧,半年後冬天就過去了!”程問,“我希望你能說話算話。”半年後,聶錦瀟灑離去,程問卻再也回不到從前。
27.1萬字8 19933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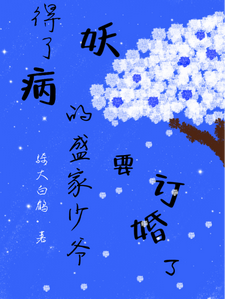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