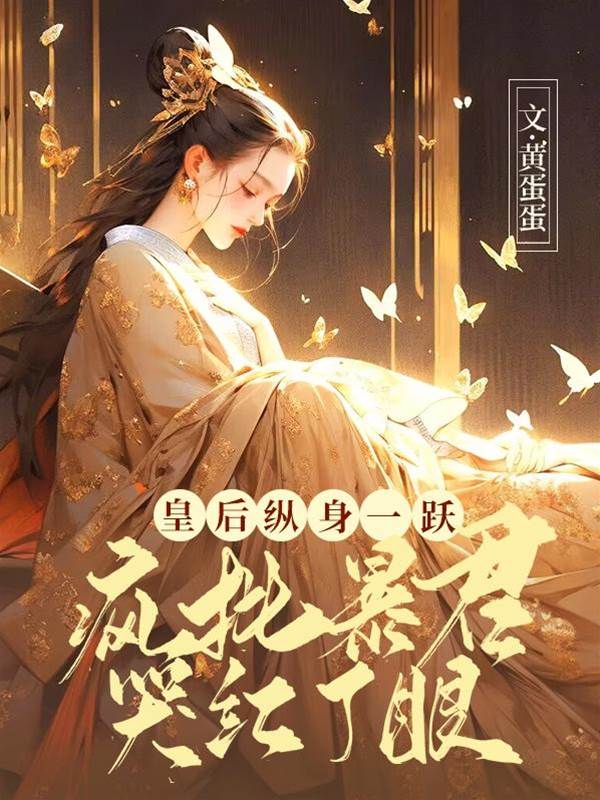《笨蛋美人重生后》 第34章 指腹
“太子忙于公務, 無暇前來探。托屬下傳話給小姐,五日后去拜訪蕭老太尉,問小姐是否方便。”
虞秋聽到最后一句, 手中飛速走著的繡花針一歪,直直刺指腹,“嘶”了一聲捂住了手指。
“沒事沒事。”擺手讓丫鬟出去,虞秋問,“怎麼突然要去太尉府?”
遲早都是要去,但虞秋以為至還能拖半個月時間的。
并非不愿意去,而是近日心神全都被云珩與云瑯這兩人占據,且要加速繡荷包, 本就沒能靜下心來思索要如何獲取蕭太尉的原諒。
侍衛答道:“圣上催著小姐進宮面見皇后娘娘。”
幸好虞秋手中的針已放下,否則多半還要再被扎上一回。
這也是必須要經歷的, 不慌。
沉住氣, 問出最想知道的事,“太子他戴了我繡的荷包了嗎?”
“戴了的。”
虞秋認命了,讓侍衛回去, 繼續飛針走線。
云珩外出戴著繡的荷包, 多半已經被許多大臣看見了,沒了退路, 必須要在云瑯上的荷包被人看見之前, 把其余幾個全都繡好。
這邊忙得指尖要著火,罪魁禍首還跑來搗。
“皇嫂,我想出去玩。”
虞秋道:“把那本書看完,明日我考考你, 全部讀懂了才能出去。”
云瑯撇, “那我要吃外面的東西, 你們府里的廚子手藝太差了!”
府里的廚子廚藝的確很普通,飲食很是清淡,他吃不慣也正常。虞秋停了手中針線,問清了他想吃什麼,吩咐下人去外面買來。
事安排下去了,走回來一看,云瑯著針線正在。
虞秋真是要被這兄弟倆折騰死了,趕走過去,還不敢手搶,“殿下當心,十指連心,扎到會很疼的。”
Advertisement
云瑯往手指頭上瞅了瞅,“那你還繡?”
虞秋道:“你把那只還給我,我就不繡了。”
“那不可能。”云瑯想也不想就拒絕,“我得報仇雪恨呢。”
虞秋長長吸了一口氣,再吐出,難怪云瑯總挨打,現在連都想手了。
最后虞秋停下手中事,答應念書給他聽,他才還了虞秋的針線。
這人也不知道是什麼壞病,皮實的很,不喜歡看書,字也寫得丑,就是喜歡別人給他念書,這時候就聽話得很。
念了大約兩頁,丫鬟傳話說靖國公府來人了。“是個管家,說是來賠禮的。”
云瑯騰地起,嚷嚷道:“得罪了我與皇嫂,就派一個管家來賠禮?欺負人呢!等著,看我怎麼教訓他!”
“不許去!”虞秋喊道。
云瑯作靈敏,虞秋追不上,喊了一聲平江,才把人堵住。
虞秋耐心與他講道理:“管家是聽命行事的,何必為難人家?況且這事鬧的夠大了,葛齊去打探了消息,說已經傳得人盡皆知。”
“左右咱們沒吃虧,太子也已經為咱們做了主,不能太過分的,落了人家的口實會讓太子難做的,知道了嗎?”
云瑯恍悟:“皇嫂你說的對,不該去為難管家,該直接找許國公與他夫人算賬的!”
“……”虞秋扶額,說了那麼多,他就聽進去第一句,還把其中意思曲解了?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并且用了平江,才終于將人勸下。
對方只派了管家過來,虞秋也僅讓管家出面,算是給彼此一個面子將這大事化了。
之后幾日,虞秋再未踏出過府門,一面看著云瑯不許他鬧事,一面忙著繡荷包,終于在第四日傍晚將荷包全部完。
叮囑虞行束一定要把荷包戴著,虞秋再一次與他說起要去拜訪蕭太尉的事。
Advertisement
虞行束是不一起去的,他很能理解蕭太尉不愿意見他的緣由。其實他能不能獲取蕭太尉原諒并不重要,只要虞秋能多個靠山就行,這樣他日面對九泉之下的妻子,他心中也能好些。
他反過來囑咐虞秋:“一切順著太尉的意思,他說了難聽的話罵我不要的,幾句話而已,咱們聽聽就算了,你萬不能忤逆他。”
“他若是罵了你娘,你也只當沒聽見,父親教訓子,是理所應當。”
虞行束細細叮嚀,“但當年種種與你是沒有丁點兒關系的,若是有人敢提起往事欺辱你,你只管借著太子妃的份反擊回去,反正有太子跟著你。說到底這是皇家讓咱們和好,他不愿意也得忍著。”
類似的話他說過許多回,虞秋早已耳能詳,奈何以前從未真正與蕭太尉過面,此時心中難免張。
將這些話記在心底,至于到時候怎麼做,且再看吧。
次日是個艷天,虞秋早早梳妝打扮好,認真地將荷包系在腰間,務必要讓云珩第一眼就能看見。
檢查了一遍要送去禮品,喊來了云瑯。
時至今日,荷包已全部完,沒必要再惦記著云瑯那只了,把那只半品補全了,配上流蘇垂穗給了云瑯。
云瑯著荷包塞了塊銀子進去,眉飛眼笑道:“我好久沒收到荷包了,上一回還是四年前,我母妃給我做的呢。皇嫂,你對我真好!”
虞秋問過平江,云瑯的生母去世時他才十一歲。大抵是因為今日要去蕭夫人生長的地方,虞秋被了緒,聞言微有傷。
想說這不算什麼,云瑯又喜氣洋洋道:“皇嫂,我能不能喊你一聲娘啊?”
虞秋一口氣險些岔過去,掩咳了兩下,倉皇訓斥道:“不許胡說八道,待會兒太子就來了,當心我告訴他,讓他親自來教訓你!”
Advertisement
云瑯懼怕地起脖子,探頭了,見周圍沒人,小聲嘀咕道:“還是算了吧,他要是我爹,肯定天天揍我……”
虞秋瞪了他一眼,忍了片刻,終是沒忍住,提醒他道:“我只比你年長一歲。”
“哦。”云瑯搔了搔腦袋,歪頭問,“那你為什麼要嫁我皇兄……”
虞秋真是怕了他了,云珩都快到了,他還提這種話,若是不慎被云珩聽見,真是太尷尬了。
匆忙轉移話題:“待會兒我與你皇兄就要走了,你老實待在府中,不許欺負人。”
虞秋一看他骨碌轉的眼珠子就知道他不安分,警告道:“平江會留下看著你的,你皇兄送我回來時候要是他告了狀,你知道的,你皇兄可是心狠手辣、六親不認的。”
云瑯做乖巧狀,朝著后大聲道:“皇兄,你聽見了,是皇嫂說的,不是我。”
虞秋后心一涼,僵著子不敢彈。
全府上下都知道今日云珩要接去太尉府,早就得了令不必通傳,直接讓人進來就行。
虞秋悔不當初,應該讓人守在周圍的,背后說人壞話被抓包,也太讓人下不來臺了。
云珩一定會問為什麼要這麼說。要怎麼答呢?
他那兇狠與強勢勁,虞秋只在夢中見過,對云珩的印象應該是風度翩翩的儒雅君子才對。
虞秋心里七上八下的想不出個理由,云瑯拍著手大笑起來,“我騙你的!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也怕我皇兄,還說勸他不要打我,你敢開口嗎?”
“……”虞秋咬著牙轉向庭院,見院中除了不遠來往的三兩下人,本就沒有云珩的影。
長長舒氣,努力平復心,出笑道:“就你貪玩。”
這麼貪玩不聽話,怎麼還沒被云珩打死!
“我去前面等你皇兄了,你一個人老實點。”
已經完全不想理會云瑯了,逃難似的去了前院,步伐匆匆地穿過月亮門,正好迎面看見云珩,虞秋心中一,腳步就此頓住。
上次與云珩見面的景涌腦海,那是在閨房的外間,沖云珩撒了個,被他抱起坐到了桌面上。
熱氣從心底蒸騰起,轉瞬爬上了虞秋的臉,開始覺得被那雙手過的幾個地方麻起來,兩人明明隔了那麼遠,那雙手好像又重新回到了上。
不自在地轉向一側,被盛開的山茶花填滿了視線。
云珩看著俏生生立在花前,角向下去。
這太子妃今日需要他幫忙,果然又開始對他用人計了。
他腳步不疾不徐,目掃視著著虞秋,從高挽起的發髻與致朱釵向下,在修長脖頸多看一眼,接著目一頓,轉向腰。
然后右手輕輕挲了下。
下一刻,就看見了腰間的荷包,與他上的一樣,上面是燦爛桃花與振翅相逐的比翼鳥。
這是他的太子妃,就是不用人計,他也是會幫的。
思緒回轉間,人已至跟前,云珩低頭問:“怎麼見了我就不了?”
虞秋躲閃著道:“沒呀,我沒看見,我在看花呢,開得真好。”
云珩一句“花不及人”藏在心中,道:“是不錯。今日去你外祖父家,可準備妥當了?”
虞秋胡點著頭,兩人并著往外走去。
中間云珩問了幾句靖國公府賠禮的事,又問云瑯是否聽話,有沒有給添麻煩。虞秋挨個答了,不想云瑯挨打,也盡挑著好話回的。
上馬車時,又是云珩來扶,穩穩當當地把虞秋送了上去。
掀簾與虞行束道別,馬車啟程后,虞秋覺得呼吸不順暢,偏頭看向小窗外以躲避云珩的視線。
“阿秋。”云珩喊道。
虞秋臉熱,抿著輕緩轉眸,聽他道:“把手給我。”
兩人各坐一邊,中間大約是人小臂那麼長的距離。他端坐著,面平靜,視線直直落在虞秋擱至膝上的雙手。
虞秋著眼睫,乖順地將左手了過去。
云珩接住,掰開微蜷的手,在指腹看見數個小小的針眼。
是為他做荷包被針刺傷的。
他眸轉深,去抓虞秋另一只手,同樣掰開細細檢查。
虞秋被他抓著雙手,只覺得他手掌太大了,力氣也很重,箍著的手讓無法彈,就好像那日被他困在桌上一樣,讓無可逃。
好一會兒,手指忽地被云珩了,心突地一跳,強迫自己沒去掙扎。
云珩的聲音再次傳耳,較之前低了許多,“今后不必再為任何人針線。”
猜你喜歡
-
完結1858 章
王妃她不講武德
寧孤舟把劍架在棠妙心的脖子上:“你除了偷懷本王的崽,還有什麼事瞞著本王?”她拿出一大堆令牌:“玄門、鬼醫門、黑虎寨、聽風樓……隻有這些了!”話落,鄰國玉璽從她身上掉了下來,他:“……”她眼淚汪汪:“這些都是老東西們逼我繼承的!”眾大佬:“你再裝!”
326.8萬字8.18 247903 -
完結81 章
太子妃只想擺地攤
南知知穿成一本重生复仇文里的炮灰女配,身为将军千金却家徒四壁,府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只鸡,她只好搞起地摊经济。 从此京城西坊夜市多了个神秘摊位,摊主是英俊秀气的少年郎,卖的东西闻所未闻,千奇百怪。
21.8萬字8.53 8502 -
完結212 章
鐘娘娘家的日常生活
鐘萃是堂堂侯府庶女,爹不親娘不愛,但沒關系,鐘萃知道自己以后會進入宮中,并且會生下未來下一任皇帝。這些蹦跶得再歡,早晚也要匍匐在她腳下,高呼太后千歲。哪怕是對著她的牌位!這輩子,鐘萃有了讀心術,上輩子落魄沒關系,以后風光就行了,只要她能阻止那個要黑化,以全國為棋子的賭徒,在生母病逝于宮中后被無視冷漠長大的——她的崽。鐘萃都想好了,她要用愛感化他
75.3萬字8 1620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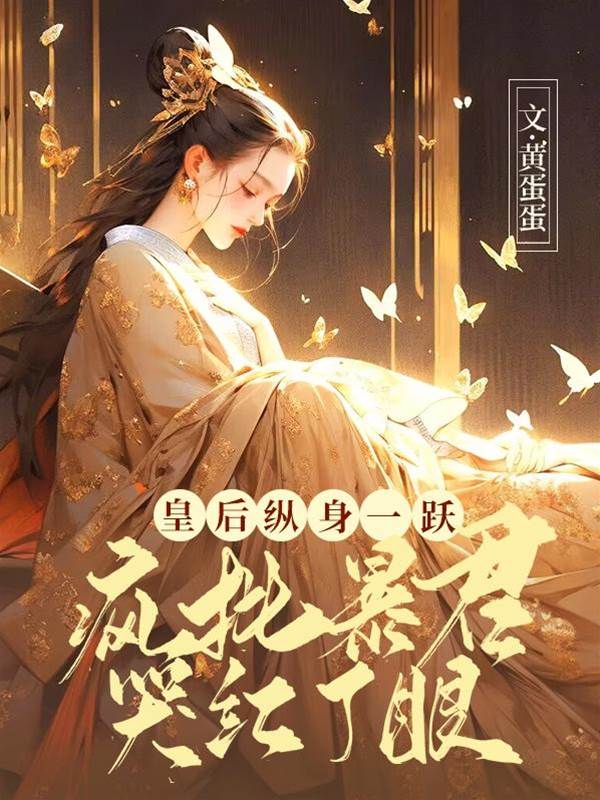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