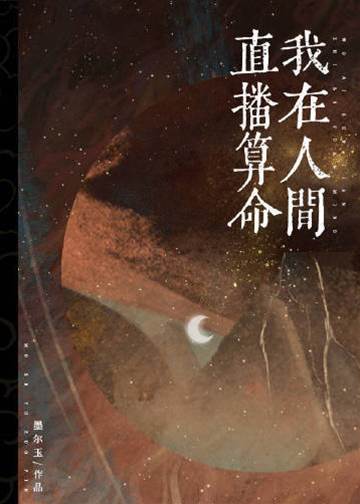《我的師妹不可能是傻白甜》 第95章 第 95 章
宋溪筱見梅良玉真走了,眉頭一皺,正要攔人,穆武和諸榮走過來打圓場,把攔住,張宇軒又客客氣氣地說了些好話,這才去追梅良玉。
顧乾見梅良玉走后,才撤下戒備,回頭看了眼文輝,他這會估計也不好,便忍了沒說什麼。
自己人做錯事自己手可以,但他可見不得梅良玉當面給文輝教訓。
兩撥人本就有恩怨,經過斬龍窟此行仇恨還升級了,梅良玉一行人對文輝手,顧乾絕不會坐視不理。
至于盛暃,他一直都這樣,顧乾這會也懶得理會他。
“先治傷吧。”顧乾淡聲道。
文輝被霍霄扶著,低頭時眼中滿是戾氣。
這一道金雷劈地猝不及防,他這會一口哽在中不上不下,五行之氣逆,呼吸都疼。
留下的雷印灼燒可以消除,但在這麼多人面前被狼狽擊飛的辱卻讓文輝無法接,他憋著一口氣,即使五行之氣逆,抓著座椅扶手的五指依舊按得死死的。
文輝靠著椅背緩緩閉目,把所有緒都藏。
敢去機關島。
他等死吧。
*
虞歲聽見敲門聲,是李金霜來,便起去開門,同時讓法家廣場的五行核追著梅良玉離開。
“走吧。”虞歲朝站在門外的李金霜彎眼笑道。
這會已經是晚上,已經快到齋堂的加錢時間,去齋堂的路上也沒有太多人。
虞歲和李金霜邊走邊聊在斬龍窟里的經歷,快到齋堂時,在前方叉口看見被張宇軒追著的梅良玉。
同樣的一條繁花道路,曾站在下邊,梅良玉坐在齋堂樓上窗口。
路道兩旁的石燈亮著熠熠火,從前方走來的梅良玉也看見了虞歲,而卻先一步轉開視線,笑著跟李金霜說話,不再像從前一樣笑盈盈地先打招呼,喊出一聲師兄。
Advertisement
虞歲錯開了對視,也錯開了道路,徑直朝齋堂里走去。
梅良玉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旁張宇軒在說的一時半會都沒聽進去,見虞歲的影沒齋堂中后,才漫不經心地嗯了聲。
張宇軒嘆氣:“你本沒在聽吧。”
梅良玉點頭:“嗯。”
“我看你去機關島也得小心些,文輝被你當眾折辱,肯定咽不下這口氣。”張宇軒碎碎念道,“文家那些老前輩也不會一直看著你欺負他吧。”
梅良玉嗤笑聲:“誰欺負誰呢?”
張宇軒說:“總之你自己小心點。”
梅良玉應了聲,隨口道:“你去忙吧,不用擔心我,他不敢在路上對我手,我先去看看師尊。”
虞歲剛走到齋堂二樓,聽見這話朝窗外看了眼,夜中只能瞧見路上的石燈明亮,看不見剛還走在路邊的人影。
回來沒有第一時間去鬼道圣堂見師尊,雖然有很多問題想問,但如今也得思考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梅良玉剛出斬龍窟就因為犯院規被罰去機關島,這點倒是出乎意料,但他臨走前也要去見師尊,又在意料之中。
虞歲在桌邊坐下,給自己倒了杯水后,又給李金霜倒了杯。
耐心等著,可梅良玉慢悠悠地走去鬼道圣堂,他連風都不用,看起來似乎一點都不著急,愣是從法家一路走到鬼道圣堂。
虞歲吃完飯,李金霜都已經離開,只剩一個人還坐著,梅良玉才走到鬼道家。
徒步也是一種鍛煉和修行,也能讓梅良玉靜下心來思考更多,他讓自己保持永遠冷靜理智的狀態,這樣才能得住心底深的憤怒。
要麼是讓起來,要麼是讓腦子起來。
沒人知道梅良玉都在想些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
Advertisement
等走到鬼道圣堂門前,梅良玉看著里邊亮著的石燈,目輕輕轉,看向旁側花落果滅的杏樹,此刻已是青翠枝葉滿冠。
最近想師妹的事,想得有些太頻繁了。
梅良玉收回視線的同時也下思緒,朝圣堂大殿門走去。
虞歲雙手捧著溫熱的茶杯,垂眸看杯中倒映的暈,意識過杯水看見站在鬼道圣堂中的梅良玉。
師兄倒是沒有直接講異火這事,而是倒在自己的椅子里,姿態放松地跟師尊聊著閑話,最先講的是剛出來就打了文輝的事。
常艮圣者也沒問為何,梅良玉就講了原因:“換做別人他不一定會手,看在自己甲級弟子的份上,怎麼也不會跟個一境弟子手。”
如果不是虞歲而是別的人,文輝就隨便尚公主理了。
“這兩年沒怎麼搭理他,倒是讓他膽兒了,覺得能欺負我師妹。”
梅良玉在躺椅上翻了個面,雙手枕在腦后,神莫測,半瞇著眼眸時,微勾的眼尾就更明顯。
虞歲聽到這里目微怔。
這是什麼態度。
常艮圣者:“若是和教習手,為師也不好替你說話。”
梅良玉:“我為什麼要跟教習打,出手我躲就行了。”
不愧是我的天才徒弟。
掛在石像上的畫卷被夜風吹得輕輕飄起又落下,那細微的紙頁聲響仿佛是常艮圣者的低笑。
梅良玉跟常艮圣者嘮叨的都是些家常閑話,常艮圣者也一一回應。
大徒弟有時候覺得,并非是自己需要師尊,而是師尊需要他。
剛來太乙的梅良玉很長時間都待在機關島,只偶爾幾天才會被人送回到鬼道圣堂,聽從常艮圣者教導修行。
梅良玉還記得,剛開始師尊的話并不多,除去必要的修行指導,他很說別的話。
Advertisement
是在他來太乙第二年的夏天,年坐在臺階上,雙手托腮看天上星辰,仍有幾分稚的臉龐,在星夜中襯得有幾分乖巧。
常艮圣者催他:“你該回去了。”
年聽后,干脆雙手一張,子往后一仰,整個躺倒在地上,撇抱怨道:“我才不想回去,那邊的孩子都很討厭,整天碎我,討厭我,不跟我玩,我一個人孤零零的,都沒人跟我說話。”
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眸中倒映天上銀河,盛著年人倔強不愿表現的孤獨。
沒等常艮圣者接話,他已經自顧自說道:“沒有爹娘是什麼值得天天念叨的事嗎?我都聽煩了,師尊,你告訴我,我爹娘是誰、在哪,不管是不是他們拋棄了我不要我,只要證明我是有爹娘的就行。”
常艮圣者回他:“你沒有爹娘。”
“胡說八道。”年氣鼓鼓地坐起,轉盤,背對臺階,面對圣堂大殿,“人都是有爹娘生的,我沒有爹娘,那我是怎麼來的,石頭里蹦出來的啊?”
常艮圣者:“你可以這麼理解。”
年擰著眉道:“那我豈不是比他們都厲害?”
常艮圣者無言。
年雙手抱,輕哼聲:“活該他們機關比試都輸給我。”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跟常艮圣者說自己在機關島的遭遇,將自己在機關島被人嘲諷、排和打罵的事全都說了,一樣都沒落下。年氣鼓鼓地說著人們對他的排,驕傲地說著自己打贏的戰績。
他說我不喜歡其他孩子,就喜歡文軸和文岫兩兄弟。
因為只有這兩兄弟喜歡他。
不喜歡他的人,他也不喜歡;他只喜歡會喜歡他的。
年一句喜歡和不喜歡在反反復復地繞來繞去,常艮圣者沉默聽著,沒有回應。
每次都是年在說。
常艮圣者總是沉默地聽著。
年把他當做傾訴對象,他問常艮圣者:“師尊,你一個人在這里,沒人跟你說話,不會很孤獨嗎?反正我在機關島沒人跟我說話,我覺得很孤獨。”
常艮圣者的意識并不能隨意地到游走。
年著圣堂大殿的畫像說:“就算是意識,永遠待在同一個地方沒有人來,也會很難過吧。”
“我在機關島沒人陪我說話,師尊你在圣堂沒人陪伴,這是什麼師門傳統嗎?我可以選擇轉修別家嗎?”
常艮圣者:“不可以。”
年其實從小就聰明,哪怕他失去了某個時間段的記憶,仍舊能很快適應當下的環境,察覺他人的緒。
他連續一段時間,晚上都跑去鬼道圣堂陪師尊聊天,某一天忽然不去了,晾了常艮圣者三五天又來,年發現,師尊回話的次數增加了。
年開始重復這一流程,頻繁去一段時間后就不去了,過些天再去,師尊的話就多起來了。
師尊從不會說要他記得回來陪自己的話,也從未回應過是否孤獨的問題,可年知道,師尊是孤獨的,他也想要有人可以陪伴自己。
因為師尊對他的態度越來越溫。
從前的常艮圣者似乎在刻意保持距離,只沉默注視,如今卻已張開羽翼將他擁在其中。
常艮圣者以為梅良玉更需要他。
可梅良玉卻認為,師尊更需要自己。
*
虞歲耐心看了許久,卻發現師兄和師尊聊得都是些無關要的瑣事,他甚至說了被錢瓔五玄毒陣困住那天晚上,在跟龐戎他們打水漂混時間玩,常艮圣者還問他最后誰打贏了。
梅良玉說打水漂還用五行之氣,那肯定是我贏了。
連這種小事都說了,卻只字不提神木種子中的占卜,三千歧路的異。
常艮圣者問:“你師妹如何?”
“中途不小心掉懸崖下邊了,還好聰明,反應快,沒被淘汰。我找了一晚上,淋了兩個多時辰的雨才找到。”梅良玉想起那天晚上,不由坐起活下脖頸,發出咔噠聲響。
他微彎著腰,手肘撐著膝蓋,垂首看地面,眸微閃。
龍中魚和雨夜里的記憶在他腦海中飛速閃過,全都是虞歲的模樣。
原本被他下去的思緒,被師尊這一問,像是報復他一般來得洶涌。
梅良玉想起在龍中魚中,虞歲撲進他懷里的瞬間,抓著他袖眼淚的時候;想起在三千歧路,虞歲蹲下后,語調輕慢地說著讓他滾,往前湊輕輕撞了下他的額頭,轉瞬而逝的無畏眼神。
也想起來在齋堂遇見時,虞歲當做沒看見他一樣,若無其事地轉開視線,越走越遠。
兩人在三千歧路說那幾句話的時候,彼此語調神態的變化都有些極端。
當時的緒似乎還沒能被完全消化,又或者還有別的東西阻攔著,讓他和虞歲之間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
直到梅良玉說要回舍館洗一洗再去機關島,從而離開鬼道圣堂,虞歲都沒有聽見他告訴師尊異火的事,甚至沒有提過滅世者的話題。
梅良玉這次是用風趕路,五行核趁機在他上。
虞歲對五行核的控制提高不,第一次被師兄察覺,是因為核力量還沒升級,第二次在山谷中被師兄察覺,是因為他用了神機。
如今只要師兄不使用神機,他是絕無可能發現五行核的存在。
就算發現了,也不會知道五行核還能被監控。
所以不存在梅良玉知道在監視才不打算提起異火的事。
三千歧路中波的異火力量,師兄絕對是知道的,否則也不會在兩位圣者來時瞞。
既然他也會被古龍力量凝視,說明這樣的異被發現了也沒關系,除非他認為不能被發現是異火,所以才撒謊瞞。
明明知道,卻不說。
虞歲以為梅良玉會告訴師尊的。
這世上他最親近的人不就是師尊嗎?
虞歲最初并未太在意梅良玉這個人,對他也并沒有很了解,許多時候只是隨意地掃一眼,記了個大概。
因為之前在意的只是常艮圣者。
同是常艮圣者的徒弟,又去鬼道圣堂,兩人總是會在鬼道圣堂不可避免地遇上。
梅良玉作為師兄似乎沒什麼能挑剔的,也正是如此,虞歲對他才不是很在乎,兩人保持師兄妹的關系就好。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