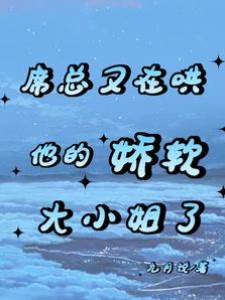《爽文女配明明超強卻過分撒嬌》 第69章 不見
黑豹的變異種突擊行失敗了, 一共三十多個變異種行,但最后死了一半。
變異種們果然做事很隨意,他們本就沒有團結意識。
在發現被人類基地發現后, 他們就知道況不妙。一些變異種幾乎就是頭也不回的直接逃跑, 干脆利落的背叛了同伴。
活下來的這十五個人有十幾個估計都是叛軍。
好吧,黑豹覺得自己也應該算一個。
畢竟他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這次這個小基地的武怎麼這麼強,老子襲過好幾個小基地了,這他媽是打得最狠的一個。”說話的是瞎子副隊。
大概還是第一次那麼憋屈, 瞎子副隊心非常不好。但他現在也不敢自己回去,畢竟他也清楚自己到底幾斤幾兩。本來他現在對變異種基地沒有什麼歸屬, 這次背叛那背叛的一個心安理得,完全沒有心理負擔。
十五個變異種有一大半還傷了, 黑豹也舊傷復發,他上都開始流。傷口的已經把服都浸了。是需要找個安全的地方治療一下傷口。
變異種們彼此之間都互相不信任, 最后只剩下黑豹跟瞎子副隊一起走。其他人都去找各自覺得安全的地方療傷。
瞎子副隊越想越難,他從自己的口袋里出來了一香煙。
香煙皺的,看得出來已經在口袋中很久了。
這是瞎子的最后一香煙,他還一直沒有舍得。自從離開了人類基地后, 他連香煙都不到了。
“他媽的,你說到底是誰暴了我們,真是個傻,明明這次我們的勝算很大的。”瞎子副隊一邊吸煙,一邊叨叨,“該不會是那個禿驢吧,或許是那個黑蛋。這兩個人平時也不說話, 行總是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Advertisement
禿驢跟黑蛋是瞎子副隊隨口給別人起的外號, 黑豹就不知道這是誰。但是他下意識的帶了一下,他總覺得禿驢跟黑蛋都像是在說他。
黑豹氣得給了瞎子膛一掌,冷聲道,“滾蛋。”
瞎子被揍的一臉懵,“你他媽的,你發什麼神經啊!”
黑豹畢竟沒有真的用力,瞎子也是嚎了幾句并沒有還手,畢竟他也打不過黑豹。
而且他不但沒有還手,還依舊跟著黑豹一起走。
他們兩個上都有傷,一個人行有些危險,兩個人還有點照應。瞎子還是信得過黑豹的。
他們漸漸走到了森林深,森林深有的地方比較安全,因為這里都是一些大型異種的領地,很有別的異種出現。只要大型異種不過來,這就是個很安全的地方。
走了好久,黑豹終于找到了個好地方坐下來休息。他發現自從變變異種后,痛也不是那麼強烈了。
他的都已經被打穿,如果換做是人類,估計早就已經疼的不行。可他現在還拖著這條被打穿的走了好久。
瞎子隊長也坐下來休息,他的神很好,左看看右看看的,黑豹都開始覺得他有點煩。
就在黑豹想開口訓斥時,瞎子突然手指了一個方向,“你看那邊是什麼。”
黑豹朝著瞎子所指的方向看了過去,就在他們的不遠有個很奇怪的藤蔓。
他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有生命力的藤蔓。
“要不我們過去看看?”瞎子的好奇心太重了。
“不去。”黑豹覺得好奇心會害死貓,而且這個藤蔓也非常的奇怪。
“你難道不覺得那藤蔓里面好似包裹著什麼東西嗎?”瞎子繼續說。
黑豹:“不覺得。”
黑豹并不打算過去看,他靠在樹邊閉目養神,但還沒有好好休息幾分鐘,瞎子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草,你快看!”
Advertisement
再一次被打擾,黑豹是真的有點煩了。但沒想到他一睜眼還沒看到到底是什麼東西,他的面前就出現了一道強烈的綠。
是他們面前的那個奇怪藤蔓發出來的!
--
三月二十號這天突然就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就仿佛是到了什麼奇怪力量的制,變異種們都變得有些奇怪,那些正在進攻基地的變異種們也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應。
與此同時還有那些正在基地中肆的變異植,他們都在同一時間進到了休眠狀態。
這一下,不只是人類基地懵了,變異種們也懵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變異種們的染能力變得很差,人類軍隊一看出現了這樣的況,也不去探究原因了,他們立刻瘋狂反擊。
沒有了植異種的幫助,變異種們的實力大打折扣,況且現在他們自也出現了問題,也不敢跟人類基地繼續糾纏了,直接轉頭就跑。
這樣的況大概只持續了十幾分鐘,但這十幾分鐘也足夠關鍵了。很多基地就是靠著這十幾分鐘翻了。
在森林深的謝圖南跟言歡并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他們只是發現森林的植異種們突然興起來,一些平時都不怎麼生長的植只在短短的十幾分鐘時間就長大了很多。
“怎麼回事?”言歡很敏銳的覺到了周圍出現了一力量,但是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況。可直接告訴這好像并不是壞事。這個力量給的覺很舒服。
謝圖南同樣也覺到了,“不知道,但看著應該不是壞事,或許有什麼更厲害的角出現了。”
與言歡的覺不同,謝圖南覺森林里面的這些植除了興激之外,還有一臣服。
Advertisement
植異種們雖不會說話,但謝圖南也知道他們都是獨立的,而異種們都是很驕傲的,他們很多時候寧可滅亡也不愿臣服。
但這一次.......
謝圖南抬眸看向遠方,不只是一個,周圍的很多植異種都出現了這種況。
謝圖南靜靜的看了許久,不知為何,他總覺得出現這樣的況,或許是在預兆著,有些事要出現轉機了。
言歡跟謝圖南這一刻的注意力都在外面,沒有人注意到,就在他們邊,有個小芽突然從地里鉆了出來。
那小芽很快的生長,變了綠的小藤蔓,而后纏住了賀雯的手腕。
--
溫賀自從晚上出事后就一直在忙。這些天他就沒有怎麼睡好過,黑眼圈又重了不。
“長,已經排查完畢,沒有任何危險指數。”
溫賀現在還在城區邊緣的控制部,他的手里拿著一份資料,據資料顯示他們這次一共擊斃了十個變異種。變異種的尸也已經被銷毀。
溫賀剛從外面回來,他親自檢查了一遍才放心。不知如此,他現在還越想越后怕。這些變異種們明顯就是有備而來,他們的計劃應該是很完善的。
幸好基地防反應靈敏提前發現了要侵的變異種,如果反應慢一點,后果真的不堪設想。
可溫賀莫名還是覺得有點不對,“你說城區的防系統大半夜的響了,可是它為什麼響,監控查到了嗎?”
被溫賀這麼一問,工作人員明顯愣了,他低頭看了看數據,才回答說:“系統上面顯示的是在三號防給出的警告,但,但是我們并沒有發現任何監控異常。”
這麼一說,溫賀的眉頭皺的更深了,“沒有任何異常,沒有任何人進來,但是防卻給出了警告?”
這可不是什麼好現象,溫賀的腦海中立刻出現了兩種猜測,第一種就是他們基地已經混了變異種,昨天晚上他功進來了,只是不小心到了防線。還有一種況就是基地里面有變異種的線,昨天晚上線出去接應卻不小心到了紅線。
反正無論是那一種況,都足夠讓人頭疼了。
溫賀還沒有頭疼完這件事,他又收到了一份報告資料。這是變異種的報告。按道理來說,變異種們應該死于基地的武轟炸才對,但有好幾個變異種很怪異,他們的上沒有任何傷口,更像是假死。
可是好好的為什麼會假死呢?
溫賀越想越覺得有點不對,他沒有耽誤時間,立刻拿著資料去了基地實驗室。基地實驗室正好有中心基地的博士值班,或許他可以看出什麼來。
溫賀進實驗室的時候博士并不在實驗室,他很見的竟然在自己的辦公室。溫賀道理辦公室后,先是敲了敲博士的門,而后推門進去。
博士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他戴著眼鏡,看樣子正在研究什麼。
“沈博士。”溫賀朝著博士點了點頭。
博士也抬頭看了看他,“小賀啊,我就知道你會過來的,就沒有通知人去找你。”
“博士也找我有事?”溫賀問。
沈博士有點驚訝,“你難道不知道?沒有覺到?”
溫賀:“覺到什麼。”
沈博士見到溫賀是真的不知道,他拍了拍邊的座椅,示意溫賀坐下。
“你先看看這個。”沈博士遞給了溫賀一個文件,“今天凌晨,很多基地的收容室里的變異種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暈厥,有的甚至還陷了昏迷。”
“陷了昏迷?”溫賀皺眉,“我這次來找您也是因為這件事。您應該知道基地昨天晚上被變異種攻擊,剛才我收到了報告,有幾個變異種的狀態很奇怪,大概就是您所說的昏迷。”
“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這樣的事。”沈博士說,“盡管這次事件只有十幾分鐘,但依舊引起了中心基地的高度重視。基地馬上開了個討論會。”
沈博士畢竟是中心基地的博士,很多消息他得到的更快。
沒想到是這樣的況,溫賀沉默了片刻,問:“那有沒有討論出結果?”
“目前大家也都只是猜測,還沒有任何的證據。中心實驗室的那些老家伙們正在加班加點研究呢。”沈博士說,“又出現了一種非科學力量,對人類來說,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壞事。但目前一些研究員們更偏向一種更壞的猜測。”
“更壞的猜測?”溫賀的心里也大概有了點猜測。
“嗯,最壞的結果。不完全變異種出現了超級進化。”
沈博士得表也嚴肅起來。
溫賀也很理解,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對于人類來說,絕對是個很大的災難。
--
連軸轉了一天,溫賀到了下午發現今天一天沒有見到溫。他不出,便讓自己的兄弟過去看看。但他沒想到他的兄弟很快就回來了。
他兄弟的表并不好,他看著很著急,額頭上都有了汗水。溫賀突然從座椅上站起來,他突然有些不太好的預,“我妹怎麼樣?”
“賀哥,不見了。”
溫賀的手抖了一下,他立刻朝著門口走去,“監控呢,有沒有查監控!”
“我查了,但是監控里面并沒有查到出去。”
溫賀馬上趕到溫得房間,房間很干凈,并沒有什麼不對得地方。不過溫賀的目很快就落在了房間的窗戶上,房間的窗戶是開著的。
他昨天晚上還給送來一杯水,那時候明明在房間的,如果監控沒有查到,那唯一的通道就是窗戶。
“查一下街道監控!”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溫迷迷糊糊的醒了過來。
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只是約記得自己用力用猛了,而后里面的能量不控制,也不知道自己被小藤蔓帶到了哪里。
不過這都不重要了,因為可以覺到媽媽的生命力恢復了。
媽媽沒事。
沒事就好。
溫沒時間傷,因為現在非常。腦袋有點疼,有些記憶又開始有點混。
有些東西暫時想不起來,溫也就不勉強自己了。所謂一回生二回,第二次經歷記憶錯,溫已經變得非常淡定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04 章

佛子為愛破戒,跪著對她輕哄索吻
「馬甲+頂級豪門+腹黑大佬+嫵媚美人+真假千金」那夜,情蠱發作,她為了活命,迫不得已爬上他的床。一夜貪歡,本以為與他一拍兩散,互不糾纏。可當她危在旦夕之時,他宛如神明降臨,又一次救了她。—再次相遇,她忐忑不安,避免背上‘風月債’,她選擇裝傻充愣,揚言傷了腦袋記不起事。本以為能就此逃過一劫,她卻不知,男人早已布滿天羅地網,靜靜地等待著她掉入陷阱。—眾所周知,霍嶼琛矜貴又禁欲,被稱為九爺,從未有異性能靠近他。可就是這樣一個高不可攀的男人,不知從何時開始,身邊卻出現了一個女人。—而被迫24小時待在他身邊的寧恣歡,她暗暗決定,嬌軟無辜的小白兔人設一定要狠狠艸穩了,絕不能崩塌,將‘失憶’演到徹底!隻是……每晚都闖進她房裏,揚言‘舊戲重演’有助於她恢複記憶的男人是怎麼回事?—世人皆說霍嶼琛雖身份矜貴但手段殘忍,嗜血無情,但凡得罪他的人都沒好下場。可他們不知,為了能讓寧恣歡永遠待在他身邊,他暗地裏究竟謀劃了多久,每天晚上又是如何跪在床邊輕哄著向她索吻。—眾多名媛都說寧恣歡隻不過是九爺身邊圈養的金絲雀,是被寧家拋棄的假千金。可不久後她們大跌眼鏡,本以為一無是處的寧恣歡,竟然是隱藏大佬。
38萬字8.18 29859 -
完結107 章

退婚後我被大叔寵爆了
初見,楊城人人聞風喪膽的封家少爺封曜用刀片抵著林釋的喉嚨,一邊強吻她,一邊警告她配合。林釋卸了封曜一條胳膊。再見,封曜意味深長的對著林釋說:“按照輩分,你應該叫我一聲舅舅。”林釋賞了封曜一個白眼。第三次見,鄉下來的土包子林釋要被退婚了,封曜語出驚人,震驚四座。“既然是婚約就不能輕易取消,承飛不娶,那我娶好了。”林釋不淡定了,丟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馬甲:怪醫聖手,無敵黑客,神秘特工,鑒寶大師.....眾人跪地驚呼:“大佬,我們有眼無珠!”封曜卻將林釋攬進懷裏,啞著聲音在她耳邊道:“未婚妻,求罩~”
27.3萬字8 15737 -
完結4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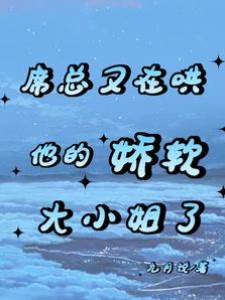
席總又在哄他的嬌軟大小姐了
矜貴腹黑高門總裁×嬌俏毒舌大小姐【甜寵 雙潔 互撩 雙向奔赴 都長嘴】溫舒出生時就是溫家的大小姐,眾人皆知她從小嬌寵著長大,且人如其名,溫柔舒雅,脾氣好的不得了。隻有席凜知道,她毒舌愛記仇,吵架時還愛動手,跟名字簡直是兩個極端。席凜從出生就被當成接班人培養,從小性子冷冽,生人勿近,長大後更是手段狠厲,眾人皆以為人如其名,凜然不已,難以接近。隻有溫舒知道,他私下裏哪裏生人勿近,哄人時溫柔又磨人,還經常不講武德偷偷用美人計。兩人傳出聯姻消息時,眾人覺得一硬一柔還挺般配。溫舒第一次聽時,隻想說大家都被迷了眼,哪裏般配。經年之後隻想感歎一句,確實般配。初遇時,兩人連正臉都沒看見,卻都已經記住對方。再見時兩人便已換了身份,成了未婚夫妻。“席太太,很高興遇見你。”“席先生,我也是。”是初遇時的悸動,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心動。
89.3萬字8.18 16227 -
完結429 章

世子爺別虐,嬌奴兒嫁你大哥了
#男二上位 身爲婁縉的暖牀侍妾,穗歲一直恪守本分,以守護淮南王府並早日迎來世孫爲己任。 可叛軍攻城後一切都變了,曾經疼惜她的男人一遍又一遍地折磨她,用盡手段懲罰她。 他將她逼到牀上蠻狠地吻她,掐的她細軟腰身上滿是淤青。 她哭喊求饒,男人卻愈加瘋狂,日日如此,她求死不成整日渾渾噩噩的過活。 直到暖出春風的大公子婁鈞的出現,讓她重燃了生的希望。 漏雨的房頂,大公子暗中幫她修好了; 她被燙傷了嗓子,大公子給她尋來世間僅有的冰玉療愈; 她被郡守嫡女污衊是小偷,大公子幫她解圍證明了她的清白; 她被患有喘症的側妃欺負,大公子種了一院子的柳樹用飄揚的柳絮給她出氣; 欺負她的丫鬟捱了板子,大公子支開了所有的府醫和方圓數裏的郎中,疼的那丫鬟咣咣撞牆…… 數年後,真相大白,她已經嫁給了侯爺婁鈞,成了婁鈞寵在心尖的小嬌妻。 婁縉悔不當初,哭着從淮南追到京城:“穗歲,我知道錯了。” 穗歲:“……” 婁鈞:“滾,這是你大嫂。” 偏愛她的人可能會晚到,但一定會出現,爲她遮擋半世風雨。
78萬字8.18 25162 -
完結245 章

黑月光她又嬌又軟
【人間誘惑黑巴克玫瑰×痞帥瘋批京圈太子爺】【男二追妻火葬場 男主暗戀成真 女主始終人間清醒 甜欲暗撩 無底線寵愛】人人都說沈清蕪命好,憑著一張狐媚子臉搭上頂級權貴陸家,成了陸家大公子陸隨之心尖尖上的人兒。誰料婚禮當天,陸隨之為了他的秘書拋下了新娘子,決絕離席。所有人都等著看沈清蕪的笑話。沒想到隔天頭條爆料,照片裏,穿著一襲抹胸魚尾婚紗的新娘子被陸家二公子陸厭行按進試衣間激吻。再後來,有媒體拍到陸隨之失心瘋一般,甘願放棄一切,隻求沈清蕪重新回到他的身邊。媒體:“對於自己老婆被前未婚夫猛烈追求這事,陸二少有什麽看法?”陸厭行:“我老婆很難哄的,隻有我能哄好。”無人的角落,陸二少一臉委屈:“我的小祖宗,今晚能抱抱嗎?我保證,隻是抱抱,什麽也不做……”
44.4萬字8.46 35007 -
完結78 章

聽夏
沈聽夏在高二那年暗戀上一個人。 他愛把校服袖口撩起,冷白色的皮膚上有不明顯的小痣,愛在課間拎一瓶北冰洋汽水,然後靠在桑葚樹下沒個正形地笑。 他是如此璀璨,發光似的照亮她一整個青春時代。 她在心裏默默祈願他能更好,而他果然如她所願,從A班到火箭班,從素人到明星,參演電影驚鴻一眼,大爆出圈。 她偷偷喜歡的人,變成了所有人喜歡的人。 他一路向前,然後離她越來越遠。 * 江溯二十四歲那年談了人生第一場戀愛,是和很喜歡的女生。 她是劇組的特邀畫師,是他的高中校友,是相隔一條走廊的同學。 他們擁有很多共同的回憶,例如學校那棵桑葚樹,小賣部裏總是售罄的汽水,袖口走線凌亂的校服。 他一直以爲是巧合。 直到無意間翻開一箱陳舊的速寫紙。 畫上都是同一個人,熟練到根本不用草稿,他起先並未認出,翻到最後,掉出幾張他主演的電影票。 票上都是七排六座——他在學校的座位號。 原來他不以爲意遺忘的青春年少,都是她念念不忘的信號。 而他記憶中那條窄而快捷的過道,於她而言,是與他漫長相望的橋。
11.7萬字8.18 1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