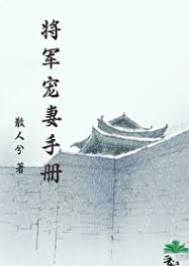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重生明珠》 恩典還是處置?
恩典還是置?
鄭明珠靜靜的發呆了很久,久到天微暗,外面丫鬟一疊聲的報:“大爺回來了。”才驚醒過來。
只是苦笑了一下,便收拾緒,款款的站了起來。
陳頤安并沒有發覺有任何異樣,鄭明珠帶著丫鬟服侍他換了服,坐下來上茶,笑道:“今天門上送了幾只野來,我想著雖說開春了,到底還冷些,便吩咐他們做了野熱鍋子。”
倒春寒倒比初春更料峭些,陳頤安便點頭:“母親那里可有送去?”
“自是送了,這還用大爺單吩咐?”鄭明珠笑著,拿了禮單給陳頤安:“這是昨兒你吩咐的,看看可,我原不大會,怕誤了大爺的事。”
陳頤安就接過來掃了兩眼,點頭說:“添一對兒如意紋金碗,就這樣吧,今天折子已經明發了,大約明天請柬就會來,你要備些小東西,到時候只怕孩子們多。”
鄭明珠點頭記下,說明這是青壯派為主,要備臨時的表禮。
陳頤安斟酌了一下,又說:“如今圣上就這一個叔叔,雖說怪誕些,世子卻是得圣上看重的,又與我一向好,禮略厚些也使得。”
這是在和代這些關系了,鄭明珠凝神聽著,果然,陳頤安又說了幾個,顯然都是與他好的,大約為了際上讓心中有數。
鄭明珠自然不敢怠慢,細細的記在心里,陳頤安笑道:“一時間你也記不清這許多,我邊有個丫頭青果,平日里我外書房有東西送給宅眷之類都是讓去辦的,這次便讓跟在你邊伺候著去,也好替你分說。”
鄭明珠笑道:“這敢好,我就怕弄出笑話兒來呢。”
陳頤安外書房四個大丫頭,鄭明珠總算都搞明白們的職分了,又笑道:“另外還有一件事,要和大爺商量。”
Advertisement
“你說。”
鄭明珠笑道:“我想著,你外書房四個大丫鬟,只宣紋格外不同些,看著有些不像,不如把宣紋抬了姨娘,另外補一個大丫鬟給你,也是服侍你一場。”
陳頤安一怔,倒是十分意外,沒頭沒腦,鄭明珠怎麼突然要給宣紋這樣的恩典?
他的目就落在鄭明珠致的臉上,見只是笑的,看不出什麼緒來,再然后,他的目就落在了炕桌上那份草擬的禮單上。
陳頤安是何等樣人,立時就明白了,鄭明珠哪里是突然想給宣紋抬姨娘,這分明就是告狀而已。
鄭明珠要備禮,從外書房走帳,又是第一次,難免需要在外書房找檔子參考,這樣的流程陳頤安是知道的,那麼多半就是宣紋為難了。
否則,什麼時候不提抬姨娘,偏要這個時候說呢?
只是主母要給一個丫鬟抬姨娘,而且還是個沒有生育的通房,那自然是極大的恩典,宣紋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只能來磕頭謝恩,乖乖的把外書房出來。
鄭明珠這一手極其明正大,你一個通房,只能暗地里使一點小絆子,而作為主母,則隨時可以掌握你的生死。
這是很早以前就明白的一個道理,在上位者的絕對權力之前,那些小花招小作都是毫無作用的,完全不夠看。
宣紋想要把持住在外書房的權力,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不過是只能不配合的要求,寄于鄭明珠做的不好而致使陳頤安失,不把外書房給鄭明珠。
或許,功過一次,新婚的那兩個月,大約就是鄭明珠的失敗和宣紋的功。
可是這一次,遇到的人已經不同了。
鄭明珠要想收拾,手段多的很,只不過必是顧慮到宣紋服侍陳頤安這十多年的分,選擇了最面的一種,給抬了姨娘,這樣的恩典,任誰都說不出的不是來,但宣紋便只有如同其他姨娘一樣,搬到甘蘭院后面去住著,守著小院,等著陳頤安。
Advertisement
姨娘怎麼可能還在外書房當差?自然就要把外書房出來了,這也是順手賣陳頤安一個人,因是你的人,我才這樣容讓的。
陳頤安心中也自有考量,當初讓宣紋攬總外書房事務,雖說是看著老穩重,做事周全,但也不過是權宜之計,份在那里,并不能長久,如今自己有意讓鄭明珠接掌外書房,本來是再名正言順不過的事了,竟敢從中作梗,必是不能就此姑息的。
只是宣紋從小就在他邊服侍,他也不想過分給沒臉,倒是鄭明珠這個置,既是恩典又是警告,細想起來便覺十分妥當。
這樣過了明路的通房,既然不會賣,陳頤安也不至于把配了人,最終還不是抬姨娘一條路,也本來是留著由主母施恩的。
這個時候提出來,簡直是神來之筆,面子里子都有了。
&n
bsp;陳頤安倒笑了:“也好,既然心大了,也不適合再在外書房伺候了,你給恩典也是的福氣。”
鄭明珠聽他這樣說,知道陳頤安是心中明白了,便說:“也是我看著從小兒服侍你的份上,這次讓一回罷了,若是再有下次,我可顧不得誰的臉面了。”
陳頤安笑道:“是,我很領你的,那麼這就進來磕頭吧。”
鄭明珠笑:“誰要你領,我很稀罕麼?現在急什麼,先吃了晚飯罷,你在外頭忙了一天,也了。”
說著便丫鬟擺飯,熱騰騰的野鴨鍋子擺上來,還有些當令的蔬菜,鄭明珠又丫鬟們也去擺一桌吃,笑道:“難得吃這樣的,要自己涮才有趣兒,你們自管吃去,大爺這有我伺候呢。”
陳頤安也點了頭,與鄭明珠對坐,又燙了熱熱的合歡花酒來,親自給倒上。
Advertisement
陳頤安覺得近些日子來,每每見著鄭明珠就有好心,事妥帖,言語俏,頗討人喜歡,既不一味強也不一味弱,溫婉中見剛強,且從來都把話說的明明白白,有一種夫妻間再無瞞的做法,很有種熨的覺。
不得不說,陳頤安很吃這一套,越是躲躲閃閃瞞著他,他越是看不上,如鄭明珠這樣,事事說清楚,什麼事讓我不高興了,我要怎麼辦,你得讓我怎麼辦,或者你得替我辦,陳頤安反而聽得進去,也樂意聽安排。
就如同外書房這件事,陳頤安原本并沒有心這樣快到鄭明珠手上,他想再看看鄭明珠的行事再下決定,可是今日鄭明珠這樣一來,他反而就不再考察,立刻把外書房給鄭明珠了。
鄭明珠當然不知道陳頤安的種種心理,只不過察言觀的本事卻向來是高手,多已經有點察覺了,見陳頤安這樣有興致,也高興,兩人涮著熱鍋子,一會兒竟把一壺酒都喝完了。
鄭明珠玉一般的臉頰上飛上了紅云,連陳頤安也微微有了酒意,俊容更比往日松弛,帶一分慵懶,歪在大靠枕上,鄭明珠給他遞茶,他就握住鄭明珠的手不放。
鄭明珠只得坐到他邊,笑道:“大爺有酒了,喝杯茶歇一歇吧。”
陳頤安笑道:“這一點算什麼,上回在東宮,太子賜酒,我們四個人喝了一壇子呢,太子還起舞劍!”
說話倒還清明,只是眼睛極亮,如天上星辰。
這樣的眼睛看著鄭明珠,有點難以自制的臉上發燙,一邊想著這是喝了酒的緣故,一邊不得不匆匆的說起話來:“那這就把宣紋來吩咐了,明兒一早我好帶著回母親去。”
“也罷,使個人去。”陳頤安漫不經心的說,放開鄭明珠的手。
鄭明珠忙站起來,吩咐人去宣紋進來說話,又讓丫頭服侍著洗了臉,擰了熱手巾給陳頤安臉,陳頤安笑道:“好歹我們也是快兩年的夫妻了,怎麼還這麼害。”
鄭明珠啐一口,心中卻想,誰跟你兩年夫妻呢!
兩人調笑了一番才坐下來,規規矩矩的說了幾句閑話,宣紋就進來了,給鄭明珠和陳頤安磕了頭,就靜靜的站在地下,低著頭一聲不吭,鄭明珠特意打量一眼,見家常穿著件半新不舊的素面淺黃的褙子,白挑線子,頭上著兩金簪子,面平靜的很。
倒是好定力,這樣還真看不出才跟主母打完擂臺當晚就被進正房說話的樣子,是篤定在陳頤安心中的地位十分穩固,還是真的十分看不起這個主母,并不擔憂?
鄭明珠在心中想了半天,也確定不了,不過,這也沒什麼關系。
鄭明珠看了陳頤安一眼,陳頤安便說:“今日你進來,是因夫人恩典,抬你做姨娘,明日你就隨夫人去給夫人磕頭,搬到后頭西院住。”
宣紋如遭雷擊,猛的抬起頭來,難掩一臉錯愕。
而鄭明珠還看得到一些更激烈的緒,仿佛有憤恨,有不甘,有痛楚,甚至還有怨毒,鄭明珠靜靜的看著,見呆了一呆,又默默的垂下頭去。
終宣紋一生,鄭明珠只看見過這一次這樣的緒發,似乎這就已經耗盡了一生。
無從掙扎,無從懇求,甚至連開恩這兩個字都被堵在里,這是一件喜事,這是面,這是主母賞的恩典。
宣紋作有些遲緩的跪了下來,給陳頤安和鄭明珠各磕了三個頭:“多謝大爺、夫人恩典。”
陳頤安又吩咐了幾句話,關于外書房事務,鄭明珠從始至終沒有說話。
在宣紋走出去之后,鄭明珠聽到外頭的丫頭紛紛恭喜宣紋,卻始終沒有聽到宣紋回應一句。
看來真是很不甘心啊,鄭明珠覺得自己已經夠忍讓了,不僅沒打沒罵,反而還抬了姨娘,怎麼也該知足了才是,可是現在看來,對這個丫頭,今后還得多警惕才行。
猜你喜歡
-
完結2263 章

步步驚華:懶懶小妖妃
一覺醒來,卻發現赤果果被關鐵籠之中,旁邊還有一雙眼睛盯著你,你會怎麼辦?洛青羽的回答是,一鞭子抽飛之!穿越?無所謂,她身為頭牌特工,換個時代照樣能玩的風生水起。不受寵的嫡女?嗬嗬,她會讓那老頭悔到腸
189.1萬字8 28745 -
連載1056 章

一胎三寶:神醫孃親,太腹黑
當醫學大佬穿越成了小寡婦,麵對嗷嗷待哺的三個小娃娃,顧清雪身懷醫神係統係統,手持銀針與閻王搶人,養最狂的崽兒,虐最渣的人!可誰想不小心惹來了邊疆出了名的鬼見愁戰神,對方有顏,有錢,有地位,拉著她就要回去當攝政王妃。顧清雪麵對某妖孽表示,已婚,有崽,不約!可誰來告訴她,為何她肚子裡出來的崽崽們個個有他的影子?二寶小呆毛麵對渣爹,逢人就說:“我家孃親博古通今,要爹爹作甚!”三寶小棉襖見人就炫:“我家孃親人美聲甜,有孃親就夠了!”唯有大寶成熟又淡定,看似毫不關心。直到,顧清雪從路邊撿來的親生小四寶大喊:“大哥,渣爹又來爬牆啦!”隻見上一刻還冷靜的大寶抄起了打狗棍衝出去,勢將孃親守護到底!
96.9萬字8 122888 -
完結496 章
毒妃有喜,我的將軍好殘暴
婚前,蕭將軍評價丞相家小姐:不知羞恥! 婚後,蕭將軍評價自己的夫人:不堪入目! 有人大著膽子問:「現在呢? “ 蕭將軍立即道:”夫人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溫柔賢淑,善良可愛,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本將軍甚是喜歡。 ”
105.1萬字8 13951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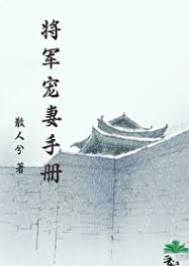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