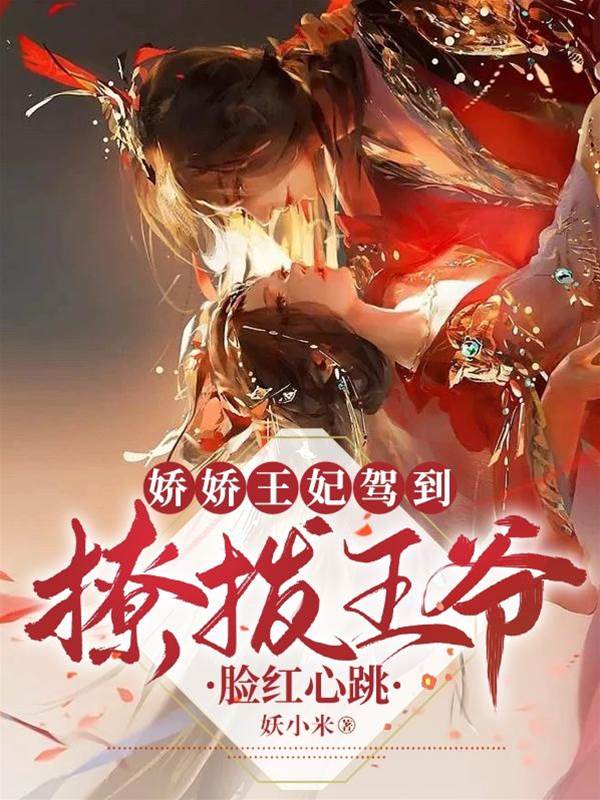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清冷世子追妻日常(重生)》 第148章 第一百四十八章
含章殿里。
永徽帝站在書案后, 目沉沉,落在階下行禮問安的宋蘊之上,良久,他緩緩道:“起吧。”
宋蘊之如今的職是從五品翰林院侍講學士, 又領經筵一職, 是以今日是一緋袍, 玉帶皂靴,可便是這樣從俗的,都無法掩蓋那一份蕭疏軒舉, 君子如玉的風神。
這樣的男子,也無怪連定國公府的嫡蕭以晴, 安郡王家的臨康縣主這等心高氣傲的貴都傾心不已,便是自己的母族安國公府, 近來也有意向他拋出聯姻的橄欖枝。
他本也視其為良臣。
永徽帝的手不覺用力,攥了案上一張薄薄的報。
永徽帝是一位溫和的君王,這是朝中大臣對這位新任天子的共識, 可今日,宋蘊之覺到一種的迫。
“不知皇上今日想讓臣講哪一篇經書?”
“宋卿是淳熙五年的狀元?”永徽帝緩緩從座步下來,走到宋蘊之旁,漫不經心道:“朕記得,那年殿試, 先帝出的題目是......問帝王之政與帝王之心。”
“是。”宋蘊之雖不明其意,仍恭聲應道。
又聽永徽帝接著道:“卿于其中提到的治國十策見解獨到, 讀之振聾發聵,是為帝王之政。”
“于帝王之心, 卿言, 使本原澄徹, 如明鏡??,照之??不見;使??軒豁,如空?虛室,約之??不容。”
“是臣之拙見。”
永徽帝淡淡一笑:“以卿之見,朕之心何如?”
“臣惶恐。”宋蘊之后退一步,拱手回道。
永徽帝不置可否地轉了話題:“宋卿是青州人氏,與定國公世子夫人系出同一師門?”
“皇上圣明,孟院長是臣之授業恩師,臣生父早亡,能有今日,多蒙恩師栽培。”宋蘊之答得謹慎。
Advertisement
“嗯。”永徽帝頷首,語氣如與臣下閑聊般,“孟昭文淡泊,但學問極好。朕聽說,他曾有意以許嫁宋卿,才子佳人,青梅竹馬,便是在朕看來,也是一段好姻緣。不知宋卿為何推拒?”
宋蘊之心中一震。永徽帝登基時日尚短,雖表現出才之心,然他并算不上帝王的心腹臣子,但永徽帝可以隨口念出他答卷中的容,一字不差,他對自己與孟清詞婚嫁未,這種兩家都并未對外宣揚的事都知之甚深。
夏日衫輕薄,殿外尾森森,殿中鎏金風款款,送進涼風習習,便是在滿殿清涼里,宋蘊之的上亦起了一層細的薄汗。
他定了定心神,回道:“臣不敢瞞皇上,于臣而言,恩師如父,因此,臣與孟夫人雖非緣至親,卻視其如妹,并無男之。”
“孟夫人亦作此想。”
永徽帝倏然踱到他前,語氣平靜“哦”了一聲:“那宋卿是另有心儀之人了?”
宋蘊之沉半晌,回道:“是。”
他垂著頭,便見那繡金線龍紋緝米珠朝靴停在了他前,“既有心儀之人,宋卿為何蹉跎至今尚孤一人?”他問得很慢,但宋蘊之能覺到他盯著他的目幽深,不放過他臉上的每一個表。
話到此,宋蘊之已可確定了永徽帝的用意,他沉默了一瞬,才鄭重答道:“臣確有心儀之人,然并無此意,臣不能強求。”
“果真?”永徽帝笑了一聲,不辨喜怒:“以宋卿這般才學人品,奉上真心,竟還有子不喜歡?”
“不知這位佳人姓甚名甚,居于何?若卿仍念念不忘,朕可下一道圣旨,為卿賜婚。”
宋蘊之一驚,忙道:“皇上,不可!”
Advertisement
“有何不可?卿是朕肱之臣,朕親為卿求娶,天下哪一家能拒呢?”
宋蘊之苦笑道:“皇上苦心,臣激不盡,但既無心,強求無益,反怨偶,況已嫁為人婦,夫妻和睦,臣做不來拆散人家夫妻之事。”
聞言永徽帝面稍緩,笑道:“聽說蕭臨簡的妹子對你有獨鐘,為此推拒了不親事,朕看你與蕭家姑娘在一起,也堪匹配,你與蕭家本就有親,親上加親,也是一段佳話。”
宋蘊之跪下,鄭重道:“皇上意,臣惶恐不已,臣如今一心于公務上,暫無家之意,恐耽誤了蕭姑娘。”
“況既說到此,臣有一念,求皇上恩準。”
“嘗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況自古圣賢言學,咸以躬行實踐為先,識見言論次之,臣不才,請外放。”
永徽帝神中出詫異之,沉思一瞬,他淡淡笑了聲:“ 既卿有實政之心,朕會考慮。”
“謝皇上。”
*
定國公府。
清詞收到宋蘊之送進來的消息,神變幻,驟然想起那日馬車上蕭以晴問的話,凝眉沉思片刻,對白道:“將今日蒸的茉莉花糕盛出一碟,隨我去瞧瞧三姑娘吧。”
自那日千秋節蕭以晴中了暑回府,近些日子一直懨懨的未見好,人也失了以往的活泛勁兒,只窩在猗蘭軒里未曾出門。
清詞到的時候,許是午歇剛起的緣故,猗蘭軒里安安靜靜的,蕭以晴坐在窗前,著午后的斜,怔怔地不知在想些什麼,都沒有聽見進來的腳步聲,直到清詞將手搭在肩上,才悚然回首,喚了聲:“嫂子。”
“好些了沒?”清詞坐在旁,邊從食盒里取出茉莉花糕,邊笑問道。
Advertisement
做好后又特意用冰湃過的茉莉花糕呈半明的鵝黃,還沒口便聞到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若是往常,蕭以晴定會興興頭頭與商量泡什麼茶來配,可今日只是瞥了一眼,有氣無力道:“多謝嫂子,可我今日胃口有些不好,先放著罷。”
清詞的手頓了頓,隨即示意屋里的丫鬟出去,待只有他們二人,才對蕭以晴道:“晴姐兒一向與嫂子親,今日嫂子想問你一句話,晴姐兒可能如實答我?”
蕭以晴睫閃,抬眸看了一眼,不作聲。
清詞恍若未注意到的神,接著道:“嫂子想問的是,娘娘千秋節那日,晴姐兒究竟是看到了什麼,或者,去做了什麼。”
“那日你問我,若是一個人無意做了錯事,卻傷害了別人,還記得嫂子是怎麼答你的嗎?”
“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蕭以晴了,言又止。
清詞目中帶著鼓勵看著,足足一刻鐘的功夫,蕭以晴才猶豫著道;"那日,我隨縣主去劃船,并沒有見什麼人。”
話音未落,便見孟清詞臉上流失落之,嘆了口氣:“原是如此,那待你哥哥回來,我們再想辦法罷。”
“出了什麼事?”蕭以晴忍不住問道。
孟清詞告訴:“是我師兄,千秋節那日不知為何惹怒了皇上,許是會被貶謫出京。”
“但師兄怕我擔心,什麼都不與我說。”郁郁道,隨之起:“罷了,這本也與你無關。”
蕭以晴一把拉住:“嫂子,不是這樣的,宋大哥他,他沒有錯,是我的錯。”“哇”地哭了出來:“是我害了他。”
清詞本就是誑蕭以晴的,見肯說實話自然松了口氣,但見哭得厲害,又有些不忍,拍了拍的手:“不急,晴姐兒慢慢慢說。”
在蕭以晴斷斷續續的講述中,清詞才知事的始末。原來那日蕭以晴并未隨晉康縣主去劃船,而是自己在太池夕波亭旁的假山旁發呆,忽見幾個穿朝服的員簇擁著永徽帝過去了,邊走邊議論著朝事,其中便有宋蘊之,但幾人并未看見,是以也未起問安。
但恰巧這時,貴妃娘娘的儀仗過來了。
貴妃拜見過皇上后便繼續前行,宋蘊之卻不知為何落后了一步,正想上前打招呼,貴妃娘娘卻帶著一個宮人去而復返,似是掉了什麼東西,過來尋找。
兩人對片刻,宋蘊之行了一禮,貴妃娘娘側避過,不久便各自離去。
“他們有說了什麼嗎?”清詞皺眉問。
蕭以晴搖了搖頭,噎噎道:“后來.....后來我在那站著發呆,德妃娘娘過來瞧見了我,問我在看什麼......我當時不知怎麼想的,就說......就說見到方才貴妃娘娘和宋大人在這兒。”
不想起那日的形,遠,太池碧葉連天,紅荷映日,眼前,一對風采無雙的人兒相對而立,縱默然無言,但素日大大咧咧的,卻能到那一份靜靜流的愫和悲傷。
“德妃娘娘笑了一聲,問我是不是喜歡宋大哥......我說沒有,德妃娘娘也未追問,便自去了。”
攥著清詞的手,聲道:“可我后來,越想越是不安,我會不會,會不會給宋大哥招來什麼禍事......”
原來如此。
后宮子,察言觀是基本的生存法則,孫德妃能從蕭以晴的神中瞧出端倪,并不奇怪,而,想必是永徽帝的后妃中,對顧紜得寵最耿耿于懷的人。
順著這個思路往下查,很容易便會查到青州往事。
是夜,清詞無比煩惱地與蕭珩說起此事,苦笑道:“果然,世上沒有不風的墻。”
蕭珩倒是比淡定許多:“竇初開,互有好亦是常事,皇上心寬廣,海納百川,許不會在意,只他們二人可互有信?”
提起信,清詞便忽然想起因著玉佩一事與蕭珩起的齟齬,忍不住橫了他一眼,才猶疑著回憶:“據我所知,應是沒有罷。”
蕭珩顯然想起了同一件事,頗為心虛地了鼻子,安:“以我來看,娘娘子極為謹慎,你若實不放心,改日遞牌子宮去見見罷。”
作者有話說:
正文完結倒計時。
1.“問帝王之政與帝王之心。”以及“使本原澄徹,如明鏡????,照之????不見;使????軒豁,如空??虛室,約之????不容。”一句出自明朝狀元趙秉忠的殿試答卷,現存于青州博館,網上有全文譯文,真滴是才華橫溢,有興趣的可以找找看一看。
2.“自古圣賢之言學也,咸以躬行實踐為先....."一句出自明·林希元《羅整庵困知記序》。
猜你喜歡
-
完結474 章

喜嫁
穿入夢中,一夢成真。 連續三日做同一噩夢,可再次蘇醒,發現自己成為夢中人! 大族後裔、庶嫡之身,父慈母寵弟可愛,可清正小家成了各房爭鬥的靶子、刀俎上的魚肉,這怎能忍? 噩夢場景縈繞心頭,會否真的發生? 她,心中隻有兩個字活著。
126.4萬字8 18298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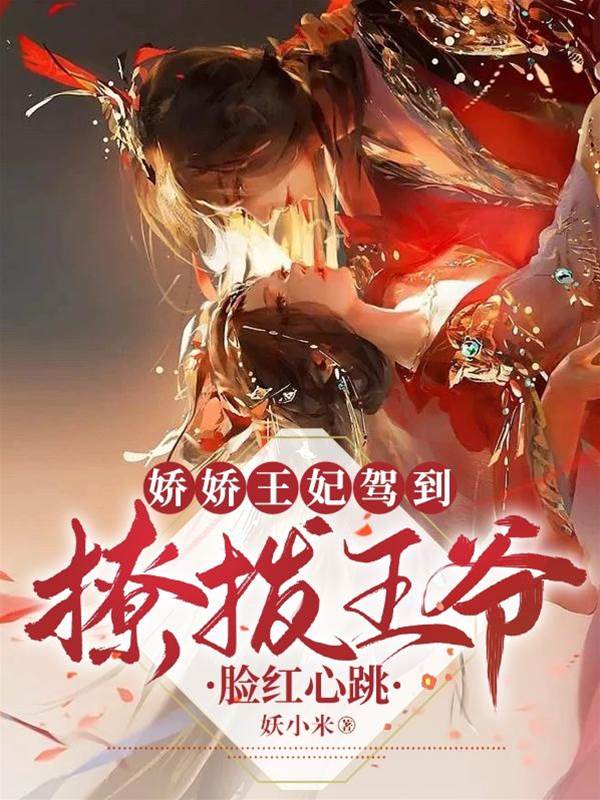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1033 章
紈绔夫妻互捧日常
未婚夫被搶? 被迫嫁京城著名紈絝? 蘇予安:嘖,當我這心理諮詢師是白當的? 這十年是白穿的!! 江起雲:我要娶我堂哥的前未婚妻? 打死我也不服...... 真...... 真打?! 滿京都的人都在等著看兩個人的笑話,可等到的卻是兩人的日常互捧。 江起雲:我家娘子機敏聰慧,可旺夫鎮宅! 蘇予安:我家夫君玉樹一棵,可遮風擋雨! 京都貴族VS百姓:......
182.3萬字8.18 19262 -
完結759 章
神醫棄女要強嫁
明幼卿是中西醫雙料博士,一朝穿越,成為被太子退婚後,發配給了廢物王爺的廢材嫡女。 世人都笑,廢材醜女配廢物王爺,真絕配。 只是新婚後……某王:沒想到明家醜女樣貌傾城,才氣絕倫,騙人的本事更是出眾。 某女勾勾手:彼此彼此,也沒想到廢物王爺舉世無雙,恩,身材也不錯~兩人真真絕配!
138.2萬字8 110557 -
完結733 章

和離后禁欲殘王每天都想破戒
前世,她為家人付出一切,卻被人棄之敝履。重生后,她果斷與眼盲心瞎的丈夫和離,與相府斷絕關系。斗婊虐渣,從一個棄婦搖身一變成了各個大佬爭相寵愛的國寵。帶著疼愛她的外祖一家青雲直上。當發現前一世一直救她護她的人,竟然是她的“大表哥”時,她紅了眼,緊緊摟著那人不撒手。欲拒還迎的男人緊繃著唇角:“青天白日,成何體統!” 可他那冷情的眉眼,都已經彎成了月牙。聲音啞沉地道:“關門!”
132萬字8.18 1744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